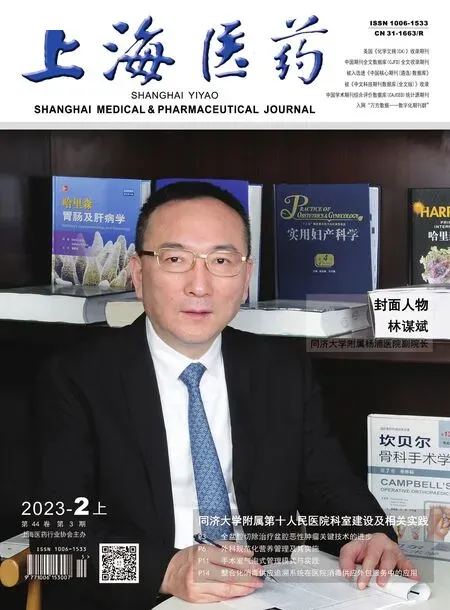全盆腔切除治療盆腔惡性腫瘤關鍵技術的進步
吳小材 吳天琪 陳春球 尹路
(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腹部外科疑難診治中心 上海 200072)
近年來,我國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呈增高趨勢,估計2022年中國結直腸癌新發病例數為59.223 2萬例,因結直腸癌死亡病例數為30.911 4萬例[1]。局部進展期直腸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表現為侵犯鄰近器官或組織,如膀胱、子宮、盆壁、骶尾骨等,約有30%的直腸癌初診時就已局部進展而侵犯鄰近器官或組織。對于此類患者,臨床上往往先給予新輔助放化療,以期達到縮小腫瘤、降低腫瘤分期的目的,使之后續能夠進行根治性手術治療。不過,有部分患者(占比約為4% ~ 8%)的腫瘤即使經新輔助放化療后也未明顯縮小,且仍侵犯了鄰近器官或組織,對這部分患者須擴大手術切除范圍[2]。此外,約有40% ~ 60%的直腸癌患者術后發生腫瘤復發,復發患者中有約40%的患者適合接受潛在治愈性治療,其中手術完全切除(R0切除)是確保達到治愈性治療目的的關鍵[3]。
對于經新輔助放化療后腫瘤沒有明顯縮小且仍侵犯了鄰近器官或組織的LARC患者,為達到R0切除的目的,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全盆腔切除術(total pelvic exenteration, TPE)。美國一項對全美外科技術促進項目數據庫數據的回顧性研究顯示,在所有接受TPE的患者中,約有35%患者的原發疾病為結直腸癌,45%患者為泌尿系統惡性腫瘤,15%患者為婦科惡性腫瘤,僅5%患者的原發疾病為其他疾病[4]。
關于局部復發的直腸癌(recurrent rectal cancer,RRC)的治療難點,首先是患者的復發模式各異,腫瘤異質性大。患者中既有吻合口處復發而導致腸梗阻的,也有非吻合口處復發的。若復發腫瘤膨脹性生長,則可導致腫瘤侵犯直腸周圍組織,如直腸后方的骶骨和兩側的骨性盆壁。這些患者往往痛苦不堪,不但腸梗阻急待解決,而且腫瘤引起的疼痛亦須緩解。其次是術前的放化療導致患者局部復發情況愈加復雜,組織受到放化療的影響,解剖結構及其層次均有與未接受放化療患者不同的表現。再次,甄選最佳治療方案時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既往治療的方案及順序、治療的質量、局部復發的程度、有無遠處轉移及遠處轉移灶可否切除等。嚴格篩選合適的患者,并進行相應的恰當治療,這是使患者獲益的關鍵。
1 TPE的泌尿系統風險
TPE是一種高風險手術,雖然過去20年間其圍手術期死亡率不斷下降,但并發癥發生率仍居高不下,最高達78%,而這些并發癥中有半數與泌尿系統有關。在TPE導致的泌尿系統并發癥中,最常見的是泌尿系統感染,其余有吻合口漏、尿漏和涉及泌尿系統的瘺等[5]。實際上,大部分TPE后患者會因為放療或腫瘤復發等原因而出現輸尿管梗阻或膀胱瘺,這是促使患者尋求進一步手術治療的前兩個重要原因。
對于全盆腔切除患者,術前請泌尿科醫師會診是非常必要的。術前應當完善患者的影像學檢查,明確其有無輸尿管擴張或狹窄。有相當比例的需要接受TPE的患者在輸尿管骨盆入口處或以下形成狹窄,前者多為放療引起的纖維化狹窄,后者則通常是復發的腫瘤堵塞或擠壓輸尿管或輸尿管開口所致。TPE前通過輸尿管鏡放置雙側D-J管既能減輕輸尿管梗阻,保護腎功能,又可在術中處理粘連分離時指示輸尿管位置,從而避免損傷輸尿管。尿路流出道重建在大多數醫院都是需要泌尿外科醫師上臺協助完成的。
全盆腔切除后的尿路重建包括輸尿管皮膚造瘺、輸尿管-回腸代膀胱造瘺等,原位代膀胱重建用于部分后盆腔廓清患者。尿漏是TPE后尿路重建最嚴重的并發癥,部分患者需要再次進行手術干預。
2 聯合血管切除、重建及其并發癥風險
對于接受TPE的LARC或RRC患者,目前已發表的涉及重要血管重建作為腫瘤根治性切除術組成的研究文獻僅有4篇[6-8],統計見最常切斷的血管是髂內血管(包括髂內動、靜脈),對約3/4的患者通過聯合切除/切斷血管達到R0切除目的,并發癥發生率為16.7% ~ 70%,但其中僅有2例患者因重建的血管出現血栓而須再次進行手術干預。Brown等[9]的回顧性研究顯示,在他們中心接受TPE的336例患者中共有21例(6.3%)同時接受了血管切除和重建。與其他TPE相比,聯合血管切除和重建的TPE的手術時長沒有顯著增加,但患者術中出血量顯著更大,R0切除率也有所下降。21例患者中,有96%的患者1年血管持續暢通,但多達52%的患者經歷了血管相關并發癥。對于腫瘤已侵犯重要血管的患者,仔細篩選合適患者并對他們進行聯合血管切除和重建的整塊切除TPE,是使這些患者手術達到R0切除的重要治療方式,不應該將他們完全排除在TPE外。
3 微創手術在TPE中的應用
Skrovina等[10]于2006年率先報告,對3例LARC患者進行了腹腔鏡輔助的TPE并獲得成功。自此之后,已見不少將腹腔鏡乃至于機器人手術技術運用于盆腔臟器聯合切除或TPE的研究文獻,其中大多數為病例或病例系列報告,且全為單中心的回顧性研究。這些研究初步證實了在經驗豐富的三級醫療轉診中心,微創技術運用于TPE的安全性良好。由于已開展的腹腔鏡和機器人TPE例數較少,加之迄今還無相關多中心前瞻性對照研究報告,故Kazi等[11]回顧性比較了他們單中心微創TPE與開放性TPE的優劣。結果發現,與開放性TPE組相比,微創TPE組患者的術中出血量較少,切口感染率較低,但R0切除率、3年總生存率、無病生存率和局部無瘤生存期相當,住院時間也未縮短。Nanayakkara等[12]于2014年首次報告進行了機器人手術系統輔助的TPE,他們的病例系列分析顯示,與腹腔鏡TPE相比,機器人手術系統輔助的TPE具有患者術中出血量少、中轉開腹率低、住院時間短等優勢。
腹腔鏡TPE的技術難點在于建立足夠的操作空間,以達到清晰辨認正確的解剖層面,確保手術安全的目的。相比之下,機器人手術系統的操作臂有720°的自由度,術者的操作空間得到很好的滿足,即使是對體質量指數高、骨盆狹窄的患者,需要進行長時間手術且保持高強度對抗牽拉等操作,采用機器人手術系統也能較傳統腹腔鏡手術節減術者的體力消耗[13]。此外,部分接受TPE的患者術前接受過放療,且許多患者并非第一次接受盆腔手術,他們的解剖結構異于常人。但達芬奇手術機器人系統具有穩定的成像系統,可以3D顯像并調節放大倍數,使術者能夠清晰地觀察到患者盆腔的精細解剖結構,幫助術者完成手術操作。須指出的是,首先我國國內很多醫院尚未配備機器人手術系統,其次是與傳統腹腔鏡或開腹手術相比,機器人手術系統輔助的TPE的手術時間延長、費用增加,而腫瘤學預后卻無顯著改善[14]。
4 聯合鄰近骨切除
部分LARC患者的腫瘤會自背側侵犯骶尾骨,自側壁侵犯骨盆入口/側壁、恥骨和坐骨等。對于腫瘤侵犯骶前筋膜的患者,為了達到R0切除目的,推薦進行聯合部分骶骨的整塊切除而不是僅將腫瘤自骶前筋膜切下,后者可能存在環周切緣陽性[15]。R0切除是聯合骨切除的TPE患者長期生存的最重要預后指標,并與患者術后的生活質量密切相關。
在所有聯合骨切除的TPE患者中,56.9%的患者僅接受了低節段骶骨切除(在第2和第3骶椎連接處平面以下),32.4%的患者僅接受了骨盆入口/側壁切除,僅切除尾骨、恥骨和坐骨的患者占比分別為6.2%、2.1%和1.6%[16]。
骨科醫師通常會讓患者采取俯臥位對其進行骶尾骨切除。不過,對于涉及聯合骨切除的TPE,手術入路的選擇應根據聯合骨切除的部位來確定。Ng等[17]指出,對于預計骶骨離斷平面低于S3的患者,應選擇經腹聯合經會陰入路,首先經腹入路游離側方相關髂血管主干及分支,以及神經、輸尿管和盆腔組織。經腹入路有利于暴露和控制髂血管,避免大出血發生。經會陰入路則可不用將患者翻身重新消毒,利用原先改良截石位在肛門邊緣做一橢圓形切口(對于部分有Miles手術史者,可利用原會陰切口),經此切口游離包括坐骨直腸窩內的脂肪墊至盆底的皮下脂肪組織,并在經腹腔手術組手術醫師的指引下向頭側游離至切除平面會師[18]。此種經腹聯合經會陰入路既有不用術中改變患者體位的便利,又具有在患者骶前出血時能從容控制髂血管等優勢。
5 結語
TPE的現狀是,盡管患者群體客觀存在,但具有實施TPE技術的醫師卻受限于各種原因(如手術風險、患者篩選標準不統一等)而無法常規開展TPE,致使大部分患者被轉診至腫瘤內科,在無窮無盡的放化療過程中最終失去最佳手術治療機會。外科醫師應有擔當,對合適患者施以援手,給患者一個提高生活質量,爭取治愈性切除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