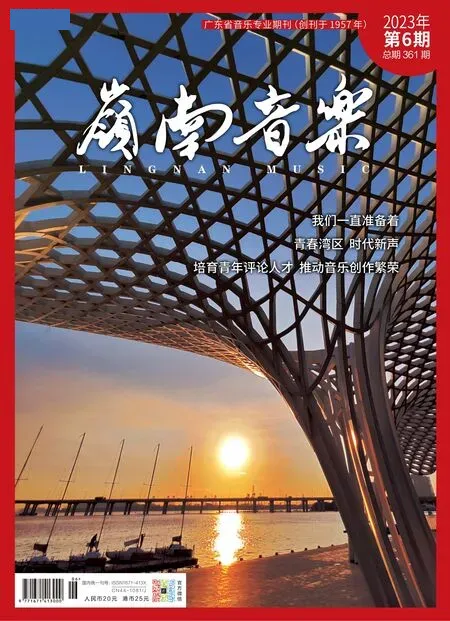記憶里的嶺南小曲
——評“2022年我們的新時(shí)代”入圍歌曲《嶺南春曉》
文|譚笑
嶺南——令人心醉的地方。騎樓街巷的千年古邑,與高樓林立的現(xiàn)代化新區(qū)相得益彰,既古老,又現(xiàn)代,孕育出獨(dú)具魅力的嶺南文明,浸潤于歷史變遷之中。在朝氣蓬勃的新時(shí)代,我們?nèi)绾瘟粝隆⑷绾巫V寫,歷史贈予我們的文化畫卷?在《嶺南春曉》中,粵樂風(fēng)格的旋律與唱腔都給人以強(qiáng)烈的嶺南印象,我分明聽見,歌曲里屬于嶺南的傳統(tǒng)氣韻與悠悠歲月。
《嶺南春曉》由崔臻和作曲,鄧耀邦作詞,曉君演唱。作曲家崔臻和2005年南下來到廣東,多年來,嶺南風(fēng)情的浸潤給予了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以深厚的滋養(yǎng);詞作者鄧耀邦作為佛山人,多年來一直堅(jiān)持粵語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演唱者曉君有著深厚的粵曲功底,她以獨(dú)特的粵劇腔調(diào)對歌曲加以潤飾,展現(xiàn)出溫婉秀美的嶺南韻味。這首歌曲依托著三位創(chuàng)作者對嶺南音樂的熟悉,流露出對嶺南的真摯之情。
在新時(shí)代音樂文化中,創(chuàng)作者的視野更為廣闊,多元豐富的創(chuàng)作浪潮下,音樂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者表達(dá)自我的方式,在某些時(shí)刻,當(dāng)諸如“民族的”“時(shí)代的”或“世界的”等命題出現(xiàn)時(shí),創(chuàng)作者擔(dān)當(dāng)起了新時(shí)代的使命,需要思考如何與此命題建立聯(lián)系,找尋更多拓寬音樂的可能性,以達(dá)到自我與藝術(shù)的平衡。多年來,以地域?yàn)楹诵牡念}材創(chuàng)作,早已成為作曲家偏愛的選擇之一,例如對該地域現(xiàn)存的民間音樂素材進(jìn)行直接呈現(xiàn),或作改編和加工,而后者的創(chuàng)作不再局限于對民間音樂的簡單援引,而是經(jīng)由作曲家的重塑,將民間音樂的特征音及元素轉(zhuǎn)化為新的旋律。在這一過程中,創(chuàng)作者回歸傳統(tǒng),尋找創(chuàng)作之內(nèi)核,通過地域性的聲音和文字符號,給予聽者聽覺和文化上的認(rèn)同與親切,以表現(xiàn)本地域音樂文化的精髓與人文精神。顯然,《嶺南春曉》正是這樣一部作品,筆者在其中體會到了記憶中的嶺南之音。
記憶里的嶺南,風(fēng)光旖旎,人情純樸。是《雨打芭蕉》的粵曲,是西關(guān)大屋前的茶香,是校園里盛開的紅棉……在歌詞寫作中,生長于嶺南的鄧耀邦,圍繞春耕主題,以牛哥哥與茹妹妹、老農(nóng)與孩童的故事展開書寫,“木棉”“芭蕉”等嶺南地域性符號的景物成為歌曲的文本,并通過《月光光》式的歌謠體再現(xiàn)了嶺南古邑山水秀麗、民風(fēng)淳樸的人文之景。嶺南的春曉,絕不僅僅是農(nóng)耕文化下的豐收,更是改革開放的春潮,是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蓬勃。歌曲尾聲,千言萬語化為一句“歡笑,歡笑”,仿佛古今嶺南人的互文,觀新時(shí)代的嶺南,無限祥和,歡喜無比。
記憶里的嶺南,粵曲名揚(yáng),剛?cè)岵?jì)。粵曲以調(diào)式、律制的豐富性、復(fù)雜性、多變性而著稱,其音律稱為“線”,在傳統(tǒng)粵樂常用的四種音階合尺線(5-2)、上六線(1-5)、乙凡線(7-4)、士工線(6-3)中,皆以兩個(gè)純五度的工尺音名呼之。其中“乙”“凡”兩音具有游移性,同時(shí)兩音之間構(gòu)成純五度關(guān)系,這是粵曲極富特色的地方。《嶺南春曉》鮮明的嶺南風(fēng)格取決于作曲家崔臻和緊緊扎根于嶺南音樂的沃土,通過對粵樂調(diào)式的錘煉得以實(shí)現(xiàn)。在歌曲中,“乙”“凡”常以骨干音形式出現(xiàn),如樂句“芭蕉俏”“老屋檐”“醉人暖”“愛啼鳥”,“凡”音均在強(qiáng)拍位置;旋律中圍繞4、7構(gòu)成的旋律進(jìn)行,也總讓人聯(lián)想起乙凡線的運(yùn)用;歌曲中普遍出現(xiàn)的小三度跳進(jìn)加大二度級進(jìn)的旋法,凝練出聽眾所熟悉的嶺南音樂的共性風(fēng)格。盡管作曲家并未使用高胡這類極具代表性的粵樂樂器作為伴奏,但對音高材料的組織與運(yùn)用,基本遵循了粵樂音響與聽眾聽覺習(xí)慣的傳統(tǒng)樣式,得以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粵樂的審美效果,嶺南韻味呼之欲出。
記憶中的嶺南,是古樸文雅的粵語,是讓詩詞歌句更押韻的九聲六調(diào)。在《嶺南春曉》的表演上,創(chuàng)作者顯然考慮到歌曲的地域性質(zhì),選擇讓演唱者用粵語演唱。一方面,滿足了嶺南人共有的聽覺習(xí)慣,另一方面,演唱者曉君扎實(shí)的粵劇功底為整首歌曲的呈現(xiàn)錦上添花。縈繞著的假嗓吐音與婉轉(zhuǎn)的拖腔讓整首歌曲充滿嶺南情調(diào),優(yōu)美溫婉;樂句“聽到雨打芭蕉蛙在稻田里叫”弱起上板,歌者出乎意料的加速處理與高亢的音調(diào),讓歌曲富于變化,提升了作品的完成程度。
盡管無法得知《嶺南春曉》究竟是先曲后詞,還是先詞后曲,但整體而言,該歌曲擁有地域特質(zhì)的歌詞、傳統(tǒng)粵樂風(fēng)格的旋律與粵曲的唱腔,的確在詞、曲、唱三方面表現(xiàn)出一致性,地道的聲、景構(gòu)造展露出創(chuàng)作者極具地域意識與傳統(tǒng)意識的創(chuàng)作觀念。或許,對于《嶺南春曉》這樣一部主題鮮明、地域性極強(qiáng)的歌曲作品,創(chuàng)作者并不刻意通過宏大的敘事或高深的音響去構(gòu)建“現(xiàn)代”①的氣質(zhì),看似傳統(tǒng)的樣貌也許并不是創(chuàng)作者的妥協(xié),而可能是創(chuàng)作者多年來堅(jiān)守的創(chuàng)作理念。作曲家崔臻和在一次采訪曾道:“好歌是能讓觀眾記住的,所以我在創(chuàng)作上注重旋律,講究旋律的線條感。”②無論是早年的《阿爸的草原》《十二木卡姆》,還是來到廣東后創(chuàng)作的《咸水謠》,崔臻和充分尊重民族、地域原有的音樂風(fēng)格,做好聽的歌曲,作大眾喜聞樂見的音樂。
這也正是流行歌曲這一體裁與其他音樂形式最不相同的一點(diǎn),它與社會大眾緊密聯(lián)系,可聽性對一首歌曲的評價(jià)至關(guān)重要,好的歌曲需要滿足聽者的聽覺審美與愉悅。因此,筆者以為,對《嶺南春曉》的評價(jià)無須涉及是否平庸,或是“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這一悖論的討論。在流行歌曲中,若盲目“出新”而強(qiáng)加異響,旋律雖富有深意但不再好聽,這種力求突破的做法也稍顯尷尬。相反,若能在現(xiàn)有的地域音樂語言、創(chuàng)作觀念和范式上創(chuàng)造富有文化溫度和情懷的作品,也能流傳萬芳,何樂而不為?此種程度上,《嶺南春曉》似乎達(dá)成了它的使命:小曲兒一唱,聽眾津津樂道,流淌千年的嶺南文化在新時(shí)代中再次鮮活。
當(dāng)然,這并不代表我們無須發(fā)掘流行歌曲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只是在新時(shí)代的流行音樂發(fā)展中,探索與突破不應(yīng)成為創(chuàng)作的枷鎖,創(chuàng)作的主體需要面向社會大眾,而非一味囿于自我。同樣,地域性的歌曲并非一定遵循“傳統(tǒng)加現(xiàn)代”的范式,我想,《嶺南春曉》也給予了一定啟示:回歸傳統(tǒng)之根,尋人文精神之寄。
記憶里的嶺南,風(fēng)光旖旎,人情純樸。是《雨打芭蕉》的粵曲,是西關(guān)大屋前的茶香,是校園里盛開的紅棉……
注釋
①這里指的是當(dāng)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某些音響新奇晦澀、創(chuàng)作技法高深復(fù)雜的現(xiàn)象。
②崔臻和受訪資料:《20首歌曲唱出20首中國故事》,羊城晚報(bào)。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166352738467656&wfr=spider&for=pc2022年10月31日。
- 嶺南音樂的其它文章
- 我們一直準(zhǔn)備著
——寫在“灣區(qū)有新聲”2023粵港澳大灣區(qū)青年流行歌手大賽總決賽結(jié)束之際 - 云開日出·水綠山青
——解析琵琶協(xié)奏曲《云開日出》 - “我們的新時(shí)代”2023主題歌曲精品原創(chuàng)歌曲9首
- 少年的夢想從未遠(yuǎn)離
——記廣東省音協(xié)會員、全國文科衛(wèi)“三下鄉(xiāng)”服務(wù)標(biāo)兵陳晚翠 - 那片流淌著的花田
——從《花田不見君》看粵劇的金聲玉振 - 發(fā)揚(yáng)民間藝術(shù)家優(yōu)良傳統(tǒng) 推動嶺南音樂高質(zhì)量發(fā)展
——紀(jì)念廣東漢樂名家李德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