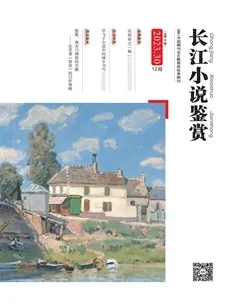《夜雨秋燈錄》對《聊齋志異》女性形象塑造的繼承與新變
[摘? 要] 《夜雨秋燈錄》及《續錄》在《聊齋志異》一眾仿書中脫穎而出,被稱為唐人小說之流亞、《聊齋志異》之嫡傳。與蒲松齡相比,宣鼎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發生明顯改變,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從以狐鬼為主體的形象向現實生活中女性形象轉變,以及從以主觀視角來描述轉向以旁觀者的視角來審視現實中的女性光輝。在這一轉變的背后,反映出了作者更為復雜的創作心態和女性觀。筆者將以此為出發點,結合時代背景深入剖析女性形象的繼承與變化。
[關鍵詞] 《夜雨秋燈錄》? 《聊齋志異》? 女性形象繼承與新變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30-0007-04
一、《夜錄》與《聊齋》的淵源
《聊齋志異》是文言傳奇小說的巨擘,在后世出現了許多仿作,并形成一種文學現象。“作為《聊齋》之后的余波,《聊齋》仿書仍然是清代文言小說界的一個重要群落,最終以其連貫而趨同的藝術風格而成為一個重要的小說流派,成為清代文言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1]這些作品通常沿襲《聊齋》常用的狐鬼花妖題材,在塑造人物形象、諷刺黑暗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等方面十分突出。
對《聊齋志異》諸多仿作的界定,目前學界觀點較為統一。在時間上一般認為自清乾隆中葉始,受《聊齋》影響,文言小說創作出現繁盛局面。在形式上因思想的分野形成兩個派別:聊齋派和閱微派。前者多是對《聊齋》的直接模仿,注重故事的外在表現,重綺麗之思少質樸之言,如《諧鐸》《夜雨秋燈錄》《夜談隨錄》《子不語》等;后者不滿足于單純敘述故事,著力在抒發議論、勸善懲戒之處下功夫,如《閱微草堂筆記》《右臺仙館筆記》《耳郵》等。經筆者統計,綜合兩種派別之后,《聊齋志異》的仿作書目多達三十種,分別在清乾隆和光緒年間出現兩次創作熱潮。在一眾仿書之中,晚清時期安徽天長人宣鼎所著的《夜雨秋燈錄》及《續錄》尤為引人注目。蔡爾康的題序贊此書“書奇事則可愕可驚,志畸行則如泣如訴,論世故則若嘲若諷,摹艷情則不即不離。是蓋合說部之眾長,而作寫懷之別調”[2]。從中可以窺見《夜雨秋燈錄》藝術造詣之高。
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宣鼎在繼承《聊齋志異》的基礎上做了許多新的嘗試。他關注生活在各個角落、擁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在作品中寄托了自己對社會環境的看法,對丑惡現實進行揭露、對女性之美進行塑造等。因此,比較兩部作品對女性形象的刻畫,可以窺見時代的變遷、作家個性的差異與文言小說的新發展。
二、同工之妙
《夜雨秋燈錄》能在《聊齋志異》一眾仿作中脫穎而出,與其深刻體悟《聊齋》精神是分不開的。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夜雨秋燈錄》對《聊齋志異》的繼承。
1.具有道德和人情之美的女性形象
《聊齋志異》通過對一系列超現實女性的描摹,表現了作者對理想女性的期待和對美好人性的向往。在小說中,這些女子雖非人間的正常女性,但在接受了人類的恩惠之后,她們展現出了知恩圖報的美好品質,不僅成為書生的紅顏知己,更在關鍵時刻挽救了書生的性命。這些女子身上所表現出的美好情操,正是人類所贊賞的。
《聊齋志異》中的狐女嬌娜,是孔生的紅顏知己。蒲松齡說:“不羨慕孔生有貌美嬌妻,卻傾慕他得到一位紅顏知己。”[3]嬌娜第一次出場就幫孔生解除病痛,等他痊愈后便悄然離去。兩人再次相見已經過了數年,這次張生為救嬌娜幾乎殞命,嬌娜得知后又再次救活孔生。嬌娜雖是狐女,卻更像是溫柔體貼的女人。另有狐女小翠,因王太常對其母親在雷電中無意的庇護之情前來報恩,嫁給王太常的癡兒元豐。小翠不嫌棄丈夫智力低下,不僅仔細照顧他,還辛勤操持家務,獨自一人撐起了整個家庭,這是許多女子都做不到的。
宣鼎的《夜雨秋燈錄》也是如此,作者在超現實的世界中描繪了知恩圖報的女性形象。《鄔生艷遇》中的狐女小素因鄔生吟詩而至,雙方感情直線升溫,不料遭到小素父親強行拆散。鄔生因此大病不起,小素得知后贈藥使鄔生痊愈。另有虎女珊珊,為報救父之恩嫁給焦生,不僅持家有方還幫助丈夫走上了仕途,卻因受到小妾讒言無奈退回山林。焦生遇難時珊珊不惜化身虎形來解救他,不計前嫌帶其問道求仙,實現長生。盡管珊珊多次遭到誤解,仍不改初心屢次幫助對方。作者將人和虎的行為進行對比,表達對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女性人物的期待。
2.巾幗不讓須眉的奇女子形象
自古以來,男性與女性在社會地位上存在顯著差異,男性通常占據主導地位,而女性則被限制在家庭空間中,缺乏獨立的人格和價值。
但在蒲松齡和宣鼎筆下,卻一反傳統男尊女卑的思想,塑造出了一類巾幗不讓須眉的奇女子形象。她們與男子有同樣的才華,甚至更勝一籌。《聊齋志異》中的《顏氏》,講述了女主人公顏氏因丈夫屢試不第,氣憤之下自己去參加考試,一朝高中在官場上大顯身手,最后還成了御史的故事;《夜雨秋燈錄》中《耍字謎》一篇,講述女子劉士璜,從小便不甘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之后她女扮男裝進入仕途,成為一方縣令造福百姓,但被證實女子身份后她卻難逃世俗規約,前后落差之大,令人唏噓。這兩篇作品皆是女子女扮男裝去參加科舉,考取功名后造福一方的故事,體現出作者不被儒家思想束縛,對女子才能與魄力的贊美。可一旦真相被拆穿,她們又只能重回閨閣,也體現出現實生活中女性生存空間的狹窄。
另有一類女性身上充滿了俠義精神,她們比男性更勇敢,更有決斷。如《聊齋志異》中的《商三官》,身為男兒的兄長懦弱無能,身為女子的商三官卻為父親報了仇。蒲松齡說:“家有女豫讓而不知,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為人,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3]蒲松齡把商三官比作春秋時的俠客豫讓,又說即便荊軻在她面前也要羞愧,可見作者對她壯舉的高度贊賞。
俠士、義氣多是形容男性的詞語,《聊齋志異》卻塑造了閨中俠女的形象,這是難能可貴的。《夜雨秋燈錄》中也有這類描寫,最具代表性的是《閨俠》一篇,講述兩位女性在亂世中扶危濟困、互相救贖的故事。富家女鳳卿在一次外出路上遇到貧女湘蓮,兩人萍水相逢,鳳卿卻慷慨解囊救湘蓮一家于危困。危機解除后湘蓮一家生活日漸富裕,這時又遇到了落難的鳳卿,湘蓮當即分出一半家產贈給鳳卿,兩家自此成為至交。兩位女子身上體現出良善赤誠、慷慨助人的俠義精神。
三、異曲之音:女性類型與意圖之異
魯迅先生評價《夜雨秋燈錄》:“狐鬼漸稀,而煙花粉黛之事盛矣”[4]。之所以有這樣的觀點,其實是因不同版本的偏差造成的。申報館本《夜雨秋燈錄》發行后,贗本大行其道,在之后的《清代筆記叢刊》本和《筆記小說大觀》本中,也隱藏著托名而作的贗本,由于這些作品質量參差不齊,且多為狹邪之作,難免引起誤會。然而“狐鬼漸稀”也是事實,《夜雨秋燈錄》中的女性更多為人間女子,在刻畫女性形象方面,《夜雨秋燈錄》及《續錄》在繼承《聊齋志異》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
1.《聊齋》女性:狐鬼仙的非人類女性與男性幻想的滿足
談鬼說狐,以夢幻寓真實,是《聊齋志異》的一個顯著特點。“《聊齋志異》往往以非現實性的女性人物作為主題與價值觀的載體,或者用來提供奇幻的意緒和色彩。”[5]由此,在許多描寫愛情故事的篇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為突出。
作者有意將人的特質加在非人類的角色上,以達到藝術性的融合,最突出的一點便是打通現實與異界。《嬰寧》《翩翩》《公孫九娘》在刻畫異域空間時,從人類進入異界空間展開敘述,隨后借人物之口表明,生活在這里的女性為狐女、仙女、鬼女的身份,再用人間的禮節、座位的排列等方法,暗示在異域世界也存有等級秩序、群體意識、家族榮辱之類的觀念,從中可以窺見人類世界的影子。故事中的人物可以在不同空間穿梭,無形中破除了人與異界的隔閡,讓他們的交流具有真實性,也讓讀者感覺更真實。
與此同時,蒲松齡又不斷暗示故事的虛幻特征。例如《仙人島》《翩翩》中描繪的仙界風光、仙女演奏的風采,是在人間不可能見到的。《畫壁》中朱生遇到的少女,是由他的心境產生的夢境。“夢境作為一個超現實的空間,給了作者以相當的自由去擺脫現實世界時空的局限,因而可以‘時間倒錯敘事,在特定的虛幻空間內構思離奇魔幻的事件。”[6]然而,無論夢境多么令人向往,總有清醒的時刻。在蒲松齡筆下,道士或和尚一揮、一敲、一喊就能喚醒夢中人,夢醒時分幻境隨即破滅。作者用簡單的動作暗示在異域發生的一切都是虛無縹緲的,轉瞬就會消失,具有濃郁的夢幻色彩。《連城》展示的鬼蜮空間,雖然為連城和喬生最終相守創造了機會,然而,當現實中的矛盾無法得到解決時,人們往往寄希望于超現實的力量來緩解沖突。這種做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暫時緩和矛盾,但同時也向讀者傳遞了一種虛假的意識。原本存在的矛盾被華麗的幻想所替代,而讀者所感受到的滿足感,也僅僅是幻想。
2.《夜錄》女性:廣泛真實婦女群像圖與現實女性魅力的發掘
宣鼎在創作《夜雨秋燈錄》及《續錄》時,更加關注作品的真實性。作者往往將虛幻世界作為引子,讓人物在入夢與出夢之間,從第三視角對其進行審視然后獲得體悟,并起到反映現實的作用。
上至貴婦、下到普通女性,宣鼎都有所關注。這些女性雖然身份各異、社會地位懸殊,但在她們身上都閃耀出人性的光輝。這些女性可以分為兩大類:現實世界的女性和異域世界的女性。前者如《銀雁》中至純至孝的銀雁,是沒落富戶家的小姐;《龍梭三娘》中豪俠義氣的龍梭三娘,是蒙古的逃難女子;《雪里紅》中有勇有謀的薛一娘,最初是一名妓女;《卓二娘》中頭腦清醒的卓二娘,是出身平民的寡婦;《沉香街》中面甜心惡的素嬌,是貪財薄情的妓女。后者如《東鄰墓》中的女鬼多絡霞有情有義;《迦陵配》中的仙女巧巧足智多謀;《珊珊》中的虎女珊珊替父報恩等。此外,那些擔任次要角色的女性人物,她們或心地善良或個性暴戾,對于表現不同的人性也起到了關鍵作用。《盈盈》中的少女張盈盈不顧世俗眼光,大膽追求婚姻自由,最終和心上人劉鐘順利成婚;《谷惠兒》中的谷惠兒,用比武招親的方式挑選夫君,在找到中意的男子后主動放水,二人終成眷屬;《秦二官》中女藝人阿良的性格更加復雜,她主動追求愛情而不得,最終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最震撼人心的要數《麻瘋女邱麗玉》中的邱麗玉不愿將自己的病傳染給無辜之人,自己默默忍受多年,由于真誠感動天地病情得以病愈。這種凜然大義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情愛,在她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博大無私的愛。
從《聊齋志異》到《夜雨秋燈錄》,宣鼎立足于旁觀者的角度,將人物本身的自由活動呈現出來。在宣鼎筆下,女性形象更加立體飽滿,同時也暗示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四、《夜錄》與《聊齋》女性形象差異的原因
文人的創作離不開時代背景。蒲松齡和宣鼎處于兩種社會境況下,經歷不同的人生波折,因而形成的文學作品風格各異。從觀照自我意識到映射社會民生,這是文人的自覺,也是時代的選擇。
1.命運遭逢之變
蒲松齡生活在清順治、康熙年間,這一時期的社會環境較為安定。蒲松齡十九歲應童子試,連獲淄川縣、濟南府、山東道三個第一,但天不遂人愿,屢試不第后他接受了功名無望的現實,去私塾教書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坎坷多舛的命運,窮愁無聊的人生使蒲松齡一腔激情無從抒發,在世間難尋知己,只能發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憤慨又無奈的呼喊,借花妖狐魅,‘妄續幽冥之錄,抒發憤懣。”[7]受這一孤憤心態的驅動,在他親手構建的狐鬼花妖的世界中,困擾知識分子的難題得到解決,蒲松齡實現了人生的終極追求。
宣鼎童年時期的生活較為閑適,二十歲時養父母相繼離世,隨后遭逢戰亂荒年,接著入贅外祖家。接連的變故使他的內心嚴重受挫,由富到窮的經歷也讓他深有感觸。二十七歲時宣鼎選擇從軍,幾經生死回到上海,為了維持生計,三十一歲至四十歲時去山東做了幕僚,生活反而愈加困頓,晚年更是依靠朋友接濟才能勉強度日。“宣鼎一生恰好趕上一個空前絕后的封建末世兼亂世,帝國主義對滿目瘡痍的天朝上國進行著軍事、經濟、文化等多層次的入侵;太平天國起義帶來的震撼和戰亂,擾亂了社會各層的生活狀況。”[8]
《夜雨秋燈錄》及《續錄》就展示了這樣一幅晚清社會圖景:受到新思潮的沖擊,人們思想上的枷鎖變得松動,對物欲的追求攀升,道德標準卻不斷下滑。“‘驚盛世之秋,救衰世之敝的時代主題對宣鼎產生了直接影響,激起了他挽狂瀾于既倒的救世苦心,因而他把‘無語不關勸誡作為主要的創作目標,寓抒憤于勸誡中。”[7]由于深感國家到了危亡之時,宣鼎帶著個人良知與社會責任感,將封建倫理道德融入小說之中,希望通過文字能夠喚醒民眾。對蒲松齡和宣鼎來說,苦難似乎如影隨形,長期經受壓抑為宣鼎仿《聊齋》而作《夜錄》提供了契機。但二人又略有不同,前者更多是為了抒發孤憤,后者則趨向承擔社會責任的自覺。
2.婦女觀念之變
蒲松齡所處的時代,男尊女卑的觀念還十分嚴重,但在《俠女》《商三官》《霍女》等篇章中,他創造性地提出女性可以反抗,并為她們的反抗精神唱了贊歌。與此同時,蒲松齡又認為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對女性提出了諸多要求。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展示的婦女觀念是相當矛盾的,這一點從他的描述中可以明顯看出。
宣鼎對女性的刻畫主要集中在三方面:肯定女性對愛情的大膽追求、體現美好的道德品質、揭示封建社會女性的悲慘命運。在古代社會,女性對于自己的婚姻是沒有決定權的,但《盈盈》《谷惠兒》中的女性在追求自由愛情婚姻的路上,經過自己的勇敢抗爭,最終得以和心上人修成正果。宣鼎對這類女性的刻畫及肯定,實則是對男尊女卑傳統的反思與批判。小說在展現女性美好的道德品質時,書中的男性往往表現出懦弱、自私、迂腐的品質特征。如《珊珊》《雪里紅》的主人公雖是虎精和妓女,但在危急關頭總是她們挺身而出,而她們的丈夫卻只知道躲在女子背后尋求庇護,宣鼎從中看到了女性優于男性之處,并將其表現出來。在反映女性的命運握于他人之手時,纏足無疑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夜錄》及《續錄》中常用“蓮鉤”來比喻女性腳的秀美,宣鼎生動地再現了這一畫面:母親一邊流淚一邊為女兒裹腳,并認為世間最慘烈之聲是母親為女兒裹腳時發出的哭泣。由此他提出不必過分纏足、一味追求小腳的主張,這與當時社會審美相反,卻十分接近現代人的審美,是難能可貴的。宣鼎對女性的刻畫立足現實,因此顯得較為客觀理智,他的一些女性觀在當時來說也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五、結語
從《聊齋志異》到《夜雨秋燈錄》,不同時代的作家的創作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女子不應被囿于閨閣,而是要像男子一樣自由展現自己的才能,這樣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蒲松齡筆下的女性多為非現實的狐鬼花妖,她們的美好是作者對人間女性的美麗幻想,是作者在現實世界為自己所構造的幻影。而宣鼎筆下的女性除了少量的狐鬼,更多是現實世界中性格各異的女性人物,這些勇敢反叛封建社會父權、夫權的女性來自作者對男尊女卑傳統的反思與批判,是在作者經歷了社會動蕩,在新舊思潮的交互影響之下創作出來的。通過對兩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對比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聊齋志異》之后仿聊齋系列小說的發展歷程及其演變軌跡。同時,這也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評估此類小說的文學價值。
參考文獻
[1] 崔美榮,胡利民.《聊齋志異》仿書發展流變[J].蒲松齡研究,2007(1).
[2] 宣鼎.夜雨秋燈錄[M].恒鶴,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蒲松齡.聊齋志異[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4]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5] 王昕.選擇經典:清代文言小說七十年研究的線索與方法[J].文學遺產,2023(1).
[6] 姜克濱.論《聊齋志異》夢境敘事[J].蒲松齡研究,2020(3).
[7] 吳娜.宣鼎《夜雨秋燈錄》及《夜雨秋燈續錄》研究[D].蕪湖:安徽師范大學,2007.
[8] 胡芳.試論《夜雨秋燈錄》的末世風度[J].成功(教育),2007(12).
(責任編輯 羅芳)
作者簡介:楊睆,貴州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