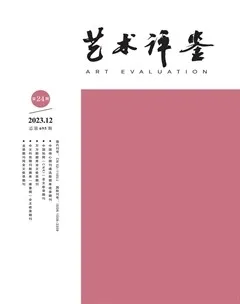古詩詞藝術歌曲《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音樂詩性探究
康晉源 唐凱瑞

【摘? ?要】《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代表作之一,其在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這首詞的文本細讀和音樂分析,主要探究其在文學和音樂藝術融合中的表現力,對詞中的意象、韻律、情感和哲思進行深入剖析,考察這首詞轉化的音樂語言,特別是在旋律的塑造、和聲的處理,以及節奏的安排上與詞中情感和意境相互呼應的聯覺反應,并對音樂創作與敘事層次,以及情感深度間的邏輯關系進行梳理,探討音樂與文學在藝術表達上的互補性。
【關鍵詞】李煜? 古詩詞藝術歌曲? 藝術表達? 意象分析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3)24-0069-06
在古詩詞藝術歌曲《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的創作與演繹過程中,傳統的詩詞敘事方式經歷了顯著轉變,展現了與傳統文學作品在表現形式上的根本差異。這種藝術形式不依賴于詳細的文字敘述或復雜的情節構造,而是通過音樂元素——包括旋律、節奏、和聲來傳達故事情節和情感流動。在此過程中,利用音樂的動態變化和歌詞的象征性質來展現情節發展和情感傳遞,這種敘事主要以隱喻和象征的形式呈現。旋律的多樣性揭示了情感的層次,節奏的變化模擬了故事發展的節奏,而和聲的調整則用于營造氛圍,共同創建了一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敘事環境。
敘事的構建依托于詞的文本內容和演唱者的表達。詩詞的文學性描述與演唱者的情感投入,結合其聲音的質感和演唱技術,共同創造出一個能夠激發聽眾情感共鳴的敘事框架。特別是在這首歌曲中,演唱者不僅要準確傳達歌詞的文字意義,而且要通過聲音的細微差別來描繪李煜詞中所蘊含的深層情感,使聽眾能夠深刻體會春天的流逝,以及無盡的哀愁。通過這種復合型的藝術手法,這種藝術形式在不直接敘述的情況下,成功傳達了豐富的故事情節和情感敘事,引領聽眾在音樂的引導下探索生命、家國和時間流逝等主題的深層含義。
一、情境遐想——詩詞內蘊解讀
(一)意象流轉與詩詞象征
李煜,南唐末代皇帝(937—978年),字重光,號鐘隱,在五代十國時期繼承皇位。面臨宋朝已確立的強勢局面,南唐的國力日漸衰弱。李煜在位期間,深感形勢之不利,遂在位十年之際,主動降低國家地位,改稱江南國主,以示對宋朝的臣服,寄希望于通過定期朝貢來維系國家的微弱生存。不幸的是,開寶七年(974年),宋朝發動軍事行動,由曹彬領軍南下,終于在次年攻占金陵,將李煜擄至汴京。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李煜悲劇結束其生命。李煜的文學成就尤以詞為最,其詞風格初期多反映宮廷生活之奢靡,后因國破家亡,作品風格轉為凄美哀怨,深刻反映了個人的身世與時代的沉痛。其代表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烏夜啼·昨夜風兼雨》等,展現了李煜作為“千古詞帝”的文學地位。除此之外,李煜還精于書法與繪畫,通曉音律,其詩文亦有較高成就,成為后世文人雅士所推崇的多才多藝的文化象征。
《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作于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初夏,是李煜在北宋都城汴梁城中的悼國之作,直抒胸懷,感情沉痛,屬于其晚期的創作作品。這一時期的作品多表達了他個人深切的身世感慨,以及對過往生活的懷念,情調更加凄涼和哀怨。
“臨江仙”為詞牌名,原為唐代教坊曲名,本首詞格二雙調,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五句,三平韻,李煜詞上下片第二句“蝶翻金粉雙飛”“望殘煙草低迷”,“望”字俱仄聲,“蝶”字、“輕”字、“煙”字俱平聲。本詞之上片,巧妙構筑了一幅春末獨處的憂愁畫卷。“櫻桃落盡春歸去”首句設景,不僅確立時空背景,亦透露出詞人內心的蕭索與不歸之意。“蝶翻金粉雙飛”之句逆用景物之歡快,反襯出詞人心中之孤寂與無奈。“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融合聽覺與視覺之雙重感官,深夜未眠的描繪,彰顯出詞人的愁緒紛擾、情懷怨恨。
李煜作為南唐末代君王,雖未能善治國政,但對于國家的衰亡與民眾之苦難,內心自有所感,卻又無力回天,櫻桃落盡及子規啼月暗含典故,寓意為:用櫻桃難獻宗廟、子規失國這兩個典故,隱喻著國家將亡與個人之哀傷,因此李煜借歷史典故以喻現實,以思婦之懷喻個人之憂愁①。詞中后繼兩句轉入內景,盡管時空轉移,思婦之悲愁仍難以驅散,眼中所見無不沾染上難以割舍的情感。
下片之起筆“別巷寂寥人散后”承接上片情緒,未言之愁已躍然紙上。“望殘煙草低迷”將“寂寥”賦予更具體、更生動的形象。“爐香閑裊鳳凰兒”由外及內,由遠及近,不僅描繪空室之寂靜,亦顯露詞人心中的迷惘與孤獨。“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中恨字貫穿全篇,成為詞意之關鍵。整篇詞作,景物描寫細膩而不失跳躍,情感表達雖直接卻不乏含蓄,構筑了一種虛實相生、內外相融的敘事結構。時空轉換處理自如、流暢,筆法靈動,喻象含蓄,直抒胸臆之余亦保持婉約之美,輕聲細訴之中蘊含著深沉的感情波動。
(二)自然與情感的交織
本文以李煜詞、時昊譜曲,以及李治昊配器的古詩詞藝術歌曲《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為研究對象。李煜巧妙地將自然景象與個人情感交織在一起,展現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這首詞不僅是對自然景象的描繪,而且是通過自然來抒發詞人的情感和哲思。在這種交織之中,自然不再是簡單的背景或裝飾,而是情感和思想的載體,與人的內心世界緊密相連。
除了暗含典故的“櫻桃落盡及子規啼月”外,這些自然界的各種元素,包括已經提到過的櫻桃、蝴蝶、夜月、殘煙等,都富有深刻的象征意義。櫻桃的凋零預示著春天結束,象征著美好時光的流逝和無常;蝴蝶雙飛則暗示著詞人對逝去美好的追憶和渴望;夜月和殘煙則增添了一層深沉的憂郁氛圍,象征著孤獨和思念。通過這些自然元素象征,李煜不僅表達了對過往美好時光的懷念,而且反映了對現實無奈和哀傷的深刻感受。
在音樂創作方面,這首作品的旋律、和聲與節奏的安排緊密地與文本中的情感和意境相呼應。從旋律來看,曲調以溫婉、抒情的線條為主,既反映了詞中的哀愁情緒,又能夠引發聽眾共鳴。從和聲處理來看,通過富有變化的和聲色彩增強音樂的表現力,使得音樂能夠更好地傳達詞中的情感層次和意境深度。從節奏來看,通過變化的節奏處理,展現出流動的時空感,使得音樂與詞中的意象和情感更加貼近,從而加深聽眾的情感體驗。
二、旋律情韻——音樂創作的詩性探究
(一)曲式和聲分析
在譜曲時,遵從該詞本身格二雙調的規制,后按照曲式劃分本首曲目是A+B的二部曲式結構,上片速度悠緩情緒憂慮,下片轉快情緒堅定。調性節拍為e小調4/4拍,曲目中多次出現同主音大小調的和聲結構。
曲式結構:A58=Int9+{[A9(a4+b5)+Re4+A19(a14+b15)]+Re4+B16(c8+d8)}+Coda7
第1~9小節是引子部分,以e自然小調色彩展開,和聲主要選用下屬功能組TSⅥ-D與S-D-T的正格進行,其中在第9小節的結尾解決則采用同主音大小調的和聲功能終止延后解決歸屬感,在聽覺方面設置期待。
譜例1:《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b樂句中16~18小節
A 樂段(9~18小節)開始部分和聲上沿用主題動機前奏走向,在b樂句(14~18小節)中低音不再是單純柱式和弦,增加了短琶音,并開始出現離調。其中16小節的和聲刻畫十分巧妙,此處先是以e小調持續進行,然后向三級進行離調G大調,采用常用于小調中的二級那不勒斯和弦 N7(b1sⅡ)營造憂慮氛圍,然后回到e自然小調sⅡ之后再次進行轉向e和聲小調,直到D7-t的完滿終止后通過Re進行A樂段重復,也就是A1樂段,至此格二雙調第一部分結束。A樂段與B樂段中Re部分不再沿用主題動機音型,而是采用高低聲部反向三連音的走向,在35小節出現標志音#c與#d標志調性離調向旋律小調。
B樂段(36~51小節)標志音還原,調性回歸e自然小調,伴奏聲部以主功能組的連續頓音預示主題開始轉變,由A樂段的憂慮吟誦轉向堅定,但此處編曲采用反其道而行的手法,大道至簡反而沒有太過復雜的和聲進行,每個樂節基本只采用一個和聲組別進行拆分,以c樂句(36~43小節)來說,和聲走向為t-tsⅥ-DⅦ-DtⅢ-s-t-s-K46-D-t,不難看出功能十分規整,此處的編排是為了突出旋律特點而將伴奏聲部置于強調調性的位置,d樂句和聲走向為t-tsⅥ-DⅦ-DtⅢ-s-t-tsⅥ-D-t,此處出現阻礙進行聽覺效果,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D-tsⅥ的阻礙終止,只是在聽覺上相似。
最后的Coda部分是d樂句的變化重復,區別主要體現為節奏與旋律,和聲的差異是回歸到主題動機上,呈現了首尾呼應的特點,最后的結尾沒有采用傳統的完滿終止,而是不斷出現下屬、屬與主和弦的六級和弦外音,最后的終止式也是采用主和弦加二級和弦外音,與之前提到的阻礙進行同樣使人產生意猶未盡之感。
(二)旋律情感分析
曲目開頭,主題動機前奏以力度稍弱的短琶音加三連音進行展開,預示著曲目哀怨婉轉的情感基調,伴奏聲部為柱式音程,旋律的流動主要依靠高聲部,旋律聲部在前奏主題當中多次出現伴奏聲部省略音,如在第1小節中,伴奏聲部下屬功能和弦的三音省略而出現于旋律聲部,第三小節sⅡ級和弦三音同樣省略,并出現于旋律聲部,這種處理方式是將下屬功能組營造的憐愁氛圍增強,從而在聽覺上凸顯主題。在第4小節活躍、快速地出現,伴奏聲部級進上行,整體情緒進行梯度攀升,節奏型發生改變,低聲部不再是單一的三連音向心環繞手法,開始進行大山型旋律型的和弦分解跳進,高音聲部以柱式三和弦下行射線型線條級進后,以同主音大小調的G大主功能結束,因為前部分一直以小調呈現,最后的同主音大小調稍顯突兀,給人以懸而未決之感。
A樂段開始的伴奏聲部再次以主題動機向心環繞展開的legato進行,人聲介入,旋律聲部以音節式即一字對一音的手法發展,旋律集中于中音區,以波浪式旋律音型發展,此處力度沒有過分強調,按照旋律走向自然流動,由于伴奏的連貫進行與人聲的音節式節奏線條的差異性,所以更加襯托出人聲旋律的沉重,將氛圍渲染得更加低沉。Re部分依舊是主題動機前奏以力度稍弱的短琶音加三連音進行,區別之處在于低音旋律不再是單一柱式和弦,而是采用分解上行和弦,并增加和弦外音的手法,使聽覺上更加飽滿。A1樂段是變化重復樂段,其與之前樂段差異主要體現為低音伴奏織體豐富,和弦出現離調。A1與B樂段的間奏與之前的差異體現為上下行旋律的逆行發展,35小節的情緒攀升。B樂段在旋律與詞的搭配中,不再是單一的音節式進行,而是選擇偷聲減字的創作手法,整體旋律線條拉長,一字對多音,音域攀升多集中于高音區,伴奏聲部不再以向心環繞三連音行進,而是改為低聲頓音加中聲柱式和弦,頓音的出現會使此部分的節奏感增強,聽覺上更加急促,力度也與之前的音樂發展出現顯著區別,不再是根據音高走向自然浮動,而是以ff強音直接展開,這種創作方法在如今很多古詩詞藝術歌曲中都有所體現,主要作用是先抑后揚,形成明顯的句讀間隙,使兩樂段間聯覺聽感涇渭分明。但曲目的旋律依舊以大山型線條為主,Coda部分是對d樂句的變化重復,rit的出現不僅預示著速度開始放慢,還可以預見情緒收束后的曲目終止時刻,最后的進行是以上行射線性旋律線條主音e2加自由演唱結束,在最后部分伴奏聲部再次以主題動機三連音呈現,首尾呼應。本曲通過精巧的動機開發與旋律線條的運用,從開頭的哀怨婉轉到中段的激情四溢,再到結尾的緩和收束,每個部分都通過獨特的和聲處理和節奏變化,巧妙地構建音樂情感弧線,展示了創作者對于音樂情感細膩的把握。
(三)演唱技巧分析
在演唱古詩詞藝術歌曲時,歌者需要對作品有深刻了解,才能更好地演繹。從作品的語言發音、情感內涵、旋律伴奏,再到演唱時氣息的運用、技術的細節和感情的把控等方面,由淺入深、從簡到繁、精細入微,一層一層全面剖析,力求完美表達與展示作品。《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作為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對于中文的咬字發音和字尾歸韻極為看重,考慮到歌者大部分母語為漢語,很多人會忽略中國歌曲的咬字,把日常說話習慣帶入歌唱中,正因如此,在演繹中文作品時要有意識地控制咬字,注意歸韻。以本首作品上闋第一句為例,“櫻桃落盡春歸去”中,平仄分明,“櫻”與“盡”的前后鼻音歸韻要格外注意,不可把“櫻”發成前鼻音。該句中多為“in”“ui”“ao”“wo”的歸韻,在歌唱中不同的韻母給歌者的反饋也大不相同,“in”和“ui”會給人聲音“向前”的感覺,而“ao”“wo”則反之。這就要求歌者在演唱時避免里出外進,做到字正腔圓,從發音這一根本問題上使歌曲整體聽覺更加生動和諧。
歌曲伊始,“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伴隨著伴奏緩緩道出。此處伴奏舒緩,三連音如潺潺溪水而來,開頭的情緒基調已經將歌者帶到一千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的心理世界。在演唱該句時,需要歌者融入伴奏提供的情緒,保持住氣息,將音量收小,控制語速的平緩,將哀傷的氛圍娓娓道來。“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該句刻畫了一幅獨處傷懷的落寞畫面,歌者演唱此處時需要更多的以氣帶聲,采用“半聲唱法”,把音色展現出柔軟朦朧的感覺,將心中的倀恨與無奈凸顯出來。“玉鉤”和“羅幕”在曲譜中用休止符斷開,歌者也要注意在此處將聲音斷干凈,可以更好地表達沉痛無力的情緒。作者在創作中將上闋反復,第二遍演唱時,注意與之前譜面的區別,情緒變化不大,但要一定程度上加強,上闋結尾“惆悵暮煙垂”需要將情緒加重,聲音要有一定的延續性,可以將“煙”“垂”兩字適當延長,增加情緒色彩,為下闋的情感做鋪墊。
上下闋的連接,伴奏織體以之前三連音為主轉換為以柱式和弦為主,旋律變得快速有力,情緒出現遞進。“別巷寂寥人散后,望殘煙草低迷”該句為情緒的迸發,歌者要結合詞作者李煜當時滿腔悲憤無處可發的悲痛之情,用聲音表達出來,此處聲音需要一定的力量感,仿佛將心中的悲憤發泄出去。緊接著“爐香閑裊鳳凰兒”又是情緒的再一次推進,這里要把控好氣息流出的速度,控制好音量,避免情緒激烈、氣息給得過多,或者聲帶閉合不夠而破音的情況出現。歌曲的最后,“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出現兩次,前一次為情緒迸發的收尾,凸顯出李煜心中無可奈何的憤恨,后一次出現與前面的情緒進行對比,此處伴奏由快轉慢,伴奏旋律零星的音符需要歌者將聲音塑造得更為細膩,歌者在此處要格外注意聲音的把控,“依依”兩字為全曲最高音,而情緒卻是整首作品的最低谷,“最高”和“最低”的融合要求歌者采用“高音弱唱”的方法,將情感烘托住。在唱這句結尾時一定要采用胸腹式呼吸,保證氣息穩定,身體略微前傾,讓音量漸漸變小,速度放慢,讓聲音自由延伸,維持內心的情緒,讓音色統一地保持到作品的最后,只有情感與技巧巧妙結合,方能更好地演繹作品。
三、詞曲交融——音樂與文學詮釋
在《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中,詞曲交融體現了一種“音文互譯”的藝術探索,即如何將文學作品的意境、情感,以及象征意象轉化為音樂語言。這一過程涉及多個層面的創造性轉換,包括意象的音樂化、情感的旋律化,以及意境的和聲化,展現了音樂與文學在藝術表達上的深度融合與互動。在將李煜詞作的意象轉化為音樂語言時,作曲家需要捕捉文本中的關鍵意象,且通過音樂元素的選擇與組合重新構建這些意象的音樂形態。例如,“櫻桃落盡春歸去”的落櫻意象,通過大山型的旋律線、減弱的音量,以及柔和的音色來表現,象征春天的消逝,以及櫻花的凋零。作曲家通過旋律的抑揚頓挫、節奏的流動性,以及和聲的色彩變化,從而表達和強化文本中的情感層次。例如,“惆悵暮煙垂”的情感,通過緩慢而深沉的旋律、低沉的音域,以及含蓄的和聲進行展現出一種淡淡的憂愁與無奈之情。
音樂中的和聲處理能夠獨立地傳達情感和構建意境。在詞曲交融的過程中,和聲的選擇和變化成為重塑文學意境的關鍵手段。通過和聲的豐富度、解決或未解決的張力,以及調性的明暗變化,音樂能夠營造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感、時間感,以及抽象的情感氛圍,從而使得文學作品的意境得以在音樂中得到新的詮釋和體現。
音樂與文學詮釋中,象征主義的轉化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的音樂中,作曲家不僅需要捕捉文本中的直接意象,而且需要深挖其背后的象征含義,并將這些象征意義轉化為音樂語言。櫻桃的落盡不僅象征著春天的結束,也隱喻著生命的無常和時間的流逝。這種哲理的深度可以通過模態轉換、調性的模糊處理或是不解決的和聲懸念來表達,從而引發聽者對于歷史更替和存在本質的深層次思考。
李煜的詞作在韻律上具有獨特的美感,這對音樂創作提出了挑戰:如何讓音樂節奏與文本的韻律相匹配,以及如何通過音樂節奏來復現詩詞的韻律美。在詞曲交融的實踐中,作曲家通過變化音樂的節奏模式、強調特定節奏點,或者采用不對稱節奏來模擬詩詞的韻腳和節奏感,從而使音樂與文本韻律實現和諧對話。這種節奏上的巧妙安排,不僅能夠增強音樂的表現力,而且能夠使聽者在無形中感受到詩詞的節奏美,以及音樂律動美的融合。在將李煜詞作的情緒轉化為音樂時,作曲家面臨著將復雜情緒層次和細膩情感轉化為音樂表達的挑戰。這要求作曲家不僅要準確捕捉詞中的主要情緒,而且要注意到其中的情緒轉變和微妙差異。通過動態的音量控制、音色的多樣化選擇,以及旋律線條的精細雕琢,音樂可以細膩地表現從憂愁到寂寞、從回憶到期盼的情緒轉變,使得聽者能夠在音樂中經歷一段情感旅程,深刻體驗詞中所蘊含的豐富情感和深邃哲思。
四、結語
在對《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這一古詩詞藝術歌曲的研究中,通過深入分析其曲式結構、旋律情感,以及演唱技巧,揭示了這一作品如何通過音樂的手法將古典詩詞的美感與現代聽眾的審美需求相結合,展現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價值。本曲采用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曲式設計,既保留了古詩詞的韻律美感,又融入了現代音樂的曲式變化,創造出一種新的聽覺體驗。作品的旋律線條流暢且富有表現力,既有古典音樂的嚴謹性,又不乏民族音樂的靈動和自然。在演唱中,要求歌者不僅要有扎實的音樂基礎,而且需要深刻理解詩歌的意境和情感,通過聲音的顏色、強弱、速度,以及呼吸的控制來傳達作品的情感深度。這種對演唱細節的要求,不僅展現了古詩詞藝術歌曲對表演者高度的技術和表達能力的需求,而且體現了音樂與詩歌深度結合的藝術追求。
《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中詞曲交融的實踐,展現了音樂與文學在藝術創作中的深度互動。這種跨藝術門類的融合不僅豐富了作品的表現層次,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理解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視角。通過音樂的視聽語言,李煜的詞作得以跨越時空限制,用一種更為直觀、感性的方式觸動現代聽眾的心弦,實現了文學與音樂共同的藝術追求,觸及人心深處,并引發人們共鳴,不僅展現了文學與音樂在藝術表達上的互補性和融合之美,也體現了作曲家在音樂創作中對文學作品深度理解和創造性轉化的能力。通過這種跨藝術融合,李煜的詞作以一種全新的藝術形態呈現,給現代聽眾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同時也為文學與音樂的跨領域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展示了藝術創作的可能性和價值深度。
參考文獻:
[1]李婭茜婭.古詩詞藝術歌曲《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演唱技巧與舞臺表演分析[D].保定:河北大學,2023年.
[2]王丹芹.探析聲樂演唱的情感體驗[J].中國民族博覽,2023(15):130-132.
[3]王仔.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鋼琴伴奏的演繹路徑[J].藝術研究,2023(01):123-125.
[4]顧瀟.詞的品格與曲的境界——有感于兩首《蝶戀花》古詩詞藝術歌曲[J].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22(04):160-164+166.
[5]陳剛毅,黃振洪.文化自信視域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在高校的傳承[J].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12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