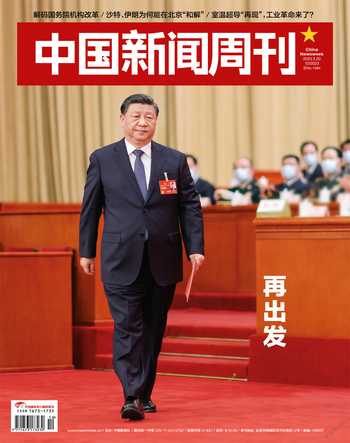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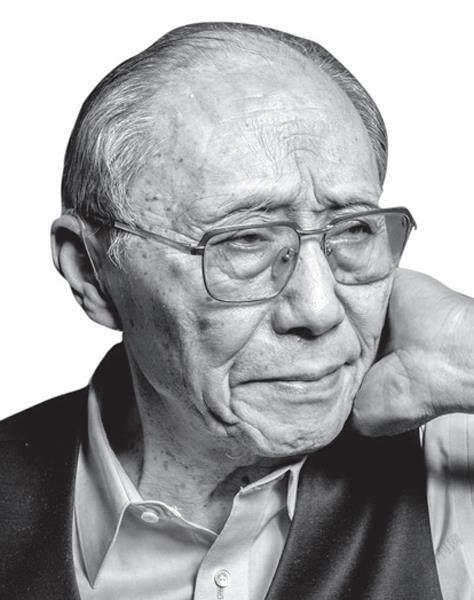
劉道玉
教育是周期最長的事業。孩童從開蒙到獲得博士學位,至少需要20年,這僅是從學習經歷來看。如果在要學業或事業上有所成就,成為“人物”,不到而立之年是難于圓夢的。
這一點古人是看得清的,反倒是當代中國人犯了糊涂。春秋時期,哲學家管仲在《管子》中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他深知育人要作為頭等大事抓好。清朝梁章鉅的《楹聯叢話》中說,“剛日讀經,柔日讀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百年”計代替管仲的“終身”計。
百年樹人,可作狹義和廣義理解。從狹義上說,專指人才的培育;而從廣義上,則泛指教育,以及與教育有關的學術著作、學風和學派。春秋時代,中國百家爭鳴,盛況空前。
明代,中國有《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傳世經典名著,也誕生了繼春秋之后最多的學派。可是清代以后,除了《紅樓夢》,中國鮮有傳世經典著作,我以為這與清朝的閉關自守和腐敗密切相關。
雖然歐美國家的文明史比中國要晚得多,但在文藝復興旗幟下,歐洲的教權走下神壇,人性得到解放,極大地推動了教育、科學、學派和哲學、藝術、文學的蓬勃發展,對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物理學上的哥本哈根學派,是1920年代以玻爾和海森堡為首的物理學家在哥本哈根創立的,其成員不乏30歲出頭的中堅力量。該學派有一張29人的合照,其中17人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玻爾創造的哥本哈根精神是:在切磋中提高,在爭論中完善,平等無拘束的討論和密切合作的學術氛圍。這無疑推動了量子力學的發展,也非常符合玻爾的個性與主張。
十多年前《紐約時報》曾評論說,歐洲若干學者堅信,千百年以來人類寫過具有永恒價值的處世智慧書:一是意大利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寫于1513年),二是中國孫武的《孫子兵法》(成書于公元前5世紀),三是西班牙格拉西安的《智慧書》(出版于1647年)。
法國思想啟蒙家盧梭曾說,馬基雅維利自稱是給君主講課,其實他是給人民講課。1530年代《君主論》風靡一時,1550年代被列為禁書,大約百余年后這本書又恢復名譽暢銷全球。在西方,這部書被認為是對政治斗爭獨到、最精辟和最誠實的“驗尸報告”。
這本16世紀初期的著作,撕破了人類道貌岸然的表象,揭示出人類心靈深處最卑鄙、最骯臟、最奸詐、最殘忍部分,有助于認識人性丑惡的一面。
此外,還有俄羅斯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被稱為“天書”,是20世紀百部英文小說之首。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于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獨》,風靡世界。
那么,為什么中國大師鮮見?我以為,原因就是,學風浮夸、造假泛濫,功利化日趨嚴重,沒有人再皓首窮經、清心寡欲地做學問了。前幾年,國內一些知名大學爭先宣布建成“世界一流水平大學”的計劃,難免有打腫臉充胖子的嫌疑。
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宣布退出世界一流大學排名的舉措,值得肯定,這是在反對商業化對大學的干擾和其錯誤導向。
但同時,其又宣稱這是與洋指標脫鉤,這又錯了。世界學術頂尖水平的大學,是有客觀標準的。說到洋指標,中國的大學本來就是舶來品,借鑒外國又有何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