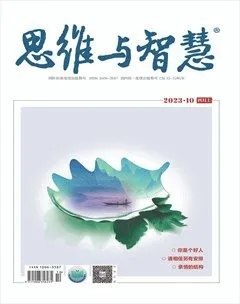土地里藏著快樂(lè)的種子
王國(guó)梁
回到老家,正趕上父母種菜。父母年紀(jì)大了,已經(jīng)有些年不種糧食了,每年種點(diǎn)小菜,算是與土地親近的方式。我也有很多年不干農(nóng)活了,土地上的勞動(dòng)早已生疏。
父親打發(fā)我用鎬頭翻地,這是最原始的勞作方式。因?yàn)榉N的菜很少,不值得用機(jī)器翻。再說(shuō)了,父母好像是刻意通過(guò)這種最簡(jiǎn)單的勞作方式,來(lái)溫習(xí)土地上的快樂(lè)。我這樣說(shuō)真不是矯情,干了一輩子農(nóng)活的人,徹底拋棄勞作會(huì)感到不舒服。
記得早年我是家里的主勞力,參加工作把家安在城里之后,每年耕種和收獲之季還會(huì)回家?guī)兔ΑT谔锢锔苫詈芾郏亍z草、施肥、灌溉、收割,都是重體力勞動(dòng)。我像父輩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有模有樣地?fù)]舞著農(nóng)具勞動(dòng)。一天下來(lái),累得胳膊腿發(fā)沉,覺(jué)得力氣都用盡了,就想躺到床上睡一大覺(jué)。吃過(guò)晚飯倒在床上,過(guò)不了一分鐘就能進(jìn)入深度睡眠,而且一覺(jué)睡到大天亮。
現(xiàn)在的很多年輕人都體會(huì)不到那種累的滋味了。故鄉(xiāng)的土地上,機(jī)械化進(jìn)程很迅速,僅僅十幾年的時(shí)間,幾乎所有的農(nóng)活都由機(jī)器代勞了。村里的年輕人把種田當(dāng)成了副業(yè),他們中很多人去城里或者附近的工廠打工,生活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改變了。在田里干活的勞累,對(duì)他們來(lái)說(shuō)也很遙遠(yuǎn)了。而那種累的滋味,卻是刻入了我的骨髓中的。尤其是在烈日下干活,筋骨仿佛每一刻都在被鍛打,不停地?fù)]汗如雨,感覺(jué)體內(nèi)的力量一點(diǎn)點(diǎn)往外掏,直到筋疲力盡。
但是說(shuō)實(shí)話,我并不覺(jué)得那種累有多痛苦。你體驗(yàn)過(guò)累過(guò)之后的徹底放松嗎?勞碌了一天,回到家休息的時(shí)候,心里是滿足和愉悅的。那種簡(jiǎn)單的幸福,特別純粹。我常常覺(jué)得自己就像土地上的小蟲(chóng)、飛鳥(niǎo)和小獸一樣,以最本真的狀態(tài)生存著。勞作覓食,心滿意足。沒(méi)有什么太過(guò)復(fù)雜的情緒,歡喜和滿足也是簡(jiǎn)單的。
當(dāng)下我在城里有一份在別人看來(lái)不錯(cuò)的工作,我的工作基本上不耗費(fèi)體力。一些協(xié)調(diào)組織工作,還有寫(xiě)寫(xiě)材料之類(lèi)的,就是我工作的全部。平時(shí)的生活中,我家務(wù)活做得不多,連輕體力勞動(dòng)也不大參與。可是我經(jīng)常有身心俱疲的感覺(jué),就是人們常說(shuō)的“心累”。心累的感覺(jué)很痛苦,明明什么都沒(méi)做,就是疲憊不堪。既然累,晚上該睡個(gè)好覺(jué)吧?可是,失眠成了家常便飯。我經(jīng)常躺在床上翻來(lái)覆去,到了黎明時(shí)分才勉強(qiáng)睡著。天亮后,疲憊絲毫沒(méi)有緩解,反而更累了。一天又一天,我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中。
我有時(shí)候特別懷念曾經(jīng)在土地上勞作的快樂(lè)。年輕時(shí)有幾年,我很鄙棄父輩的生存狀態(tài)。他們把一生都耗在土地上,在無(wú)望的勞作中周而復(fù)始,無(wú)所作為,庸碌至極。可是,最近幾年我忽然覺(jué)得他們的人生也是值得羨慕的。因?yàn)橥恋厣喜刂鞓?lè)的種子,他們通過(guò)勞作來(lái)?yè)焓皩儆谧约旱目鞓?lè)。他們一生可能也沒(méi)有多大的建樹(shù),但在簡(jiǎn)單的勞動(dòng)中享受著簡(jiǎn)單的幸福,生命狀態(tài)也是鮮活生動(dòng)的。
我有時(shí)也像隱居瓦爾登湖的梭羅一樣,思考人類(lèi)應(yīng)該有的生存狀態(tài)是什么。我已經(jīng)徹底理解了梭羅為何能在耕種中享受到人生樂(lè)趣。我想人類(lèi)不管如何發(fā)展,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如何迅猛,都應(yīng)該適當(dāng)回歸原始的生活方式,在土地上找尋快樂(lè)的種子。
幫父母種好了菜,那晚我睡在了老屋里。夜風(fēng)吹得窗子當(dāng)當(dāng)作響,我卻沉入了最安然的夢(mèng)里……
(編輯 高倩/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