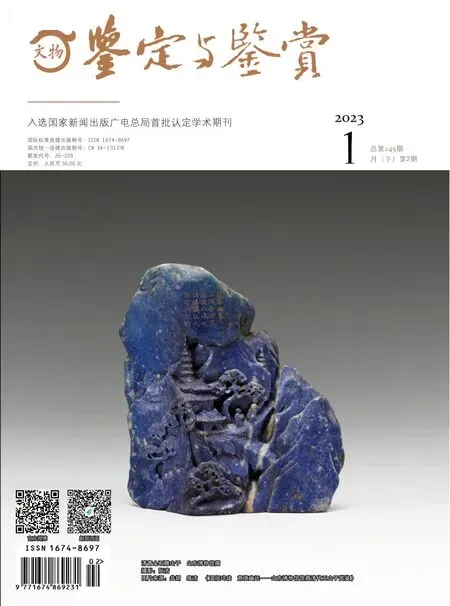湯斌《洛學編》對洛學史的譜系建構
劉文娟
(鄭州大學,河南 鄭州 450001)
明清交替之際,受明亡的沖擊,以學術為先導,掀起了一股反思浪潮。這一時期誕生了許多地域性學術史著作,其中湯斌所著《洛學編》作為洛學史梳理的開山之作,無疑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此時的學術史著作承襲于理學道統之說,在學術傾向上,或尊程朱,或尊陸王,抑或是折衷朱陸,以期客觀展現學術傾向。當下學術界同樣以此為切入點,以著作所選人物或是節選語錄作為判斷作者學術傾向的依據,往往容易陷入朱陸之辯、漢宋之爭的道統話題之內。本文擬對《洛學編》書中傳主排序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呈現清代學術史梳理的多種旨趣提供一個獨特視角。
1 《洛學編》傳主排序情況
與《洛學編》同一時期的著作還有《中州道學存真錄》《中州道學編》,其中后兩本在人物排序上大體相同,而《洛學編》卻顯現出很多獨特之處。
首先宋儒排序上,《中州道學存真錄》與《中州道學編》首列二程、邵雍;其次則是謝良佐、尹焞等人,他們作為程門四大弟子,思想各異,在歷來的學術史梳理中都是作為緊隨二程的存在,因此這兩本書如此排列自然無可厚非。但是湯斌《洛學編》一書中,將呂希哲列于四大弟子之前,則是罕見的排法。同樣的,湯斌的老師孫奇逢在《理學宗傳》一書中,雖首列楊時,但卻在楊時與謝良佐中相繼加入劉絢、李吁。最后在朱光庭的排序上,《中州道學存真錄》《中州道學編》都將其排列在四弟子之后,而《洛學編》中則稍顯靠后,與《理學宗傳》的安排同樣如出一轍。
在元儒的排序上,姚樞作為與趙復并駕齊驅的元代儒學開創性人物,也應當位列于元儒首位,《中州道學存真錄》《中州道學編》均是如此安排的。可在湯斌的《洛學編》中,則首列許衡,次列姚樞,許衡雖也與姚樞交好,二者也并無明確的師承關系,但據記載許衡“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注》”①,因此許衡常被視為是繼承姚樞而將元代儒學發揚光大的承上啟下式人物。湯斌的這種安排顯然與客觀的學術傳承不符,但是孫奇逢在《理學宗傳》的元儒考中,也并未將姚樞放置于首位,而是將與許衡齊名的劉因排在了姚樞之前,可見師徒二人都是有著自己的深刻用意。
在明儒譜系的安排上,曹端常被認為是明代理學開宗,正德時期,大司馬彭澤稱其為本朝理學之冠,可見曹端的學術地位不僅在明朝,或是在后代,都應該位列首位。劉宗泗在創作《中州道學存真錄》時,雖然在曹端之前加入李希顏,但是在曹端與薛瑄的地位對比上,仍舊將曹端位于首列,肯定了二者聞道先后的客觀事實,但在《洛學編》中,卻將薛瑄放置于曹端之前,這也是歷來學術界討論的熱點。有學者認為,此舉是受到從祀情況的影響,但是在《理學宗傳》一書中,孫奇逢盡管在曹端的傳記后刻意強調“舉從祀孔子廟庭”②,卻仍然將薛瑄放置于傳道十一子里,而將曹端放于明儒考中,顯然不完全是因其地位不同而做出的考量。
綜上,湯斌在《洛學編》一書的學人譜系建構中蘊含著自己不同的價值審視態度,并且在人物的強調上亦不完全是基于地位的考量,以提高洛學學術的分量。本文認為湯斌此種架構主要是受其老師孫奇逢道統思想的影響,以及對洛學學術概念的重新定義。
2 孫奇逢對湯斌的影響
孫奇逢在為《北學編》所作的序中說道:“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沐)梓于內黃,因于湯孔伯(斌)商搜《洛學》一編,與魏蓮陸(一鰲)商搜《北學》一編。”③可見《洛學編》一書是在老師孫奇逢的囑托下所編,在編寫的過程中,湯斌多次向老師請教義例、體裁以及學術思想等方面的指導。“承諭《洛學編》……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如有稿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④也就是說,在《洛學編》編纂的整個過程中,孫奇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么湯斌在傳主排序上的想法,自然也不能忽視老師孫奇逢對他的影響。而要了解孫奇逢具體的道統思想,就必須要從他的理學史著作《理學宗傳》入手。
孫奇逢在編寫《理學宗傳》時寫道:“如一身之有冠冕,一家之有大宗。一切上衣下裳,皆不敢出冠冕之上。一切小宗、別宗,皆不敢出大宗之上……至如堯大圣人而道其心,湯之大圣人而禮其心,孔子大圣人而矩其心,是謂理學。釋氏本心之學,不可謂之理學。曾以至善為宗,孟以性善為宗,周以純粹至善為宗,是謂傳宗。釋氏無善之宗,不可謂之傳宗。”⑤因此,孫奇逢就是要明確“宗”的概念,展現出學術流傳中有分有合、與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指導思想明顯不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并不執著于在“史”的角度下,還原學脈演變的真實情況。孫奇逢將大宗解釋為冠,而將小宗解釋為人的上衣下裳,目的就是要展現儒學道脈傳承中雖然各家學術主張各異但都不脫離于“道”的核心定義。一方面孫奇逢肯定各學派主張的不同,就具體而言,即便曹端是明代儒學的開創人物,但是其義理的深刻性與系統性都無法與薛瑄相比。曹端與薛瑄雖然在明代都被視作從祀孔廟的候選,但最終還是薛瑄成了明代從祀的第一人。曹端在當時經過多次奏疏請求,卻依然沒有得到認可,可見時人大都認同薛瑄的學術貢獻要大于曹端。因此,孫奇逢將薛瑄列入十一子之中,肯定了他在道脈傳承中的突出地位。劉因與之情況大致相同。許衡評論過“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⑥。在元代諸儒中,許衡對此三人評價如此之高,正是因為他們對道學做出了傳薪之功。
在這三人之中,孫奇逢尤為推崇劉因,正在于他展現了儒家士人“隱”的學術氣象。孫奇逢提到過一個劉因與許衡交談的舊例,“宋元之際,道在許子。當年與靜修同征,過容城,裔進止,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某亦出則道不尊。二子固各有所處也。”⑦在這一句中,劉因為自己的不出仕做了解釋,也就是出則道不尊。孫奇逢提到這個舊例顯然是頗為贊同劉因的。孫奇逢的這種認識延續了自唐宋道統說以來,道統主宰治統地位的內涵。君主雖然掌握著治理天下的大權,但是以何種方式治理天下,以何種形上架構來解釋世界運轉的本體依據,這個權力就落在了以劉因為代表的士人身上。就許衡和劉因二人來說,許衡的貢獻在于引導君主、傳衍儒學,促使整個社會回到儒家所搭建的倫理道德體系中。而劉因的貢獻則在于通過不出仕的態度,來讓君主對士子產生敬畏,同時看到士子所肩負的“理”的主宰力量。就這個層面來講,孫奇逢將劉因放在姚樞之前,顯然是有著學術貢獻的考量。對于孫奇逢《理學宗傳》中所體現的大宗、小宗的思想,學術界多有討論,但都集中在以十一子為主體的大宗和以諸儒考為主的小宗關系上,而未能看到這種主輔關系在各環節上的體現。從整本書來說,十一子是大宗,諸儒考是小宗;就時代關系來看,宋儒是大宗,漢儒是小宗;但就同一時代來說,貢獻突出者為大宗,學術闡發較為淺薄的為小宗,譬如元儒考,劉因即為大宗,姚樞等人就是相對的小宗。顯然孫奇逢的這種架構對湯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洛學編》中將許衡放置在姚樞之前,薛瑄放置于曹端之前,就是要明確洛學傳承中的主與輔。
另一方面,就孫奇逢個人的學術傾向來看,調和各家還是其思想主題。小宗雖然在地位上不同于大宗,但是在根本上卻是與大宗相等的。正如同宗法制下血脈是聯系各家的紐帶,孫奇逢一直強調的“本天”之學,就是各學派抽象的共同點。孫奇逢編纂《理學宗傳》之書雖然有過按學人的不同學術氣象而分門別類的想法,但最終還是選擇了以時間為標準來梳理學術傳承,顯然就是要刻意模糊各家在義理上的不同。倘若要完全反映儒學傳承中的差異性,那么在二程之后,應當是直接羅列及門四大弟子,但孫奇逢卻在這之間加入劉絢、李吁,就是要有意地打破二程弟子間差異性的聯系。當然,孫奇逢羅列的這兩人也不是隨意設置,謝良佐評價道:“向見程先生言《春秋》,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多。”⑧可見二人在程門地位之高。
除此以外,《宋史·道學傳》與《宋元學案》也將這二人放置于程門弟子中的靠前位置,足見二人的學術地位。但在湯斌《洛學編》中,卻并沒有完全沿襲孫奇逢的做法,而是先列程門四弟子中的尹焞、謝良佐、張繹,然后才是劉、李二人。可見湯斌也非完全附述師說,而是將《洛學編》創作的目的性融入其中。他的這種排列是為了更加明確二程以后的洛學道脈,強化洛學在源頭上與二程的關系,同時凸顯洛學的學術地位。
3 湯斌對洛學概念的重新定義
湯斌在《洛學編》傳主排序問題上也有著自己對洛學學術概念的重新考量。洛學在創建之初,是因二程講學于洛陽而得名,此時的“洛”字雖然是地域上的稱呼,但其實還是與二程的聯系更為緊密。洛學在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學術性,并非地域性。它表征著以天理為本體,由二程所搭建起來的學術體系。洛學在南宋時期得以發揚光大,真德秀說道:“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其子五峰、五峰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承得之為永嘉之學,其源示同自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宗。”⑨上述反映了洛學在南宋時期發揚光大的歷程。但是早期洛學的思想體系還稍顯簡略,二程弟子們對洛學含義的擴充,同時也是對洛學內涵的解構。隨著道南學、湖湘學等學派的興起,洛學一詞則漸漸失去了傳統的話語體系。梁山在《宋人“道學”與“理學”名稱考辨》一文中提到:“隨著洛學的薪火相傳,程門弟子在政壇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在他們口里‘道學’……那就是二程先生及其學問。”⑩也就是說,隨著道學名稱的逐漸形成,“道”也逐漸成了統攝各家的根本宗旨,洛學也逐漸內涵于道學的概念中,成為學術史脈絡下的一段歷史。湯斌作《洛學編》要擴充洛學中的學術內涵,就必須要打破這種學術框架,而代之以一種地域上的考量。
在《洛學編》中,湯斌將呂希哲放在二程和邵雍后的洛學第一后學的位置,這種變動是巨大的,至于其究竟是何目的,可以從《洛學編》對呂希哲的評價中體現出來。“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孫祖謙、祖儉,南渡后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首先從前一句來看,湯斌強調呂希哲是二程之后,首以師禮的學人地位,這與尹焞、謝良佐的排列目的相同,均是要凸顯洛學在源頭上與理學開宗人物二程的密切聯系。但是至于為何要將呂希哲放在尹、謝二人之前,可以從后一句看出。隨著朱子學的發展興盛,也標志著理學發展為儒學正統。呂祖謙提出的中原文獻之傳,除了作為南宋與金朝對峙的理論依據外,也成了儒學內部道學正統的代名詞。宋金對峙之時,南宋示弱,不得不削去帝號,尊金朝為正統。金朝作為華夏正統,自然也成為儒家文化的主導。因此,呂祖謙提到:“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之而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逾嶺如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和,遂定師生之分。于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歷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殊;以踐履為實,而刊繁文之枝葉。……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呂祖謙認為他的伯祖呂本中繼承了儒學的正統,以此來展示南宋對于文化正統的繼承性。呂祖謙的這種表述,不僅是他自己單方面的宣稱,同時也得到當時士人的認可。
隨著道學名稱的逐漸確立,中原文獻之傳衍也成了道統的一部分。后來隨著朱熹對理學的集大成,理學逐漸成了儒學在宋明時期的代名詞,朱熹也儼然以道統的繼承者自居。那么朱熹所繼承的道統,就不再是呂祖謙等人所談論的儒學學統,而是《伊洛淵源錄》道學的譜系傳承。在這種情況下,結合之前所討論洛學概念的演變,呂祖謙所提到的中原文獻之傳也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洛學在儒學發展演變中的重要地位。經過這種解釋,我們可以明確湯斌何以將呂希哲放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正是因為以呂希哲為代表的呂氏家族在成為儒學學脈傳承的同時也緊密地聯系了洛學與道統以及洛學與儒學的關系。
同時湯斌弱化洛學的學術概念,也就意味著他不主張反映洛學的具體學術思想,不強調洛學后學中各式各樣的思想傾向。而是將洛學概念逐漸變成中州學術概念,將反映中州學術的學術思辨性轉變成中州學術的傳承性,這也是湯斌將許衡放置于姚樞之前、薛瑄放置于曹端之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這里,湯斌既是繼承了孫奇逢大宗、小宗的內涵,同時也將此作為自己搭建洛學傳承的理論內涵。二程、許衡、薛瑄,儼然構成了一條道統傳承的學術譜系。這幾人既是各個時代理學的開宗人物,同時也是理學傳承的關鍵節點。這條主線無疑是湯斌在創作《洛學編》的過程中暗含的一種價值取向,也就是要通過這些主要學人地位的強調,將中州地區的學術傳承與道統相聯系。這一方面展現了中州地區濃厚的學風及學人氣象,同時也強調了中州學術的代表性與主體性。
4 總結
學術史書寫中的傳主排序是反映作者思想的重要標識,但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研究視角。湯斌受其師孫奇逢思想的影響,同時也為凸顯洛學概念中的地域色彩,重新為程門弟子、元儒中的姚樞、許衡以及明儒中的曹端、薛瑄規劃排序,反映了他在創作《洛學編》的過程中強化中州學術概念,強調地域學術傳承性,強調洛學在儒學發展演變中的重要地位的編寫目的。這無疑在原來以調和朱陸、漢宋等方面的舊視角上開辟了一個新的切入點。同時也為我們以后以學人排序問題來作為觀察學者學術思想視角的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釋
①⑧湯斌.洛學編[M].吳元炳重刻本.1876(光緒二年).
②孫奇逢.孫奇逢集(上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038.
③魏一鰲.北學編[M].重刊本.1868(同治七年).
④湯斌.湯斌集(上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61.
⑤孫奇逢.孫奇逢集(上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332.
⑥孫奇逢.孫奇逢集(上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404.
⑦孫奇逢.孫奇逢集(上冊)[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243.
⑨真德秀.西山讀書記[M]//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筆記:第十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8:415.
⑩梁山.宋人“道學”與“理學”名稱考辨[J].華夏文化,2017(2):37-39.
?呂祖謙,黃靈庚,吳戰壘.呂祖謙全集(第1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