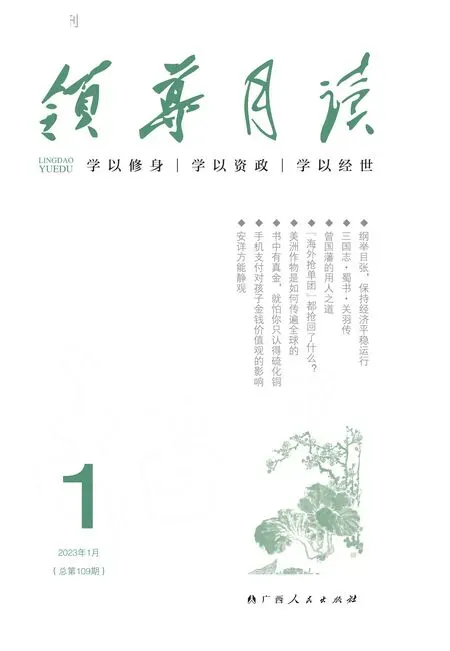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舞
宮玉振
戰略從出現那天起,就是為了給組織提供一個相對確定的未來。但是戰略的環境永遠充滿了不確定性。戰略其實就是必須在確定與不確定的悖論中,去做出關系到未來組織命運的大的投入的決策藝術。
克勞塞維茨說過一段經典的話:“戰爭是充滿偶然性的領域,人類的任何活動都不像戰爭那樣給偶然性這個不速之客留有這樣廣闊的活動天地,因為沒有一種活動像戰爭這樣從各方面和偶然性經常接觸。偶然性會增加各種情況的不確定性,并擾亂事件的進程。”
如果認為有了戰略計劃,事態就會按照你的計劃發展下去,那就大錯特錯。意外和不確定性是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你不可能通過你的計劃就清除掉所有的不確定性。沒有一場仗會從頭到尾完全按照你的設想去打。一定會有太多的事情讓你措手不及,你必須學會面對各種各樣的意外事件。不要僵硬地堅持最早確定的路線。不要把最早的戰略計劃看成是神圣不可挑戰的東西。老毛奇曾經講:“只有門外漢才相信,在一次戰局中,一個事先決定的、考慮到所有細節、直到戰局結束的思想,能夠自始至終地加以貫徹。”
戰略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在你大致的戰略框架指導之下的不斷探索、不斷嘗試、不斷明確的過程,而探索和嘗試的過程必然是不斷試錯和修正的過程。
商業世界也是如此。創業學家杰弗里·蒂蒙斯在談到創業時曾經說:“所有的計劃書在打印出來那一刻就已經作廢。”不只是創業,即使是成熟的企業也是如此。美國《商業周刊》的一篇文章也說:“由計劃人員制定的、想象中非常完美的策劃案,只有很少數得到了成功的貫徹”。
本田摩托車在進軍美國市場時,曾對美國市場的特點進行過周密分析,結論是美國人的消費習慣是“更大、更奢華”,據此本田制訂了以重型摩托車為主打產品的銷售計劃。盡管同時也推出了輕型摩托車,但本田認為這種產品并不適合美國市場。沒想到,本田重型摩托車的銷售業績非常糟糕,市場對這一產品的反應極為冷淡。就在這時,本田銷售人員在大街上跑來跑去時所騎的輕型摩托車,卻引起了美國人的注意,本田接到了著名的連鎖超市西爾斯的訂貨電話。本田開始十分猶豫,擔心輕型摩托車的銷售會傷害公司在重型摩托車市場的形象。然而在重型摩托車打不開市場的情況下,本田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放棄了原定的計劃,改為推出輕型摩托車。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輕型摩托車在美國大受歡迎。喜出望外的本田順勢而為,將重心轉到輕型摩托車市場,并圍繞輕型摩托車做文章,推出了一系列的營銷手段。到1964年,美國市場上每賣出兩輛摩托車,就有一輛是本田摩托車。
明茨伯格曾經警告過戰略決策者:“在各種因素不確定期間,危險并不是來自缺乏明確的戰略,恰恰相反,它來自戰略過早地被敲定。即使在不確定成分很小的情況下,仍然要注意明確表達戰略存在的危險。明確的戰略可能使組織只重視前進的方向,忘記了觀察周圍環境。因此,在需要進行戰略變化時,明確的戰略又妨礙了戰略的變化。換句話說就是,戰略家能夠把握現在,但不一定能永遠把握將來。戰略越是表達得明確,越容易在組織的習慣和戰略家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事實上,戰略的明確表述將封閉戰略,產生一種抵觸變化的力量。”
所以,你最好把你早期的戰略看成是一個概率事件。在事先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在一個相對限定的大的方向上,不斷地去試錯和校正。大的方向你不要錯,關鍵的決策要做對,具體的路線,你只能根據你的戰略意圖和你對形勢的判斷,提出一個大致的假設,有目的地嘗試,分析你的嘗試帶來的反饋不斷修正你的假設;然后再根據你對新形勢的認知和假設,去做新的試探。如此往復,不斷調整你的路線,不斷校正你的方向。
在這樣的戰略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不再是你最初做出了什么樣的判斷,制訂了什么樣的計劃。任何初始的判斷和計劃都有可能被不斷修正甚至推翻。
那些偉大決策的背后,往往是無數次錯誤換來的。所以,你要鼓勵試錯,接受犯錯,甚至要接受失敗。任正非在與華為研發人員座談時講過一段話:“我們對未來的實現形式可以有多種假設、多種技術方案,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逐步傾向哪一種方案,我們再加大這方面的投入,逐步縮小其他方案的投人。且不必關閉其他方案,可以繼續深入研究,失敗的項目也培養了人才。”
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戰略一般會經歷嘗試期、形成期、發展期這樣幾個階段。在嘗試期,你的戰略一定要有一種開放的結構,這樣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未來出現的一切可能的機會。一旦發現大概某個方向是對的,你就要開始逐步收斂到這個方向上去。一旦你確定了戰略方向,就要果斷地加大投入,乃至集中你全部的資源,全力以赴,通過強有力的執行,取得戰略性的突破,迎來最終的柳暗花明。
環境永遠是動態的、不確定的。即使在你已經形成了相對明確的戰略的時候,你還是不要忘了觀察周圍環境。這就要求競爭者要把不確定性作為常態,并且還要主動地去參與塑造未來和創造未來。
所謂的“因利制權”,核心就是要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舞,并把你的戰略變成利用不確定性來創造機會的過程。讓不確定性變成你的朋友。這樣,你就可以成為不確定環境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