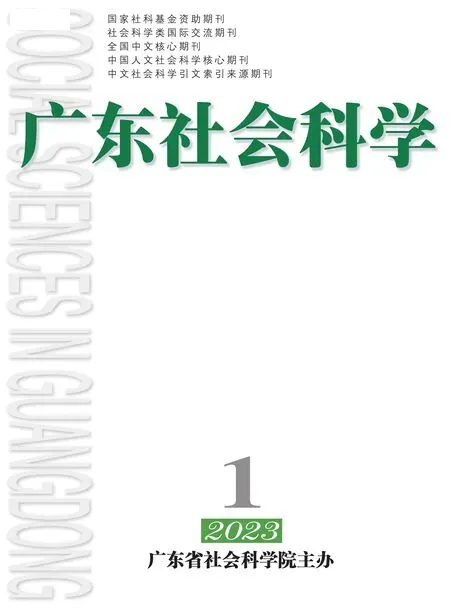從“語言”到“圖像”
——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機制與文化反思*
鄧依晴 程廣云
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的快速推進,數字技術突破性地將人類社會的表意圖譜進一步在視覺經驗處集結,推動視覺樣態從靜態圖像到動態影像的摹狀轉換,人類的生存世界被視覺機器編碼成像,視覺產物作為物質性力量的存在正創造著“景觀的積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從“語言轉向”到“圖像轉向”,傳統“左圖右史”的語圖關系發生了新的變革,圖像敘事打破語言敘事的空間壁壘,視覺圖像以其面向能力不斷擴展自身敘事空間的現象學深度。視覺圖像以強大的空間現實化力量滲入到身體、話語、體制之中,深刻改變了人們的認知和行為,使人們更加依賴視覺圖像來理解世界。視覺圖像對意義的直觀性承載與傳播改變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主客體經驗關系,由圖像主導的視覺機制為主流價值觀認同開辟了新的路徑,聯動著“觀看”與“被觀看”的視覺圖像日漸成為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表意樣態。如何破譯圖像的價值密碼就成為展開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機制研究的基本線索。
一、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敘事形態轉變
在人類敘事史上語言和圖像沿著兩個不同的敘事邏輯展開,語言敘事乃是“實指性”的,遵循的是事物的“質”,圖像敘事乃是“描繪性”的,依據的是事物的“形”,二者共同繪制了一幅交織權力和意義的價值圖譜。語言敘事與圖像敘事的生發與進化伴隨著人類社會的成長變遷。語言與圖像分別在同一時空發展著自身特有的敘事功能,語圖關系在原始社會表現為語圖一體——“以圖達意”敘事,在文本時代呈現出語圖分體——“以字言說”敘事,經由載體的發展變化呈現出語圖合體——“語圖互文”敘事。晚近以來,動態的圖像敘事正以壓倒性的態勢沖擊著傳統的語言敘事規則,然而語言敘事并未就此終結千年以來的統治,圖像敘事也并未走上神壇,圖像敘事在大眾社會的深處積聚力量。圖像敘事改變個體在語言敘事中養成的抽象思維邏輯,形成的觀看認知邏輯作為認識世界的方式進入到主流價值觀的視野。圖像敘事的興發適應了主流價值觀認同與直觀形象相關聯的現實需要,并推動主流價值觀認同從語言敘事轉向圖像敘事。
在前現代社會,圖像和語言同源共存,在相互交錯中發展出了各自的敘事方式,并確立起各自的表意角色。身份共同體通過對圖像或語言文字的控制,強化禮俗觀念、宗教信仰、社會認同,衍生出以“人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群體本位生存形態。圖像是古老的表意符號和認知形式,原始先民通過圖像描繪或記錄所見之景象,圖像敘事諸如原始巖畫、圖騰符號、器物紋飾等寄托著原始先民的審美心理和價值觀念,大體呈現出對自然整體性的、實用性的、神秘性的原初認知。隨著人類的目光由自然轉向社會,固然圖像敘事因模仿機制先天具有隱喻性和想象性優勢,但是圖像敘事卻無法凝聚日益抽象化的社會思想體系。因此,語言敘事和圖像敘事的分離開啟了人類表意史上第一次分離,語言敘事逐漸取代圖像敘事上升為主要的文化敘事形態,最終形成以語言敘事為典范的文化表意體系。“文化的歷史部分是圖像與語言符號爭奪主導位置的漫長斗爭的歷史,每一個都聲稱自身對‘自然’的專利權。有些時候,這場斗爭似乎以開放邊界上的一種自由交換關系結束;而在另一些時候,邊界消除了,各自相安無事。”①[美]W.J.T.米歇爾:《圖像學:形象、文本、意識形態》,陳永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47頁。在某種意義上講,一部文化表意史就是一部語言和圖像的張力史。圖像敘事雖是表意系統的原點和母體,但經歷“語圖分體”②趙憲章:《文學和圖像關系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江海學刊》2010年第1期,第187頁。的洗練之后,語言敘事的能力和范圍顯著拓展與深化,最終獲得表意世界的主角地位,而圖像敘事則下降為表意世界的配角。
在現代社會,圖像敘事在“語圖糾纏”中開始上升,借助現代媒介技術完成圖像敘事的現代性轉變,營造出語圖“一體化”的視覺場域。“物的依賴關系”將人從對自然共同體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頁。在資本主導的現代社會,資本的增殖邏輯推動技術的革新與擴散,從攝影術和印刷術等復制技術的誕生,到電影和電視等動態媒介的呈現,再到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變革,都直接加速了傳統圖像敘事的現代性轉變。技術的變革帶來了圖像的解放,圖像敘事開始突破語言敘事的藩籬,人們不再慣性地通過語言文字獲取知識、傳遞信息、建構意義,而是憑借視覺經驗捕捉圖像所蘊涵的意義。圖像敘事改變了先前自上而下的敘事模式,將言說和表達的權力下放,釋放了表征的自由空間。現代視覺技術造就了形象被大量復制的可能性,“視覺圖像以典范傳播媒介的身份取得了進入現代表征世界的入場資格,憑依技術與藝術一體化的運作圖式與表征優勢,視覺媒介接管乃至替代了主體認知世界的文化感官進而獲取了不可言喻的表征自由,在拓展社會主體視覺感官經驗的同時從事著社會結構的再建構。”①張偉:《從“技術驅遣”到“體制建構”——現代視覺傳媒藝術的權力運作與敘事策略》,《現代傳播》2016年第5期,第94頁。視覺圖像憑借技術力量實現對價值的另一種書寫,同時也完成對價值的另一種再造。視覺圖像“更像是一種變得很有效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通過物質表達的世界觀。這是一個客觀化的世界視覺。”②[法]居伊·徳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頁。現代資本邏輯征用視覺圖像來搭建自身符號結構,通過圖像與資本的合謀實現對表意的操持和編碼,營造符合資本邏輯的動感時尚表意樣式,來傳遞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文化邏輯與價值觀念。合而言之,立足于資本和技術的增殖邏輯,為現代主體提供了酣暢淋漓的視覺快感,圖像敘事在將符號生產與圖像消費全面推廣到各個場域的同時,也將其承載的價值觀撒播到場域的各個角落之中。
現代社會繁榮的視覺景觀背后醞釀了語圖關系的新的裂變,視覺景觀的支配原則不再是現實原則,而是模擬原則,語圖關系在仿像化和擬象化的彌漫中變得斑駁迷離。當現代人類開始意識到自身被物化的枷鎖束縛時,卻發現又戴上了仿像化和擬象化的鐐銬。“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積聚(accumulation de spectacles)。直接經歷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了一種表現(représentation)。”③[法]居伊·徳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第3頁。就這樣,能指擠壓所指,表現勝過現實,表象超越存在,人們更加偏愛視覺圖像而不是語言文字,圖像敘事對自身的增殖和對本原的僭越,覆蓋了語言敘事的還原和解釋,圖像敘事促成了效率至上、感官享受的“圖像化生存”現狀。從此,感性世界被人們選擇的凌駕于世界之上的視覺圖像所替代,蕓蕓眾生被整合進資本邏輯主導的視覺帝國,在圖像、資本、技術的結合中制造出仿像和擬象來控制思想,擺布意義,奴役現實。在現代視覺社會中,主流價值觀認同衍化為視覺圖像的鏈動過程,主流價值觀認同的經典“涵詠”之法已經不再,直觀可感的視覺圖像將大眾招攬進自身的表意場取得了主流價值觀表達的優先權,由視覺圖像呈現的形象以其在場性的體驗將大眾規制于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框架之中。在這一過程中,圖像敘事建構自身的表意邏輯,不斷充盈和豐滿其價值王國,在延展敘事空間的操作中溢出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增殖效應,完成語言敘事所無法達到的主流價值觀認同的空間正義架構。同時,也需要立足于人類本真的現實世界對圖像敘事做出反思,針對圖像敘事的局限性,將語言敘事的理性認知編入圖像敘事中,增強視覺圖像的敘事深度,在視覺的認知意義上完成主流價值觀的認同。合而言之,收緊圖像和語言的空間間距,在語言的認知邏輯和圖像的形象邏輯共時呈現、遙相映襯、彼此交錯中達成主流價值觀的認同。
二、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表征結構
在現代視覺社會中,正在印證W.J.T.米切爾斷言的“圖像轉向”所發出的明確信號,“話語與‘可見’之間、可眼見的與可言說的之間的裂痕,并將這種裂痕作為現代性‘視覺制度’(scopic regimes)中的關鍵斷層線。”①[美]W.J.T.米切爾:《圖像理論》,蘭麗英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5頁。面對圖像世界的興起,主流價值觀認同必須有新的思路,主流價值觀認同面對的不再是被描寫的世界,而是被表征的世界,因此,主流價值觀認同是通過視覺圖像對現實世界的再現來實現的,是在視覺圖像的能指和所指的視覺表征運作來實現的,是在圖像生產者編碼和圖像觀看者解碼的視覺交流運作來實現的。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表征要素包括:生產者,觀看者,能指,所指等。“W.J.T.米歇爾將一個表征體系設想為兩個對角線的四邊形,一條線連接能指(signifier)和所指(object),另外一條線則把表征的生產者(maker)和觀看者(viewer)連接起來。連接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軸線叫做表征軸,而連接表征生產者和觀看者之間的軸線叫做交流軸。”②Ken Smith,Sandra Moriarty,Gretchen Barbatsis,Keith Kenney,Handbook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ory,Methods,and Media.Mahwah,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2005,p.100.連接能指與所指的表征軸構成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表征空間,圖像能指構成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可感具象,圖像所指構成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抽象概念,在能指與所指的適切表征的最基本層面還原出主流價值觀的意義裁定。連接生產者與觀看者的交流軸構成主流價值觀認同的“交流場”,圖像生產者賦予圖像以意義,圖像觀看者基于在場情景對圖像意義做出詮釋,圖像意義在生產者和觀看者之間流動,視覺圖像所蘊涵的主流價值觀就在生產者和觀看者的目光交織的“交流場”中得以生成。
主流價值觀認同通過連接能指和所指的表征軸,搭建起自身同構性的視覺表征空間。圖像符號的能指和所指構成視覺表征體系的表征軸,能指指向圖像符號在心理所形成的表象,通過對主流價值觀的具象化處理,實現主流價值觀的直觀可感,更能為受眾所接受和認同。所指指向圖像符號蘊涵的意義,經過對承載主流價值觀的意象進行反思,內化為精神理念,主流價值觀就會化作一種無意識結構從視覺圖像中浮現。能指經過由外向內的客體主體化過程,所指經過由內向外的主體客體化過程,在主客體交融中實現視覺圖像的能指和所指的契合,順利達成主流價值觀的認同。主流價值觀依托能指層面流行與傳播,語言和圖像構成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兩種不同思維路徑。語言中的能指形象,用類比性和比喻性等修辭話語刻畫涵義,這就是關于想象的語言藝術。圖像中的能指形象,用圖畫隱喻描寫認知和意指鏈,這就是以圖像呈現意義的視覺藝術。如果說語言的能指是命題投射在邏輯空間的印記,那么圖像的能指就是命題投射在心理世界的表象。能指從語言中的形象到圖像中的形象,意味著主流價值觀從理念世界中的抽象概念轉變為商品世界中的圖像拜物教。這就是文本世界的主流價值觀從抽象到具體的再生產過程。主流價值觀在所指層面的呈現,語言和圖像構成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兩種不同意義模式。語言的所指不在于語言的辭典意義,而在于語言的語境意義。圖像的所指不在于圖像符號本身,而在于圖像符號背后隱含的意義。所指從語言承載轉向圖像承載,就意味著主流價值觀從本體世界的抽象概念轉變為現象世界的直觀形象。這樣,所指從語言的情景性走向圖像的隱喻性,主流價值觀就被“視覺圖像”的光暈所籠罩,從而完成對感官世界的占領。語言能指與所指關系的“任意”使語言符號形成相對穩定的意義,圖像能指和所指關系的“相似”促使現實被轉化為各種“漂浮不定的符號”,“建立在聯想基礎上的所指脫離不了對能指‘原型’間連不斷的‘駐足’與‘凝視’,而能指與所指之間這種聯想式認知自然造成了圖像意指的迂回式再現,增強了圖像意義的不穩定性。”①張偉:《符號、辭格與語境——圖像修辭的現代圖式及其意指邏輯》,《社會科學》2020年第8期,第174—175頁。圖像符號意指的相似性極易引起共鳴效應,能夠促使人們形成對意義內容的認同,但圖像意義的不穩定性切割了完整的敘事空間,致使人們在做出關于意義和價值的判斷時,對事實進行碎片化、主觀化、虛無化的處理,對圖像符號不恰當的處理弱化了主流價值觀的塑造和傳播。
主流價值觀認同通過連接生產者(編碼者)和觀看者(解碼者)的交流軸,建構起自身整合性的視覺交流場。圖像符號的生產者和觀看者構成視覺表征的交流軸,視覺圖像的意義生成有賴于以符碼為中介的生產者和觀看者的對話交流,在生產者的編碼和觀看者解碼中實現知識創新、價值創造、意義建構。“在這個信息產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滿足一個‘需要’或者付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須被用作一個有意義的話語,被從意義上解碼。就是這組已解碼的意義‘產生效果’、發生影響、取悅于人、引導或者行為結果。”②[英]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47—348頁。也就是說,意義并不是編碼者“生產”的,而是解碼者“再生產”的,即在編碼者和解碼者的主體間性的互文中重構了意義。基于視覺機制的生產者與觀看者的對話交流構成主流價值觀傳播的新維度,深刻影響著大眾對主流價值觀的理解與認同。生產者對主流價值觀進行信息建構和符碼化,同時也會把自身的生存經驗、知識結構、價值觀念等投射到視覺圖像之上,或將圖像符號主導輸出,或使圖像符號“自然化”,或推進圖像符號兼收并蓄,無論何種圖像符號的生產模式,都是借助圖像符號將生產者自身價值取向寫入觀看者精神世界。當視覺圖像從生產環節進入觀看環節,意義的主導權從編碼者流向受眾,編碼者隨即失去了對意義的絕對控制權,解碼者對圖像符號的解碼受多種結構性因素影響,必然產生“哈姆雷特”效應。觀看者對承載主流價值觀的視覺圖像的進行解碼,視覺圖像的意義對解碼者而言既是開放的又是受到限制的。受眾通過視覺圖像的修辭直達適切的意義,即解碼者全然根據編碼者明確的規則,解讀出編碼者預先嵌入的主導性意義。受眾對視覺圖像編碼者的設計意義持否定態度,即解碼者打破編碼者的符碼規則,將圖像信息進行對抗性再造。受眾對視覺圖像攜帶的主旨既有所認同又有所保留,即解碼者與編碼者雙方意見基本相容,同時解碼者能夠對視覺圖像進行協調性解碼。在生產者和觀看者的交流對話中,對視覺圖像的編碼和解碼并不構成尖銳的二元對立,而是呈現為互補轉化的形式。編碼者將解碼者召喚為主體,解碼者將編碼者召喚為主體,正是在編碼者和解碼者的主體間性的對話中創造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世界。
三、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個體視覺素養
“圖像轉向”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顯性事件,物化存在的“表象化”呈現構成了對個體的全域包圍。個體視覺不僅有來自天然圖像的切入,還有來自數字世界電子影像的投射,更有來自鏡頭的拼接、特寫、虛化、渲染等虛擬圖像的沖擊,形成獨特的現代視覺敘事效應。這就是媒介以驚人的力量和效率所生產的,并給大眾帶來全新視覺沖擊力的“擬象”。“這不僅是‘視看’權力的技術延伸,更是一種全新視覺體驗的自覺形成,帶給主體的自然是一種新奇的視覺表達能力。”①張偉:《從“視覺機制”到“視覺體制”——現代視覺圖式的權力架構與意義延展》,《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第172頁。視覺圖像擴寬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被感知空間,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認知能力、視覺理解能力、視覺想象能力等視覺素養結構得以出新。圖像符號的生產者“通過制作圖像以表達自我,乃是取自自我意識本身最為深刻的本質和根源。”②[英]保羅·克勞瑟:《視覺藝術的現象學》,李牧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98頁。圖像符號的觀看者結合自身實際對圖像意義做出詮釋,同時也將自我意識寫入圖像意義之中。媒介締結了圖像生產者與觀看者之間的觀念認同與交往關系,生產者與觀看者的視覺交互性構成主流價值觀認同的邏輯前提,圖像符號表征軸和交流軸共同指向了主流價值觀表征重心的轉移,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個體視覺素養問題也就凸顯出來。
圖像生產者在主體客體化過程,將主流價值觀外化到視覺圖像中,創造傳播主流價值觀的視覺作品。生產者以視覺圖像形式呈現意義,但意義如何被視覺圖像所呈現,受制于生產者的視覺素養。生產者的視覺素養構成主流價值觀認同的主體性能力。由視覺認知能力、視覺理解能力、視覺想象能力耦合成的生產者的視覺素養,為主流價值觀認同提供一種一般意義上的直觀導向,也成就了視覺世界中棲居的意義從外在性到內在性的通達。視覺認知是生產者呈現主流價值觀的重要環節。生產者對圖像的亮度、形狀、色彩、運動和視覺深度等視覺信息進行形象辨認,析出對承載主流價值觀的視覺圖像空間結構的整體性認知,在視覺經驗的日積月累中就會生成以視覺圖像主導的認知范式,圖像生產者憑借這種先入為主的視覺直觀也就會無限接近主流價值觀的本質。視覺理解是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基礎。為達到圖像的視覺沖擊效果,圖像生產者會重構圖像編碼的結構性要素,并自覺將主流價值觀熔鑄于圖像符號結構之中,從而賦予經驗世界以再造性意義的可能性。視覺想象是通達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最佳路徑,視覺效果是最佳的說服力,主流價值觀要獲得最佳的視覺認同效果,就要用視覺敘事再現主流價值觀認同問題的種種畫面,這等于將觀看者帶到真實的場景,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視覺體驗。因此,在推動主流價值觀認同上,畫面感的視覺敘事比聲音感的語言敘事更具有說服力。圖像生產者肩負引導主流價值觀的責任,以視覺認知能力解決主流價值觀認同的理性坐標問題,以視覺理解能力把握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存在結構,視覺想象能力喚起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內在魅力,從而創作出蘊含主流價值觀的圖像作品。圖像生產者要充分理解圖像符號的表征機制,根據主流價值觀的規定性把握圖像符號的編碼,促使視覺圖像搭建從認知到理解再到想象的完整意義鏈條,提升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效果。
圖像觀看者在客體主體化過程,將圖像中所承載的主流價值觀內化到自身的心理世界,從而實現對主流價值觀的自覺認同。當圖像離開生產者,便迎來了受眾的新的“觀看”,對圖像意義的解釋由此脫離了生產者的場域進入到觀看者的經驗空間。作為視覺表征中交流軸的重要端口,觀看者對生產者所創作的圖像符號的解釋,取決于觀看者的選擇性接受能力、多元化解讀能力、審美式想象能力等視覺素養。觀看者的視覺素養為主流價值觀認同提供一種深度經驗性呈現,主流價值觀便在視覺空間中浮現,這就是圖像表征主流價值觀最為深邃的意指。觀看者的視覺選擇能力解決的是主流價值認同的面向問題,不同觀看者的經驗背景決定了觀看者的視覺選擇性,同時也決定了其所秉持的不盡相同的價值取向。觀看者對視覺圖像的選擇性接觸、選擇性聚焦、選擇性統合構成了一個關于意義和價值的統一場域,這種意義和價值規定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具體切入模式。觀看者對圖像意義的多元解讀帶來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整合問題。圖像能指的漂浮與多義致使其與意義所指的分離,圖像意義的非穩定性將完整的敘事割裂成孤立的碎片。主流價值觀的圖像化和視覺化傳播也正印證了這一趨勢,主流價值觀以直觀顯現的方式靠近受眾,經由觀看者的認知和理解,形成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多元闡釋路徑。觀看者的審美式想象力鋪展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具象化路徑,審美式想象是基于一種自然而然的相似性的慣例化視覺指涉,在視覺圖像與主流價值觀之間建立起同構性鏈接,將抽象的主流價值觀認同置換為具象化的身體感知,并在圖像的變量中尋找主流價值觀的常量,這種意義的指向性是在最為基礎的圖像發生學意義上產生的,并且較之語言敘事的任意性取向就更為便捷。
媒介為圖像生產者與觀看者實現主流價值觀認同提供體外化的技術延展。圖像生產者與觀看者通過媒介進行主流價值觀的塑造和傳播,這實際上是在圖像的空間結構與價值的可能性之間建立起關聯,這種媒介成為圖像生產者與觀看者之間對話的象征性要素。從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謂媒介是人的延伸,到居伊·德波強調媒介是對社會環境和社會關系的塑造,彰顯了媒介從工具論到生存論的演化路徑。從媒介的工具性看,視覺素養的提高取決于媒介技術的革新,正是技術革新帶來了人類感官和能力的延伸或拓展。麥克盧漢將媒介定義為人的延伸,不同媒介延伸了人的不同部分,也延伸了不同的感覺器官,并借用“按摩”一詞表述媒介對受眾的認知模式和感官比率的變革,受眾在媒介的“按摩”中被動地接受碎片化的信息。在某種意義上講,媒介所營造的擬態環境以沉浸式方式塑造著受眾的價值觀念,受眾始終身處主流媒介所建構的主流價值觀的社會氛圍之中。“在給定文化中的任何新形式的媒介的引進,都會決定性地改變該文化的成員對其物質世界和既定價值觀予以中介化的方式。”①胡泳:《理解麥克盧漢》,《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期,第93頁。質言之,媒介改變了主流價值觀的認同方式,重要的不再是主流價值觀本身,而是媒介帶來的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時間和空間感知模式。從媒介的生存論來講,媒介不僅把創作者/閱讀者、發送者/接收者、表演者/觀看者等存在關系的兩方關聯在一起,而且還會構筑一種偽真實,即媒介將影像升格為貌似真實的存在,進入到視覺經驗媒介化的景觀社會。在景觀社會中,視覺蛻變為媒介伺服機制,人的視覺被媒介表象化,對物的“觀看”轉向了對媒介化影像的“顯現”,媒介成功實現了對價值觀念的控制。居伊·德波迫切反對利用媒體中性地遮蔽景觀的意識形態屬性。“景觀是杰出的意識形態,因為它在其圓滿中展示和表現了任何思想體系的本質;對真實生活的窮困化、奴役和否定。景觀是物質上的‘人與人之間分離和疏遠的表達’。在其中集聚的‘欺騙的新的力量’,其基礎就在生產中,通過生產,‘隨著對象的數量的增長,奴役人的異己存在物的新領域也在擴展’。”②[法]居伊·徳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第136頁。質言之,在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機制中,媒介的工具性延展了人的感官,媒介的生存性使人沉浸在視覺的盛宴中,整個社會生活呈現為圖像化的表象,圖像編碼者和解碼者都無法脫離媒介進行自我構建,只能在媒介打造的景觀中所選擇呈現的畫面,自覺接受由現實圖像化構建的主流價值觀。
四、主流價值觀認同的社會視覺體制
當視覺圖像以權力形式完成對敘事空間的占領后,主流價值觀認同就從生理層面的“視覺機制”轉向社會層面的“視覺體制”,表意世界就成為主流價值觀認同的基本場域,通過打造自覺自為的表意世界,建構起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以“權力體制”為軸心的社會性視覺架構。視覺是人類處理人與世界關系的基本方式,視覺不僅代表人與世界的一種存在關系,同時更象征著人與世界的社會關系。“看制造意義;它因此成了一種進入社會關系的方式,一種將自己嵌入總的社會秩序的手段,一種控制個人的眼下的個別社會關系的手段。”①[英]約翰·菲斯克:《理解大眾文化》,楊全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8頁。當視覺作為一種圖式被生產者與觀看者在可見世界與不可見世界之間反復重置之時,視覺就獲得了社會性身份確認,生成一種類似國家機器的支配性力量,這就是視覺體制或者視覺政體。現實世界的你、我、他的視覺眼光相互交織構成一個個高度社會化的視覺體制,“觀看”與“被視看”都被框定在這種視覺體制之中,為視覺行為披上合理性外衣,為視覺圖像設計審美化包裝,為視覺敘事布置微觀化場景。在視覺權力主導之下,主流價值觀認同須要完成可見世界的視覺表象與不可見世界的意識形態的聚合,以不可見世界的意識形態之手繪制可見世界的視覺表象之景,將承載主流價值觀的視覺圖像顯現出來。
觀看與被觀看在視覺表征關系中的權力配置是視覺體制的基本問題。“誰在觀看”“怎樣觀看”“觀看什么”都是政治哲學問題,觀看與被觀看的階級問題、種族問題、性別問題、宗教問題等都預設了社會視覺體制的價值前提問題,當視覺權力在可見世界和不可見世界之間搭建符合視覺體制的表征秩序時,觀看與被觀看便構成了視覺權力實施的基本構架,觀看不是純粹主動的,被觀看也不是純粹被動的,無論是觀看者還是被觀看者都必須在視覺的社會建制框架下對圖像意義做出或認同或拒斥的選擇。傳統社會的觀看被政治權力直接統治,呈現出被動性和服從性的特質,語言文字敘事體現了權威政體或顯性或隱性地對意義領域的權力規訓。現代社會的海量圖像深入到了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為人們提供了快感與欲望交織的視覺敘事。視覺表征獲得了敘事自由,將言說和表達的權力下放,視覺觀看權力強化了觀看的主動性,觀看不僅具備了判斷、選擇、理解的權力,而且具有提出合理的質疑、要求和審問的權力。視覺圖像作為中介建立起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個體通過觀看的方式進入到社會關系中,視覺圖像對個體主體的作用力可能將主動的觀看轉化為被動的觀看,也可能將被觀看的被動轉化為主動。這就是觀看與被觀看的辯證法。在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體制中,當觀看能夠表達和施展其自身的權力,觀看就通過與被觀看的溝通交流和反饋評價,以便對被觀看合理性的審問、要求、質疑,來建構自身的價值觀念表達空間。觀看的思想意識、情感態度、審美趣味傾向獲得群體性的歸屬,圖像暗含的主流價值觀念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被觀看主動地認同。這種被視覺塑造出來的主流價值觀認同在個體觀看的權力表達中隱秘地實現著權力的社會性構架。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傳播不是生硬地表達特定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而是將其熔鑄于視覺圖像中,通過自然的圖像敘事實現情緒調動、情感激發、價值引領,使觀看在不注意圖像符號本身隱藏的主流價值觀宣傳策略情況下,主動地認同視覺圖像所傳達和指向的主流價值觀。
觀看在視覺表征關系中對自我主體地位確證是一個視覺社會學過程。觀看與視覺表征關系意味著一種權力生產機制,即觀看就是權力。“視覺場域和視覺實踐對對象、主體及其關系的建構其實就是對權力的分配或配置,視覺性必定隱含著一種視覺政治。”②吳瓊,《視覺文化研究:譜系、對象與議題》,《文藝理論研究》2015年第4期,第33頁。“誰在觀看”解決的是觀看的主體問題,觀看的主體地位并不是天賦的,而是視覺權力主體的博弈過程,觀看主體既是建構性的,又是被建構性的,觀看主體在觀看的社會建制框架下依據觀看利益所做出的觀看選擇,實現觀看效果的意義增殖。“怎樣觀看”解決的是觀看的方式問題,怎樣觀看并不是觀看的自主抉擇,而是視覺建制的社會學確認。“‘觀看’是設置我與其他人的直接關系的方式,但是它是通過使被觀看的經驗成為主要的而我自己的觀看則成為第二反應這一出人意料的顛倒的方式來實現的。”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文化轉向》,胡亞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01頁。“觀看什么”解決的是觀看內容的選擇問題,哪些觀看內容可見,哪些觀看內容不可見,不是觀看生理——物理的過程,而是觀看的社會學過程。觀看中的價值觀禁忌與懲罰問題需要在觀看的社會學過程中得以解決。從“誰在觀看”,到“怎樣觀看”,再到“觀看什么”,解決的是觀看與視覺表征關系的權力配置問題,觀看與視覺表征的關系一方面表現為權力支配關系,另一方面也表現為價值認同關系。如果說權力支配關系體現為觀看的主動或被動,那么,價值認同關系則意味著觀看在視覺表征關系中的價值身份的認同或拒斥。質言之,視覺體制既是權力的生產機器,同時也是價值的認同系統。視覺體制的權力配置中,關鍵并不在于視覺圖像所代表的權力傾向,而在于權力對價值的編碼和價值對權力的解碼。因此,主流價值觀認同就要拆解視覺體制的權力支配,讓觀看學會“反觀”,在“正觀”與“反觀”二律背反中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自覺機制才能得以生成。
被觀看基于觀看的社會需求生成被觀看的對象,在與觀看的拓撲式交換中共同生成視覺表征關系。被觀看與視覺表征關系也是一種權力生產機制,即被觀看就是權力。視覺圖像被觀看就意味著其出場權力,同時只有被觀看才能反證觀看主體的價值意向。被觀看通過刺激快感的視覺幻象招攬觀看,在滿足觀看主體的社會需求的同時,也以其潛在價值傾向形塑觀看主體,使觀看沉浸在被觀看的價值觀念認同中。“被誰觀看”設定了視覺的介入權力問題,視覺圖像從一開始就不是指向廣泛的受眾群體,而是設置了被觀看的身份門檻,此乃是一種被社會建制賦予的被觀看的視覺權力。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體制關鍵在于是誰設定了被觀看者的權力,“被誰觀看”的視覺體制成為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權力鏡像,權力的眼睛成為解開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密鑰。“如何被觀看”探討以何種方式行使視覺權力的問題,被觀看的對象看似是被選擇的客體,實質上卻在無形中規定著觀看者“如何觀看”。視覺體制以權力的規訓演繹視覺圖像“如何被觀看”,同時也將其承載的主流價值觀隱匿地附著在視覺網格之中,這樣可見的視覺圖像與不可見的價值觀念就都被收編在“視覺體制”之中。“被觀看到什么”解決的是視覺權力的效果問題,觀看的閾限問題不是由觀看決定的,也不是由被觀看決定的,而是由視覺體制所決定的。視覺體制成為“被觀看到什么”的最終決定力量。因此,在視覺化時代主流價值觀認同的關鍵在于視覺體制的建構,通過視覺體制建設破除“漂浮的能指”對現實世界的微觀拓殖,將視覺中最具表現力的感性因子和思想中最具穿透力的價值因子交疊,激活主體與世界的價值關系,讓每一個價值主體都成為視覺表征關系的真正主人。就此,視覺體制將成為一個擁有空前感知空間與價值活力的社會建制。
將觀看與被觀看結構化的視覺體制已經成為一種物質性力量,視覺體制不只是對現實世界的“反映”,同時也是對現實世界的“創造”,從認知方式,到價值秩序,再到文化觀念等都為視覺所折射,所規制,所建構。與語言敘事的邏輯認知不同,圖像敘事則是憑依感官獲得的一種自主性直觀認知。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認知方式經歷了從文字到圖像,從抽象到表象,從呈現到創造的深刻變革。基于直觀認知的視覺圖像的復制與模擬將會形成比真實還要真實的“超真實”,鮑德里亞將其稱之為“擬象”,在擬象世界中,“所喪失的乃是全部的形而上學。不再有存在和表象的鏡像,不再有現實和現實的概念的鏡像。”①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2.這樣,價值觀念就由視覺模型不斷地被復制出來,“一切都變得既是分離的又是毫無差別的,每一個人都狂熱地追隨時髦的模式,追隨大合唱式的‘擬象’模式”。②吳瓊:《視覺性與視覺文化——視覺文化研究的譜系》,《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第91頁。如果說語言是對符號與實在同一性原則的堅守,那么擬象則是對符號與實在同一性的徹底否定,從此沉迷在擬象世界的自我增殖中,最終導向價值的虛無與文化的庸俗。與語言敘事所執著的抽象價值秩序不同,圖像敘事則是追求視覺配置的邊際效益,由此就搭建起了現代視覺圖像符號的資本經濟屬性。“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視覺文本同樣遵循著資本最大化原則,如何實現自身影響力的最大化,從而掌控更多的受眾群體,拓展文本權力的運營區域成為現代視覺權力架構的重要方向。”③張偉:《從“視覺機制”到“視覺體制”——現代視覺圖式的權力架構與意義延展》,《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第173頁。當商業資本與文化資本促成視覺消費時,人本能的視覺接收便成為投射欲望的幕布,個體對觀看的控制權直接轉移到被視為文化資本的圖像符號上,圖像搭載的“思”與“意”被消費激發的“情”與“欲”所覆蓋。這種滿足虛幻的視覺運行機制直接導向隱而不現的視覺權力運作體制,被操控的圖像符號淡化了對價值觀念的引領功能,誘發著人們文化精神層面的危機。與語言敘事所建構的精神文化不同,圖像敘事建構的則是以視覺性為核心的身體文化。身體文化的崛起解除了精神世界的形而上學對身體的束縛,還原了身體的創造力,但是卻又墮入消費主義的陷阱,身體成為消費的對象。從此,語言敘事中的“可思”變成了圖像敘事中的“可視”,傳統形而上學層面的精神追求降格為淺表化、娛樂化的身體指涉,傳統的洗禮性、深刻性的文化熏陶讓位于及時性、功利化的文化消費。在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體制內,應該將視覺的身體性與理智的精神性結合起來,既規避由資本增值和欲望機器所造成的“視覺暴力”,也保留理性思維的文化底色。當然,面對身體文化的浪潮,圖像敘事可為主流價值觀擴充領地,在從語言敘事到圖像敘事的轉向進程中,承擔起新的歷史責任和文化使命。
結語
語言敘事到圖像敘事的轉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視覺性”成為從主體認知到價值秩序再到社會建制的主導邏輯,世界被視覺機器編碼為純粹的表征圖像,人與世界的價值關系就轉變為視覺化的經驗關系,所有的價值觀念都被視覺經驗所重塑。因此,視覺時代的主流價值觀認同就要在圖像的觀看與被觀看間建立起表征秩序,在媒介技術支持下視覺權力完成其視覺體制建構,在觀看與被觀看的視覺社會學過程完成對主流價值觀的意義縫合。視覺時代的到來,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機制建構,并不是以圖像敘事簡單地取代語言敘事,而是以視覺直觀充盈話語秩序,以邏輯認知條理視覺圖像,感性的圖像與理性的語言融合共生,從連接能指與所指的圖像表征軸還原主流價值觀認同的意義空間,從連接編碼者和解碼者的圖像交流軸衡定主流價值觀認同的視覺場域,從圖像生產者,到圖像觀看者,再到媒介,為主流價值觀認同提供個體層面的視覺素養支撐,從觀看,到被觀看,再到觀看與被觀看的耦合,為主流價值觀認同提供社會層面的視覺體制支撐,主流價值觀認同才會獲得來自視覺文化深處的認知潛力和價值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