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精神健康危機實錄
埃莉斯·巴爾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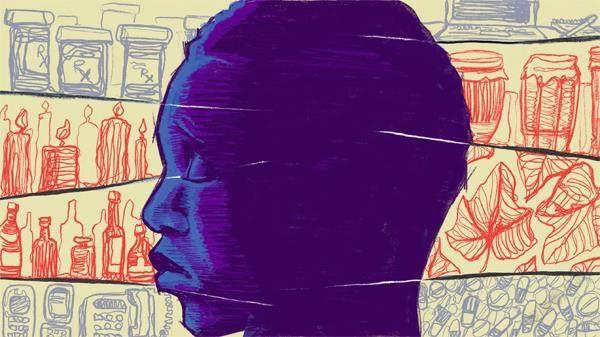
“因抑郁癥而自殺,這根本就不是非洲人會做的事。這種疾病大概只有白人或中產階級才能有幸患上。”2014年,美國喜劇演員羅賓·威廉姆斯自殺身亡,肯尼亞諷刺作家、《世界報》專欄作者泰德·馬蘭達有感而發,寫下了這段話。
這段充滿刻板印象的話語引發了輿論熱潮,這正是馬蘭達的目的:聚焦非洲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撕破精神疾病的神秘面紗,讓這個話題在非洲不再是難以涉足的禁忌領域。“肯尼亞和整個非洲的情況差不多,人們對抑郁癥及其他心理疾病充滿了誤解。這類疾病遭到污名化,在家里也是禁止討論的。”馬蘭達說,“雖然目前,非洲媒體對自殺行為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轉變,會抱著同情與理解進行報道,但總的來說,非洲在精神健康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仍相當薄弱。”
在這一方面,馬蘭達所處的肯尼亞遠不是非洲最落后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布的精神衛生報告顯示,2020年,人口為5300萬的肯尼亞擁有超過8000名精神健康專業人員。而與此同時,人口約為肯尼亞一半的馬里僅有46名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總體而言,在非洲,一名精神科醫生平均要為50萬名居民提供服務,而國際組織建議的比例為1比5000。
非洲人對精神健康服務有著巨大的需求,然而非洲的公共衛生政策卻長期忽視這一領域。喀麥隆人類學家帕爾費·阿卡納說:“在街頭游蕩的精神病人是非洲城市里永恒不變的元素。小的時候,我就經常看見有人在大街上赤身裸體,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在路邊隨地排泄,在泥漿里打滾。我聽說有男人會侮辱瘋女人,還有人會拿精神病患者作為祭品,獻祭給神靈。這些病人從未受到重視。只有在高喊‘提高衛生健康水平’的口號時,人們才會關注他們,并盤算著該如何將他們除掉。”
| 自殺率全球最高 |
世界衛生組織稱,非洲國家在精神健康方面的投入,人均僅有0.46美元,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為低收入國家建議的人均投入標準(2美元)。經濟金融以及眾多其他危機使得非洲成為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大洲。2022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曾呼吁應給予非洲的精神健康危機更多關注。
70歲以上人群的精神健康問題尤為嚴重。“但這只是冰山一角罷了。”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和物質濫用司的地區顧問弗洛朗絲·巴因加納說。她主張政府大力增加對精神疾病預防項目的投入。然而,預算是有限的。非洲大部分資源都被用于防治致命性極強的傳染病,包括瘧疾、艾滋病、結核病、麻疹、埃博拉出血熱以及新冠病毒。而且,也極少有國際援助組織能夠拿出資金專門解決精神健康問題。
不過好消息是,部分非洲國家近年來已將“加強精神健康服務建設”提上了日程。2021年,肯尼亞及烏干達通過了精神健康方面的五年計劃。加納和津巴布韋也與世界衛生組織達成合作,為國民提供相關服務。

| 塞內加爾的精神病中心 |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他接受過哪些治療?”主治醫師阿達瑪·孔度向正在翻閱默罕默德病歷資料的護士詢問道。默罕默德在三天前被送入了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該中心位于塞內加爾西南部城市濟金紹爾的郊區,掩映在繁茂的芒果樹、檸檬樹及香蕉樹下。院內排布著18間小房子,用以容納前來治療的病人及其家屬。
家人可以陪同治療,是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的特色之一。“家屬是共同治療師。”孔度說。他在這里已經工作了12年。中心里的18名患者都有家屬或朋友陪伴,他們會被安排住在同一間小房子里。“我和我媽媽一起來的。她每天幫我做飯、洗澡。有她在,我很安心。”31歲的患者帕普·布瓦耶說。他在這里已經待了一個月,即將出院。除了照顧患者的日常起居外,陪護者還負責與其他家屬保持聯系,充當患者與外界之間的橋梁,避免患者感到孤獨。
長期以來,塞內加爾一直是非洲精神健康領域的領先國家。上世紀60至70年代,達喀爾的范恩大學附屬醫院開創了兩個“精神疾病村”,這也是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的源起。精神科醫生亨利·科隆及穆薩·迪率是這個項目的牽頭人,認為精神治療不應忽略患者的社會文化背景,同時提倡使用非洲本土的傳統藥物。患者可以在家屬的陪同下入住“精神疾病村”接受治療。“這么做是為了讓治療過程更具有人情味。”孔度解釋道,“只有護士長常駐村中,為病人發放藥物。科隆每個月都會到村中探望病人。”
馬穆爾·法爾曾是“精神疾病村”(即如今的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中的一名患者,于1975年入住。現在,他病情已然穩定,在中心擔任運營負責人,時常會與患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說:“以前這里沒有警衛,是開放式的村莊。我們可以隨意出入,附近的居民還能來找我們喝茶聊天。”
上世紀90年代末,當年的護士長退休后,一直沒能找到新的人選,精神疾病村便也漸漸沒落了。2002年,從塞內加爾濟金紹爾返回首都達喀爾的“喬拉”號輪船傾覆,導致1800余人喪生大海,其中971名遇難者來自濟金紹爾。四年后,荒廢的精神疾病村被改造為了如今的精神疾病中心,讓幸存者及遇難者的家屬能夠在這里接受心理治療。
自1974年以來,該中心接治了將近6.3萬名病患,主要為精神分裂癥患者、急性妄想癥患者及癲癇患者。家屬陪護在治療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每個星期,患者家屬會聚在中心的一棵大樹下,與醫護人員討論他們在陪護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 來自鄰國的患者 |
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的常規問診費為0.32美元,每日住院費4美元,精神疾病咨詢費6.4美元,腦電圖檢查費16美元。如此低廉的價格吸引了許多鄰國患者前來看病。57歲的塞內布·馬內就是其中之一,她帶著女兒從幾內亞比紹來到塞內加爾。“她有多語癥,會和腦海里的聲音對話,而且很焦躁。”孔度醫生說,“這其實是一種急性妄想癥,患者會逐漸和現實脫離聯系。”孔度給她開了舊版的安定藥,雖然有副作用,但價格便宜。“新一代的藥品全國都斷貨了,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她說。
這一天,孔度接待了27歲的薩內女士。她來自一個“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她是丈夫的第一個妻子,孩子八個月大。近日,薩內的父母接連去世。除了要承受失去雙親的痛苦,她還需應對與另一個妻子源源不斷的矛盾。她低聲向醫生述說道:“最近我根本睡不著,腦子很亂,很容易感到疲憊。”孔度診斷她為產后抑郁癥,給她開了抗抑郁藥物。

將藥物遞給薩內之前,孔度詢問她是否在服用非洲傳統藥物。“出于謹慎考慮,我會讓病人不要將傳統藥物及現代藥物混合服用。不過,他們可以繼續進行傳統的儀式療法,比如泡泥漿浴。有信仰,有家人的支持,病能好得更快。”孔度說。
資金短缺是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面臨的一大問題,國家補助僅占該中心預算的13%。塞內加爾衛生部在2019年的一項報告中揭露:精神健康領域的人力、資金及藥物均極其短缺。該國共有13家精神疾病機構,配備38名精神科醫生及363張病床。超過半數的精神疾病機構都位于首都達喀爾。埃米莉–巴迪亞納精神病中心的醫護人員也并不充裕:兩名精神科醫生每周到訪中心四次,為新入住的病人及情況嚴重的患者會診;還有六名護士負責跟蹤病情穩定的患者的情況,他們都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
| 精神科醫生匱乏的南蘇丹 |
因為停電,天花板上的吊扇紋絲不動。陣陣微風從窗戶吹入,讓這間有著淡綠色墻壁的小診室稍稍涼快了一些。阿頓·阿尤艾爾醫生的辦公桌上放著一袋從街頭買來的炸糕,她還沒來得及吃早飯。這名南蘇丹的精神科醫生毫不掩飾她的疲倦。在兩次問診的間隙,她用雙手撐著頭,閉上眼睛稍作休息。

這是去年10月的一個周五,阿尤艾爾醫生忙碌的一周已經接近尾聲。她40歲,是三個孩子的媽媽,自2014年起擔任朱巴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科的負責人,同時也是南蘇丹衛生部精神衛生司司長。阿尤艾爾醫生致力于從不同層面推動該國精神健康事業的發展。作為精神衛生司司長,阿尤艾爾制定了一項“戰略規劃”:五年內,讓80%的南蘇丹鄉村居民享受到精神健康方面的基礎醫療服務,預估費用為1800萬美元。
南蘇丹內戰多年不休,人民心理受到重創。然而,該國卻沒能為國民提供最基礎的精神健康醫療服務。2009年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首都朱巴,約36%的居民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50%出現了抑郁癥的癥狀。世界衛生組織稱,2019年,南蘇丹的自殺率排在非洲國家第四位(全球排名第13)。這個國家同樣面臨資金匱乏的問題。此外,南蘇丹當局也缺少必要的數據,難以精確衡量精神健康情況的嚴重性。直到2021年,該國才開始在五個州(全國共十個州)內系統性地收集國民精神健康數據。
南蘇丹擁有1200萬人口,全國卻僅有三名精神科醫生,阿尤艾爾就是其中之一,她也是唯一一名在公立醫院行醫的精神科醫生。“需求太大了!”阿尤艾爾不顧家人及朋友的反對,毅然決然地進入了這個行業。“在醫學院上學時,我是全年級第二名。當時大家都說,我做精神科醫生實在是太可惜了。”她說。她原來的志向是兒科。在西加扎勒河州的一家醫院實習時,她改變了想法。她說:“面對患有精神障礙的病人,我感到很無力。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把他們關進監獄。我感覺我的專業知識毫無用處。于是,我想,為什么不做一名精神科醫生呢?”后來,阿尤艾爾完成了蘇丹醫療專業委員會的研究生培養項目,畢業后成為了朱巴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科的負責人。
“那時的精神科十分混亂,沒有病歷,也沒有合格的心理專家,每天只開診幾個小時。”阿尤艾爾回憶道。經過多年發展,精神科團隊已擴大至八人,包括多名心理專家及醫護,能夠為市民提供不間斷的接診服務,并與多個非政府組織達成了合作。精神病患者、抑郁癥患者及情感性障礙患者都可以在這里得到相應治療。
“我們收治的大多數患者都是因為物質濫用——比如酗酒或吸食大麻——而患上了精神障礙。”阿尤艾爾說,她坐在大大的辦公桌后面,桌上擺放著幾份病歷。“患者有心理創傷,想試著自我修復,濫用物質是他們的常用手段。”


阿尤艾爾所在的精神科被稱為“11號病房”,位于朱巴大學附屬醫院的邊緣地帶,和醫院不共用一個出入口。精神科共有12張病床及一間用于問診的小診室。診室內光線昏暗,褪色的墻壁和鐵窗讓氛圍顯得更為陰森。走廊上睡著一個男人,腳踝上拴著鐵鏈。阿尤艾爾解釋道:“我們給他注射了鎮靜劑,正考慮把他送入朱巴中央監獄。我們沒有能力處理有暴力行為的患者。”由于醫院缺乏相應資源,南蘇丹首都的中央監獄設有專門區域,用于關押有暴力行為的精神病患者。
雖然精神健康領域的醫療服務水平有所提升,但困難依舊存在。“我們科室的資金是全院最少的,沒有錢翻新病房。科室里的醫護人員工資都很低,缺乏工作動力。”阿尤艾爾說。作為精神科的負責人,她的月薪僅為十美元。“工資低就算了,還經常不能按時發放。”她接著說。阿尤艾爾除了在公立醫院接診外,還有一家私人診所,這是她的主要收入來源。依靠私人診所的收入,她才得以撫養三個孩子,同時——用她的話來說就是——“建設南蘇丹”。
南蘇丹的少數民族多達60余個,與他們溝通并不容易。“我學會了多種少數民族的語言,很少出錯。為少數民族患者服務,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用他們能理解的話語來解釋精神疾病及癥狀。很多時候,他們并不認為某些癥狀是精神病的表現。”阿尤艾爾說。

她還說起了她在瓦拉卜州的經歷。2016年,她在當地遇見了一名被稱為“療愈者”的傳統醫師。這名傳統醫師在遠離人煙的村莊“醫治”著13名精神障礙患者,多年來一直用鐵鏈把這些患者拴在大樹上,慘叫聲不絕于耳。阿尤艾爾以自己的名聲擔保,才說服了療愈者釋放病人,把他們送入醫院。對此,她至今仍記憶猶新。想起當時的情景,她不禁長舒一口氣,說:“從那以后,村莊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編譯自法國《世界報》]
編輯:侯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