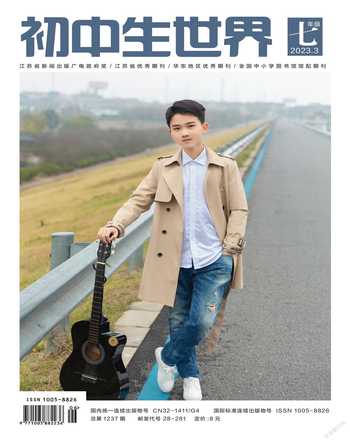許淵沖:詩意地走過一個世紀
張渺

統編語文教材七(下)第一單元拓展閱讀
主持人:張桂銀 高級教師,遼寧省大連市骨干教師,任教于大連南金實驗學校。
自古文人多疏狂
許淵沖身上始終貼著“狂”的標簽。他的狂是文人的狂。他與同行們爭論直譯好還是意譯好,被指著鼻子罵過,被寫文章批評過。他自然不甘示弱,用同樣犀利的筆觸反駁回去。
如今,他的名片上直接印著“書銷中外六十本,詩譯英法惟一人”,被許多人指責為狂妄,又自言“狂而不妄”。
2010年,許淵沖獲得中國翻譯協會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4年8月2日,他獲得國際翻譯界最高獎項之一的“北極光”杰出文學翻譯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
“我們中國人,就應該自信,就應該有點狂的精神。五千年的文化,是智慧的傳承,是精神的傳遞。”老人家仰坐著,將知名的翻譯家歷歷數來。“我這樣的人,就這么一個!”他強調,“幾千年來就這么一個!”
將創造美視為畢生追求
因為對美的執著,他堅持文學翻譯應實現“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
雖然有人批評他不忠實于原文,但他堅持將創造美作為最高標準。“為了更美,沒有什么清規戒律是不可打破的。”
1958年,他開始把毛澤東詩詞譯成英文和法文,用的翻譯方式是韻文。他孜孜以求,琢磨著怎么翻譯《沁園春·雪》。一會兒覺得,自己把“惟余莽莽”“頓失滔滔”的音韻節奏都翻譯出來了;一會兒發現,自己成功地把“略輸文采”“稍遜風騷”的對仗也譯出了精髓。他神游天外,暗暗得意。
他的一個世紀里,最大的“戰斗”恐怕是直譯與意譯的論戰。
過了幾十年,他還記得老師曾講的:翻譯最大的問題是只譯了詞(表層結構)而沒有譯意(深層結構),說有一個外科醫生醫治箭傷,只把箭桿切斷,卻把箭頭留給內科醫生去取,外文翻譯絕不能像這個外科醫生。
百歲亦如少年
晚年時幾乎每個下午,保姆都會帶著他去離家不遠的公園散步。直到2017年的中秋,他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右腿骨折。即便如此,他仍然盛贊那晚的月色,仿佛為此摔斷了腿也是值得的。
百歲的許淵沖仍然精力十足,他早早學會了使用電腦,大量的翻譯工作,都是用他書房里的臺式電腦完成的。翻得沉迷起來,就半宿半宿地熬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點。
他愛吃漢堡和方便面這些“垃圾食品”,愛喝加熱的可樂,對甜食尤為熱衷。妻子有時試圖阻攔他,他不肯聽,“我就要吃”。
2018年,與他攜手大半生的妻子去世了。那段時間他異常沉默,有時甚至一晚上只睡一兩個小時。一個失眠的夜里,他從床上爬起來,又坐到桌前,開始翻譯。“只要我沉浸在翻譯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來。”他說。
讓中國文化走向全世界,是他畢生心愿。“中國文化是博大精深、獨一無二的,我們正走向復興,一定要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價值,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
百年如夢。他揮灑著詩意,走過一個世紀。
(選自2021年2月3日《中國青年報》,本刊有刪改)
—— 鑒賞空間 ——
本文以散淡的敘事風格,如串珠般串起了翻譯界泰斗許淵沖先生追求理想與美,致力于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的燦爛生平。作者采用了與《鄧稼先》一文相同的結構組織方式,用巧妙的小標題自然分割了文章不同的敘述段落,使文章條理清晰、層次分明。同時,本文通過典型事件、典型細節,還原了許淵沖先生作為翻譯大師和文藝家的“狂”以及對美的忠誠,還有他作為一個尋常老人真實可愛的生活情緒和充滿詩性的生命追求。
—— 讀有所思 ——
身為“兩彈元勛”的鄧稼先“忠厚平實”“從不驕人”“是最有中國農民的樸實氣質的人”;而作為翻譯巨擘的許淵沖卻處處鋒芒畢露,是翻譯界的“狂人”。你欣賞哪種品格?對此兩種不同的精神氣質,你又作何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