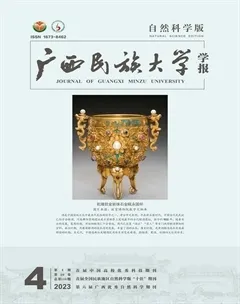古代辭賦反映的物理認識
關鍵詞:辭賦;古代物理認識;古代物理現象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462(2023)04-0010-10
從西周至明清,先人們創作了難以計數的詩詞歌賦作品。古人在詠物寄情的同時,偶爾也表達了一些對自然現象和技術發明的認識,因此古代詩詞歌賦中有不少具有科技史料價值的內容。1993 年,張秉倫先生發表《詩詞歌賦中的科技史料價值》一文,文章在論述詩詞歌賦中的科技史料重要性的同時,呼吁“科學史界對這一領域做更深入的研究”[1],由此引起了人們對古代詩詞歌賦中有關科技史料內容的關注。2014 年,戴念祖先生發表《物理與詩歌同行》,文章介紹了古代詩歌所表達的對于相對運動、鏡面反射、小孔成像、地磁偏角等物理現象的認識[2],由此豐富了中國古代物理學史的研究內容。這兩篇文章所依據的史料主要是古代的詩詞作品,極少涉及辭賦體裁。
賦既是詩的一種表現手法,也是一種文學體裁。《周禮·春官》稱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3]880 南朝鐘嶸認為:“文已盡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4]47 正是由于賦、比、興等不同表現形式的結合,使得詩具備了豐富多彩的藝術特色。賦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既具有詩的性質,又有別于詩,正所謂“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5]17。賦“鋪采摛文,體物寫志”[6]85,講究文采及韻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更適合古代文人用以表達對事物的認識。賦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和稱謂,本文統稱辭賦。從唐代開始,辭賦即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兩宋及金繼承了這種做法,元代曾一度中斷,至明代則予以廢止。清代科舉考試雖以制義為主,但賦也擁有一席之地。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古代留下了大量寫物言志的辭賦篇章,其中包含了不少表達物理認識的內容,可以彌補其他文獻史料之不足。以前的研究者基本沒有關注到這些內容,因此筆者擬對之做一初步討論。
1 對空間和時間的認識
空間和時間是物質的存在形式及運動過程的表現,是人類認識的基本對象。先秦諸子對于時空已有所認識。《莊子·庚桑楚》稱:“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7]454 《墨子·經上》稱:“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8]466 《尸子》說:“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9]15 《文子·自然》《淮南子·齊俗訓》也有類似的表述。顯然,《庚桑楚》給出的時空概念,內涵比較模糊,《墨經》和《尸子》只是對時空做了概括性描述,都沒有說明時空的性質。另外,《論語·子罕》《莊子·秋水》和《墨子》佚文等中有一些語句表達了對時間流逝單向性的認識。總體來看,先秦古人對時空的認識還是相當粗淺的。之后,漢晉尤其是唐代的一些辭賦作品表達了對時空的新認識。
對于時間,古人感受最深的是“時不可及,日不可留”[8]981,因而“圣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10]54。從漢代至清末,古人留下了大量珍惜時間、奮發圖強的詩篇。不過,以辭賦體裁論述時間的作品不多。西晉陸機作《感時賦》,描述了冬季天寒日短、萬物蕭索的自然現象,發出“歷四時之迭感,悲此歲之已寒”的傷嘆[5]51。唐代佚名作者(一說作者是趙自勤)有《時賦》一首,描述自然萬物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盛衰,人事窮達也“感天時之興替”,“時廢時通”,因而主張“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發出“ 自古而觀,惟時之大”的贊嘆[11]4097。此外還有唐代陳昌言作《先王正時令賦》等。總體來看,這類作品對時間的認識水平有限,缺乏深意。
關于空間,唐代幾首《空賦》體現了新的認識水平。唐代以科舉取士,考試內容主要有帖經、墨義、口試、策問、詩賦等,尤其是進士科,詩賦屬于必考內容。為了步入仕途,文人們會用心研習寫詩作賦的能力,因此唐代留下了大量詩賦作品。從現存文獻看,唐代至少有四首表達關于空間認識的《空賦》,其中以唐玄宗時期趙自勤的《空賦》[11]4173-4174 認識水平最高。此賦從四個方面對空間做了描述。
一是空間的形成:“若乃質渾沌,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中。不可致詰,其名曰空。”“渾沌”表示模糊不清的狀態;“鴻濛”是彌漫廣大的樣子。意謂空間形成于天地開辟之始,它混茫無際,彌漫無形,包裹天地。
二是空間的存在狀態:“夫空也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聽之不聞,搏之不有;舒之則遠彌六合,攬之則不盈一手。……大而觀之,則漭漫兮類元胎之貌;審而察之,則眇寞兮凝至道之精。”這是借用老子對道的論述以說明空間的狀態。道不具有形態,老子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以及“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描述它 。空間也是無形無相的,因此趙自勤借用這些語言描述它:“漭漫”表示廣遠無際;“元胎”表示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狀態;“眇寞”即“眇默”,表示空寂的狀態。從大的方面看,空間廣袤無垠;從小的方面看,空間寂寥無形。這些關于空間存在狀態的描述,是符合直觀經驗認識的。
三是空間的性質:“體無涯以為大,物有來而必受。徒意其湛爾無營,飄然至輕。向遙山而似畫,對澄浦而同清。……寂兮寥兮,孰能為其損益。不皦不昧,安可議其幽明。……以無有,入無間。……隨時小大,應物周旋。處覆盆而俱暗,引測管而同圓。入枝間而帶影,通野外以含煙。或高深放曠,或委曲連綿。”這是從多個方面描述了空間的性質:空間體大無涯,可以容受萬物;空間清澈無際,飄然至輕;空間的色彩,隨景物而異;空間無形無相,不可損益;空間不明不暗,無所謂幽明;空間無固定形體,可以入微隙,貫長空,隨時小大,唯物是應;空間雖然無形,但可因物以見形,所以居覆盆之下呈暗,處窺管之中形圓。如此等等,都是說明空間的性質。
四是空間的作用:“利萬物有含容之徳,包二儀有覆載之名。草木資空以長茂,日月乘空以運行。霜雁云鵬,非空無以矯其翼;喬鶯幽鳥,非空無以習其聲。”[11]空間含容萬物,包裹天地,為萬物的運動變化提供場所。
這些論述,相較于前述《莊子》《墨經》《尸子》的表述要全面、深刻、具體得多,在經驗認識層次上,可謂是代表了古代的最高水平。趙自勤在說明寫作這首賦的緣由時說,他“諦想群物,深觀至理;窮未來寂滅之端,探過去混元之始”,受佛學和老莊學說的啟發,認識到宇宙中只有“杳杳茫茫”“非色非相”的東西才是“不存不亡”的,這個東西就是“大象無形”“至恒不變”的虛空。因而對空間產生好奇,“每有書空之嘆”。由此可見,是老莊思想和佛教學說啟發趙自勤對空間這種特殊的存在進行深入思考,寫出了這首《空賦》。
此外,唐德宗時期諫議大夫林琨也作有《空賦》,其中說空間“ 搏之不得,書之不明”,“卷之在方寸之內,舒之盈宇宙之里”[11]4681。唐代郭遹的《空賦》描述空間“去有而含體,乃因無而立空”,具有“希夷難變”“橐鑰罔窮”的性質,因而“神禹莫知其至,離婁安睹其終”[11]6273。唐代張鳴鶴的《空賦》也認為空間形成于萬物產生之前:“ 生于未有,物莫能先”;空間具有“ 既從天而共色,又鑒水而同形,若乃變化隨時,憑乎動止”等性質[11]9882-9883。這些論述所表達的認識水平雖未超出趙自勤的《空賦》,但由此可以看出唐代不同時期文人對空間的思考。
這幾首《空賦》論述了空間的形成、存在狀態、性質和作用,反映了唐代文人對空間的認識水平。此后,中國古人關于空間的認識幾乎再無明顯的進步。
從認識論來看,中國古人對時空的認識與希臘古人有所不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人探討時間和空間的屬性時,將時空與物質的運動聯系起來,因而比較容易揭示其本質。中國古人孤立地考察時間和空間,割裂了二者與物質運動的聯系,因而難以認識它們的本質。
2 對力學器械的認識
桔槔、轆轤、水輪、欹器、驗濕氣、權衡等是古人發明的力學器械,其中含有一些力學知識,盡管它們在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但一般典籍卻很少對其做具體的描述或介紹。古代文人的一些詠物辭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桔槔是杠桿提水工具,最早見于《墨子》的《備城門》和《備穴》篇。《莊子·天地》篇對杠桿的形制和功效做了比較簡單的表述,并指出使用這種工具可以達到“用力甚寡而見功多”的效果。[7]247《莊子·天運》篇指出,桔槔具有“引之則俯,舍之則仰”的性質[7]296。西漢劉向《說苑·反質》稱:“為機,重其后,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12]513-514 這里所謂的“橋”即桔槔。漢代之后,一般文獻中有關桔槔的描述不多。唐代王契作《桔槔賦》,對桔槔的性能和取水過程做了較全面的描述,賦云:“智者濟時以設功,強名之曰桔槔。何樸斫之太簡,俾役力兮不勞。作固兮為我之身,臨深兮是我之理。若虞機張,如鳥斯企。山有木,因工見汲引之能;巽乎水,自我成潤物之美。不羸瓶而上出,何抱甕之勤止。執虛趨下,雖自屈于勞形;持滿因髙,終見伸于知己……隨用舍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11]4417-4418 賦文贊美桔槔雖然結構簡單,卻可以臨深取水,助人省力不勞。桔槔取水時,人牽動系桶的繩索,使桶在井中灌滿水,然后拉動繩子,借助杠桿之力把水桶提上來,節時省力。賦文形容操作桔槔的過程像虞人張弩發機,如鳥踮著腳向井中張望。“執虛趨下”“持滿因高”等,描述了桔槔的運作過程;“隨用舍而俯仰,應淺深而短長”,說明了桔槔的性能。此賦文字簡潔,表述形象,是關于桔槔的難得史料。此外,南宋詩人陳藻也有《桔槔賦》,不過其中沒有關于桔槔形制和性能的描述。
轆轤是由杠桿演變而成的井上提水或起重裝置。1974 年,湖北銅綠山春秋戰國古銅礦遺址發掘出兩根木制轆轤軸,由此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已用轆轤從豎井中提運銅礦石了。然而關于這種器物的使用情況,先秦兩漢文獻幾無記載。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排調》有“井上轆轤臥嬰兒”一語[13];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葵》有“井別作桔槔、轆轤”之說,注云:“井深用轆轤,井淺用桔槔。”[14]94這些文獻只是提到了轆轤的使用情況,而未對其形制做具體的描述。唐代仲子陵作《轆轤賦》,對轆轤的形制和性能做了比較多的描述,賦云:“智者創物以見意,立成轆轤以為天下利。木德標象,金行效事。與桔槔之用則同,比筍簴之形不異。井之勿幕,瓶亦汔至。……圓轉則智士之心,通流乃仁者之志。故轆轤之體一,有君子之道四。觀其得位攸處,居中特立。從繩以寸工,假器以尺汲。自上自下者,念茲以有成。虛往實來者,釋此而何執。利物不言利,急人之所急。舍之則其道可卷而懷,用之則其功可俯而拾。及夫挈瓶所施,懸綆所統。……其靜也,則無機之機;其動也,則有用之用……”[11]5238其中說,轆轤的功用與桔槔同,形制類似筍簴。“井之勿幕,瓶亦汔至。”“ 從繩以寸工,假器以尺汲。自上至下者,念茲以有成;虛往實來者,釋此而何執。”“挈瓶所施,懸綆所統。”這些都是對轆轤運作過程的描述。“舍之則其道可卷而懷,用之則其功可俯而拾。”“其靜也,則無機之機;其動也,則有用之用。”這些是對轆轤性能的描述。中國古代描述轆轤的文獻史料不多。《轆轤賦》雖然文字簡單,表述不夠具體,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水輪也稱筒車,是利用流水為動力自動提水的灌溉工具。關于水輪發明、應用于何時,學界尚無明確的認識。唐代陳廷章的《水輪賦》是一篇比較早的關于水輪的文獻,對水輪的基本結構、旋轉動力、運行特點、使用效果等都有一定的描述,如“水能利物,輪乃曲成”;“斫木而為,憑河而引”;“鄙桔槔之煩力,使自趨之”,說明水輪在河水推動下能夠自行運轉,不假人力。“箭馳可得而滴瀝,輻輳必循乎規準”等,對水輪的結構做了簡單描述。“雖破浪于川湄,善行無跡;既斡流于波面,終夜有聲”,說明了水輪的運行特點,即要將木輪的一部分浸入河水中,才能夠受到流水的推力,保持自轉。“轉轂諒由乎順動,盈科每悅于柔隨”;“回環潤乎嘉轂,洊至逾于行潦”;“常虛受以載沈,表能圓于獨運”;“磬折而下隨毖彼,持盈而上善依于”,描述了水輪的運轉情況,即綁縛在輪輞上的竹筒隨著木輪的轉動,虛者下移,盈者上升,沒于河水中時則灌水,居于高空時則傾水。“鉤深致遠,沿洄而可使在山;積少之多,灌輸而各由其道”;“低徊而涯岸非阻,委曲而農桑是訓”,說明了水輪使用的效果,能把河谷里的水提升到高岸,引至田間灌溉。[11]9840 這些描述對于了解水輪的結構、性能和用途都是有幫助的。
古人認為,物極必反,事盛則衰,這既是自然之道,也是人事之理。《周易》《管子》《帛書老子》《莊子》《文子》《黃老帛書》等典籍中都有這類論述,如《黃老帛書·經法》稱:“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15]420 為了避免盈滿而虧,古人提倡凡事保持不盈不虧的中間狀態。欹器即是古代用以勸導人們戒滿守中的器物,其重心隨著裝水量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反映了重心與平衡的關系。古代一般文獻對欹器的描述不多。《荀子·宥坐》最早對欹器進行了介紹,指出它具有“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的性質[16]。《文子·九守》也稱:“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侑卮”即指欹器。不過,《九守》篇說這種器物具有“其沖即正,其盈即覆”的性質[17],沖即空虛。《荀子》和《文子》介紹的都是欹器,但二者的物理性能截然不同。《文子》屬道家作品,其中描述的欹器性能反映的是道家的貴無尚虛思想。《荀子》描述的欹器性能,反映的是儒家的守正尚中思想。伴隨著儒家文化的流行,《荀子》所描述的欹器得到了古代文人的推崇。唐代有五首《欹器賦》,其中以唐玄宗時期御史張鼎的賦內容最為全面。賦文說:“圣人察兩曜之度,觀萬物之情,知務進者危于不止,擬貪取者敗于幾成。爰制座右,與人作程。開其可誡之跡,加以必覆之名。”[11]3699 這是說明制作欹器的目的和欹器放置的位置。欹器被用繩子系著兩耳懸掛起來,不裝水時,處于傾斜狀態;裝一半水時,處于正立狀態;裝滿水時,即發生傾覆。賦文對欹器的這種性質進行了描述:“不增不減,能正能平。考低昂而必應,亦有效于權衡。”“或益之而損,故至其滿成覆餗之兇;或損之而益,故當其無為有器之用。”“滿而既溢,傾必從之。”賦文指出,如果希望“避禍于將盈之日,圖全于未兆之時”,“則知欹器之器大哉,吾將以為教始”[11]3700。唐太宗時期中書舍人韋肇作有《攲器賦》,其中說:“天地忌滿,鬼神害盈。……故圣人以沖虛作式,賢達以撝謙為情。于是盤盂設誡,幾杖必紀。”[11]4475這也是說明古人制作欹器的目的。關于欹器的性質,賦文說它“不虛不滿,能安能危”,“體執謙損,性尚沖撝”[11]4475。晚唐武宗時期宰相李徳裕作《攲器賦》,描述欹器“虛則臲卼,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則跌,霆流電發,器如坻隤,水若河決”[11]7148。“臲卼”,表示搖擺不定的樣子。賦文對欹器的虛、中、滿三種狀態做了形象的表達。此外,張元覽的《欹器賦》也對欹器作了“平而則正,滿而斯側,不平不滿,無窮無極”的描述[11]9881。另外,唐高宗時期宰相許敬宗也作有《欹器賦》,但其中主要是“人靈貴損,天道忌盈”,“務循虛而守約,處崇高而慎傾”之類的處世哲學內容[11]1536,沒有對欹器的物理性能進行描述。唐代這幾首辭賦是繼《荀子·宥坐》之后,對欹器物理性能的進一步描述和強調,有助于古人對這種器物的理解和認識。
自然界空氣的濕度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漢代人發明了一種原始而又簡單的檢驗空氣濕度變化的裝置,即在等臂杠桿兩端分別懸掛對空氣濕度變化敏感的木炭和不敏感的土、鐵或羽毛之類的東西,根據杠桿兩端的低昂變化情況以探測空氣的燥濕變化。《淮南子·說山訓》稱:“ 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10]1157-1158《淮南子·泰族訓》《淮南子·天文訓》以及《史記·天官書》也有相關表述。《漢書·李尋傳》稱:“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三國孟康注曰:“先冬夏至,懸鐵炭于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18]3182這些都是關于杠桿驗濕器的簡單描述和解釋。古人認為,自然界陰與陽的周期性此消彼長,決定了一年四季氣候的冷熱干濕變化,冬至后陽氣日盛,空氣開始干燥,炭逐漸變輕,故杠桿失衡,炭端上仰;夏至后陰氣日盛,空氣逐漸潮濕,炭因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而逐漸變重,故炭端低垂。唐代貞元十四年(798)進士王起作《懸土炭賦》,對這種驗濕器具做了比較全面的描述。賦文說:“乃懸乎土炭,有象夫權衡。惟土也葉陰氣之動,惟炭也應陽氣而生。故將法之而令出,瞻之而教成。乃左乃右,一重一輕。茍二物之不爽,知四序之攸平…… 香炭于是而善系,累土由之而畢舉。分乎多少,則無黨無偏;候以高卑,知一寒一暑。”這里既說明了驗濕器的材料和結構,又說明了其作用。不過,賦文說,冬至之后,“日北至而冱寒。于是岌岌斜指,亭亭上干。土則從輕,知眾陰之將謝;炭推持重,知一陽之已攢”;夏季來臨,“觀夫炭則高而漸危,窺夫土則垂之如墮”[11]6478。這是把炭的輕重與季節變化的關系顛倒了,即認為冬日炭重、夏日炭輕,這當然是錯誤的。導致錯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王起把土和炭分別歸屬于陰和陽,根據同類感應觀念,認為冬至之后陽氣日盛,故炭重;夏至之后陰氣日盛,故土重。這顯然是不正確的。這首賦是筆者所見到的對古代驗濕器描述得最全面的史料,盡管存在這種不足,但仍然是有價值的。
上述是古代辭賦對桔槔、轆轤、水輪、欹器等力學器械的描述,反映了辭賦作者對這些器具性能的認識。除此之外,古代還有不少描述力學器械的辭賦,限于篇幅,不再討論。
3 對聲音的認識
物體的振動在空氣等介質中傳播,從而形成聲音。唐代人已認識到聲音的產生與物體的運動有關,武則天敕撰《樂書要錄》即說“形動氣徹,聲所由出也”,并認為“ 形氣者,聲之源也”[19]2。“徹”即穿透。“形動氣徹”,即物體的運動在空氣中傳播。《樂書要錄》指出物體的運動在空氣中傳播是聲音得以產生的原因,但未說明物體做何種運動。北宋張詠的《聲賦》則對物體做何種運動能夠形成聲音做了說明,賦文稱“天機動制,軋而為聲。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小大焉”[20]578。軋,即輾壓。賦文認為,物體做輾壓運動就會產生聲音。所謂輾軋,實際上是指振動。之后,張載在《正蒙·動物》篇中也指出:“聲者,形氣相軋而成。”[21]28《動物》篇還列舉了一系列形氣相軋而發聲的例子。
關于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唐代幾首辭賦表達了新的認識。唐代張德升《聲賦》認為,聲音的傳播“遇風吹而更長”[11]9877,即順著風向,聲音傳播的距離會遠一些。唐代鄭磻隱在《風賦》中用“送夕鼓而傳音,振晨鐘而成響”說明風的傳聲作用[11]9949。王起在《律呂相召賦》中用“以氣而導聲,以聲而宣氣”說明聲音傳播過程中聲與氣的相互作用[11]6476。這些認識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對于理解聲音的傳播是有幫助的。之后,五代譚峭在《化書》中才有“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的明確表述[22]27。
關于聲音的性質,唐代張彥振的《響賦》做了比較深入的論述。賦文說:聲“ 同夫道之無質,每憑虛而起象;既不睹其洪纖,亦罕知其尺丈……觸物類以成態,托空虛以運形。爾其細也,草蟲鳴于潛穴;至其大也,震雷作于天庭。離朱拭目而不見,師曠清耳而可聽。爾其響發乎器,必聲有假。故器有盈虛,而響為高下。隨之則不可究,及之如或可寫”[11]9882。意謂聲音無形無質,無法睹其形貌;它由物類相觸而發,在虛空中運行;小到蟲吟,大至雷鳴,都是聲音的表現;聲音的形成依賴于器物,器物不同,形成的聲音也不同。這些認識都是正確的。老子《道德經》有“大音希聲”之說。唐代楊發作《大音希聲賦》,其中說“大道沖漠,至音希微。叩于寂而音遠,求于躁而道違”,“聲希者其響必大,聲煩者其理斯屈”[11]7886。這也是對聲音性質的描述,只是道理說得不夠清楚。
響,本指聲音,也指由聲音引起的回聲。唐代有兩首辭賦表達了對回聲的認識。駱賓王《螢火賦》有“響必應之于同聲,道固從之于同類”之語[23],指出響與引起響的聲音屬于同一種類型。這種認識也是正確的,因為回聲是由聲音經過界面反射而形成的,反射不會改變聲音的性質。張彥振《響賦》也指出,響“乃依聲于發,有待而生”[11]9882,即回聲的形成依賴于聲音。
樂器是古人演奏樂曲、抒發情感的器具,其發音特性與樂器的結構和材質有關,符合一定的聲學道理。古代文人創作了許多描述和贊美樂器的辭賦,如戰國宋玉有《笛賦》,西漢王褒有《洞簫賦》,東漢馬融有《長笛賦》,西晉嵇康有《琴賦》、潘岳有《笙賦》,唐代虞世南有《琵琶賦》、李程有《匏賦》、鄭希稷有《笛賦》及《塤賦》,等等。這類作品在寓言寫物的同時,也表達了對一些樂器發音性能的認識。如嵇康在《琴賦》中對琴的發音特性進行了總結:“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24]130 蘇東坡對此解釋道:“ 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庳,弦長故徽鳴。’所謂庳者,猶今俗云?聲也,兩手之間,遠則有?,故云‘間遼則音庳’。徽鳴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按,乃可泛,故云‘弦長而徽鳴’也。”[25]2095 《玉篇·攴部》:“ ?,散也。”由蘇軾的解釋可以看出,嵇康認為琴身各部分協調,發音則安逸;琴弦張得緊,發音則清亮;琴弦間距離遠,發音則散漫;琴弦長,則產生泛音。這些認識都是有道理的。塤是一種歷史悠久的陶制樂器,結構簡單,音色優雅。鄭希稷的《塤賦》對塤的形制及發音特性進行了描述,賦云:“在鈞成性,其由橐籥。隨時自得于規矩,任素靡勞于丹雘。乃知瓦合,成亦天縱。既敷有以通無,遂因無以有用。廣才連寸,長匪盈把。虛中而厚外,圓上而銳下。器是自周,聲無旁假。為形也則小,取類也則大。感和平之氣,積滿于中;見理化之音,激揚于外。邇而不逼,遠而不背。觀其正五聲,調六律,剛柔必中,清濁靡失。將金石以同功,豈笙竽而取匹…… ”[11]9946-9947 塤的制作是在陶輪上成形,在窯爐中加熱,所以賦文稱其“在鈞成性,其由橐籥”。“ 瓦合”語出《禮記·儒行》:“儒有……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26]2226 意謂儒者不卓然立異,能與眾相合。塤的發音由吹孔處的銳邊激起的氣流振動而成,中空的腔體是共鳴箱,對聲音有放大作用。腔體是空的,以道家的說法,空即是無,因此賦文說它“因無以有用”。短短數語,在贊美塤具有循規守矩、樸素無華、寬裕以合眾、因無以為用等美德的同時,也把塤的燒制工藝、形體結構、發音特點、音樂作用等都做了簡潔描述。另外,西晉潘岳《笙賦》描述了笙的發音:“泄之反謐,厭焉乃揚”[27]857;“ 惟簧也,能研群聲之清;惟笙也,能總眾清之林”[27]861。鄭希稷的《笛賦》描述了笛子的發音:“引氣內填,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聯復絕。”[11]9947這些認識都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形制和材質的不同,各種樂器發出的聲音也各不相同。唐代敬括的《觀樂器賦》對土匏革木樂器的發音特性進行了概括性描述,認為塤等土制樂器,“其氣混,其音吹”;笙竽等匏制樂器,“其氣散,其音吁”;鼗鼓路鼓等革制樂器,“其氣勃,其音博”;琴瑟等木制樂器,“其氣清,其音密”。[11]3590 盡管用“吹”“吁”“博”“密”來表示不同樂器的發音特性未必準確,但由此可以看出辭賦作者對樂器發音特性做出的總結和思考,這在音樂聲學史上是有意義的。
4 對火和光的認識
火苗產生熱量,也發出光,熱和光都屬于物理認識內容。古代也有一些描述火和光的辭賦,反映了古代人對二者性質的認識。
西晉潘尼作《火賦》,認為火“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 形生于未兆,聲發于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28]2000。火不是獨立實體,依賴于燃燒物而存在,在燃燒之前和熄滅之后都無蹤跡,因此賦文說它來去無跡。賦文對火的功用做了概括性描述,如它可以“ 陶冶群形”“革變膻腥”,“流金化石,鑠鐵融銅”,等等。北宋吳淑的《火賦》述說了歷史上的一些用火典故,提到陽燧取火、鉆木取火、積油生火、然石之火,還提到了“雨里常燃”的雷電之火,也論及了火的燔物就燥屬性。[29] “然石”即“燃石”,古代傳說的一種石頭,注水后能發熱。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贛水》稱:“建成縣出燃石。”該書引《異物志》描述燃石:“石色黃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30]920 不過,燃石究竟為何物,今已很難知曉。
古代有四時變國火的習俗。《周禮·夏官》有“司爟”之官,負責“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31]1157 唐代王起作《鉆燧改火賦》,賦文不僅論述了四時鉆燧改火的道理,而且形象地描述了鉆燧取火的過程:“爾其鉆也,勢若旋風,聲如驟雨。星彩晨出,螢光夜聚。赫戲郁攸,赩熾振怒。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焰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11]6473然后說,“其初也,鉆一木而挺英;其大也,燒萬物而為燼”;“其猛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并說它“輝赫赫而不滅,性烈烈而自馳”。[11]6473 這些都是對鉆燧取火過程及火的性質與作用的描述。王起在《取榆火賦》[11]6472-6473 中也對鉆燧取火過程做了形象的描述:一有“鉆之彌堅,初若切磋之響;動而愈出,俄生煒煜之光”。二有“運手而綠煙乍起,屬目而朱焰可觀”。三有“紅星忽迸,不異乎種天之星;朱火既飛,詎同乎敲石之火”。四有“馀燼收之而有耀,死灰然之而孰難”。鉆燧取火是古人生活中比較常見的活動,但古代一般文獻卻很少對取火過程做詳細描述,王起的這兩首辭賦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古人在生活中會觀察到各種燃燒現象,對不同種類的火的性質也有所認識。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火部》中對各種燃燒現象進行了總結,將火分為陰陽兩類,凡十二種,并指出兩類火具有不同的燃燒屬性。清人陳夢雷作《火賦》,將《本草綱目》所述火之內容以簡潔優美的辭賦語言加以表述:“天陽火二,太陽星精。天陰火二,龍火雷霆。地陽火三,鉆木以興,擊石而炳,戛金而熒。地陰火二,石油水上。人之陽火,丙丁君象。陰火亦二,命門為相。三昧之火,與相同旺。陰陽各六,十二名狀。分天地人,其義始暢。陰火不焚,爍石流金,遇濕反熖,遇水不侵。撲之以灰,光焰乃沉。陽火能熱,遇木乃烈,可以濕伏,可以水滅。”[31]341《火賦》的內容雖然未超出《本草綱目》,但語言簡潔,押韻上口,有助于這種知識的傳播和記憶。
光是一種常見的物理現象。不過,古代很少有人對光有過關注,因而一般典籍中少有記載。唐代甘子布作《光賦》,對光進行了專門討論。賦文認為光的功用玄妙,道理深奧,因此稱它“功斯玄,理斯妙”;并指出光“原夫陽之化,陰之融”,由陰陽變化而成。關于光的性質,賦文做了多方面的描述,說它“明滅靡定,虛無罕測”;“寄方圓以分影,逐玄黃以變色”;“逗幽隙而露纖埃,漏疏林而分細影”;“從盈空而不積,雖駿奔其如靜”;“雖視之若溢,而攬之不盈”。還說“遇蒙則戢,因通則揚。乘物無聯,適變無方。大則彌于橐籥,小則細于毫芒”。橐籥原指用于冶煉的鼓風裝置,這里指空間。這些表述說明,光無實在的質體,明暗可變,形態不一,可以感知,難以測度。關于光的作用,賦文說“ 惟茲光之焴爚,辟重昏以臨照”,“ 沈凝者顯象,清貞者流曜”,“鑒無隱而不彰,狀雖空而可識”,“稱物咸燭,呈形被景”,“開暗空于千里,徹夜宮之九重”[11]2628。這首賦對光的形成道理、性質、作用等都做了初步論述,反映了當時的認識水平,堪稱一篇古代光學論文。
螢火是一種冷光源,有微弱的照明作用,因此古代有車胤“囊螢夜讀”之說。唐代駱賓王作《螢火賦》,對螢火做了比較全面的描述。賦文稱它“既發暉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意謂螢火既向外發光,又自身透明。螢火之光的亮度有限,只有在夜晚才可以看得到,因此賦文說它“均火齊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乍滅乍興,或聚或散”;“ 曳影周流,飄光凌亂”。還說“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并說螢火雖然“ 光不周物”,但“ 明足自資”[23]208。這些描述既形象又具體,對于認識螢光現象是有幫助的。
物體被光照射時,會在背光處生成陰影。唐代謝偃作《影賦》,對影的性質做了比較充分的描述。影不是物質實體,無固定的形質,因此賦文說它“體無定質,應變隨方;因物成象,不拘厥常”。又說它“含虛無以成體,故日中而不見”,所謂“日中不見”,是說影遇到日光照射時就看不到了。影的顯與隱取決于是否有光照射在物體上,有光則一片光明,無光則一片晦暗,因此賦文說影“ 在清明而必朗,若晦濁而斯亡”。《莊子·漁夫》有一則寓言,說一個人為了擺脫自己的影子而“疾走不休”,以至于“絕力而死”。寓言批評此人“不知處陰以休影”[7]585。謝偃《影賦》也指出,影“往來絕跡,出入無間,走不可避,速不可捐”。“速不可捐”,意謂人不能通過快跑的辦法來拋棄自己的影子。物體在日光照射下,投影的長度會隨著季節的不同而變化,因此《影賦》說影“同寒暑之延促,故夏短而冬長”。人們晚上面對明月,身影會在背后;白天背對太陽,身影會在面前。《影賦》描述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向夜月而處后,背朝日而居前”。對于影的這些性質,《影賦》作者是難以理解的,因此發出“非可以智察,難可以理詮”的感嘆[11]1593。《影賦》對影子變化情況的描述和總結都是正確的,反映了作者對這類現象的認真觀察和思考。
物體受光照射時會形成陰影,在陰影區域外圍與明亮區域交界處會形成一層模糊的微暗輪廓,古人稱之為“罔兩”,認為它依附于陰影而存在,是陰影的附庸。日常生活中,人們不會留意這種現象。由于《莊子·齊物論》有罔兩問影的寓言,因而這種現象引起了古代文人墨客的關注。唐玄宗天寶六年(747)丁亥科考試,試題即為《罔兩賦》。從現存的文獻可知,唐代李澥、石寬、蔣至、包佶、孫鎣等都作有論述罔兩的辭賦。這些賦文多以道家尚無貴虛的觀念論述罔兩的性質及其與影和形的關系,其中有些表述也含有一定的光學道理。如蔣至的《罔兩賦》稱罔兩“邈兮難名,混兮不測。離婁目眩而方見,桑宏心計而寧識。其出也與影俱游,其入也與陰俱息”[11]4164。意謂罔兩形態混暗模糊,需仔細觀察才可看到,它依附于陰影而存在。孫鎣的《罔兩賦》稱罔兩“呈纖微之虛質,揚太陽之杲杲”,“ 以影為典,以形為則”,“ 謂為無也,雖微而必有;謂為有也,雖可名曰希”[11]4432。這是說明罔兩形微質虛,有無難辨,以物和影為存在的根據。
露珠在日光照射下會產生色散現象,呈現五彩繽紛的狀態。唐代白行簡、王起、賈餗、袁兌等都作有《五色露賦》,其中賈餗的賦對這種色散現象的描述最具科學性。賦云:“ 露彩呈祥,厥狀非一。表四方之具慶,故五色而俱出。間朱青以騰文,雜玄黃而成質。……究其原兮則一,分其色兮惟五。”[11]7540賦文不僅描述了露珠顯現的五彩斑斕狀態,而且其中“究其原兮則一,分其色兮惟五”一語,指出了露珠呈現的五色是源自一種光——日光。賦文指出露珠的五色來自日光,這是難能可貴的。這可能是明確指出露珠五色源自日光的一條比較早的文獻。此后,南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才更明確地說,露珠“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32]143。
金屬鏡是生活中常用的光學器具。古代文人創作了不少描述鏡子成像的辭賦作品。西晉傅咸作《鏡賦》,其中稱鏡子照物“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于妍丑,而眾形其必詳”[33]1227,意謂鏡子成像,不分美丑,應物無方,能夠客觀地反映被照之物的原貌。唐代一首佚名作者的《古鏡賦》也稱明鏡照物“圖象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發不形”[11]9866。這些認識都是有道理的。透光鏡是古代的一項技術發明。目前所見關于透光鏡的明確記載是隋唐之際王度的《古鏡記》,其中說隋汾陰侯生持有一枚古鏡,此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盡入影內,纖毫無失”[34]。北周庾信《鏡賦》描述一面古鏡,背上“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它“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35]86。戴念祖先生認為,“照日則壁上菱生”表示鏡面承日所照,投射到墻壁上的反射光區中出現了鏡背面的圖案;“菱”即菱花,指鏡背圖案,因而這可能是中國古代關于“透光鏡”的最早描述[2]694。由此即可看出這首《鏡賦》的學術價值。
另外,古代一些詠鏡詩描寫佳人照鏡時,也揭示了鏡面反射成像的一些特性,如梁朝王孝禮《詠鏡》詩曰:“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33]1237 其中,后一句說明鏡面反射成像時,像與物具有平面對稱關系。平面對稱的特點是像與物左右位置互換,所以人做各種動作時,看到自己像的動作是“逆相同”。唐代張文恭《佳人照鏡》有“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36]505 之句,形象地說明了有形的實體可以由鏡面反射成像,而無形的聲音無法被反射成像。這些描述都是符合物理道理的。
5 結語
古人留下了大量辭賦作品,其中不少辭賦含有一定的科技內容,以上所述僅是舉例性介紹一部分與物理認識相關者。趙自勤的《空賦》、王契的《桔槔賦》、仲子陵的《轆轤賦》、陳廷章的《水輪賦》、張鼎的《欹器賦》、王起的《懸土炭賦》、張詠的《聲賦》、張彥振的《響賦》、嵇康的《琴賦》、鄭希稷的《塤賦》、潘尼的《火賦》、甘子布的《光賦》、謝偃的《影賦》、賈餗的《五色露賦》等,對空間的形態及特性、力學器械的形制與性能、聲音的形成與傳播、樂器的結構與發音、火的特點、光的性質、影的變化、露珠色散現象等的描寫和論述,既具有特色,又富有新意,有的認識水平比較高,有的認識時間比較早,有的認識比較全面,具有顯著的學術價值。此外,古代一般典籍中的物理學史料基本上都是以只言片語的形式雜存于表述其他內容的文字中,少有專門論述物理內容的篇章,而辭賦則不然,各種《時賦》《空賦》《聲賦》《響賦》《火賦》《光賦》《影賦》《鏡賦》等都可謂是論述物理現象的專門篇章,可以作為古代專門的物理學史料看待,只不過其中含有頗多抒發文人情懷的內容。
最后尚需指出,辭賦畢竟是一種文學體裁,受語句對偶、聲韻和諧、辭藻華麗等表達風格的限制,雖然不乏意境優美、情文并茂的佳句,但總體上對一些物理內容的描寫和論述過于簡略,不夠準確。這種文風既影響了作者對一些物理內容的客觀表達,也不利于讀者對一些內容的準確把握。這是辭賦體裁用于描述自然科學內容所具有的弊端,因為科學內容的表達要求的是翔實、明白,而不在于言辭華美。
[責任編輯 黃祖賓 楊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