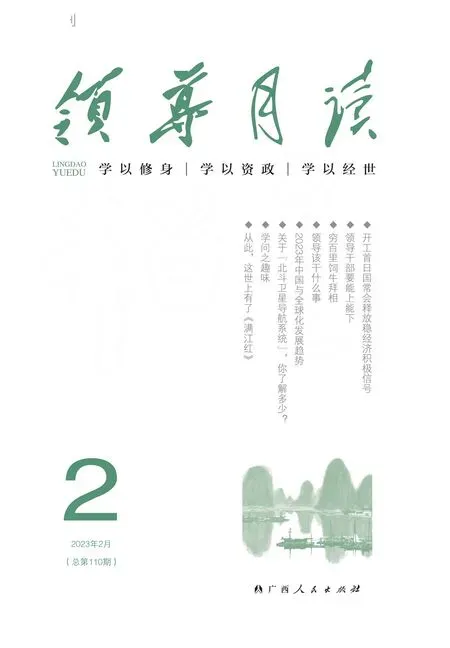晉書·宣帝紀
[唐]房玄齡 等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云。飾忠于已詐之心,延安于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于百日,擒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斗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無殉生之報。……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后昆,而身終于北面矣。
(原文據中華書局1974年版《晉書》)
【譯文】
皇帝李世民評論說:天地之大,以黎民百姓為本;一個國家以國家元首最為尊貴。和平與戰亂變幻無常,興盛衰亡卻是有時運的。哪怕統治萬乘之國的五帝也以此為憂;三王以來,身處憂患卻以此為樂。比拼智力,爭權奪利,大國小國之間相互吞并,強國弱國之間彼此侵襲。直至魏時,三國鼎立相峙,戰爭連年不息,到處一片混亂。晉宣帝以卓越的天姿才能,順應時運輔佐帝王,文能治政,武能克敵。司馬懿用人就像用自己,從不生疑,求賢若渴,唯恐不及時而錯過賢能;情感深沉不可測,性格寬厚能容人。他隨俗而處不露鋒芒,順應時勢,屈伸舒緩,斂鱗藏翼蓄志待時,隨時關注風云變幻。司馬懿把自己的狡詐之心隱藏起來裝扮成忠誠的樣子,在危難之中求得平安。他的雄才大略決斷于內,英明策劃決斷于外,在百日之內消滅了公孫文懿,用十天左右活捉了孟達,用兵如神,計謀無比。他隨后率領大軍西討,與諸葛亮相持。司馬懿控制其軍隊,本不想打仗,諸葛亮送給他女人的服飾,他這才下了戰斗的決心。使者持節在門前阻擋,雄心抱負頓時收回,千里之外求戰,無非是想顯示軍威。況且秦、蜀兩地的士兵,勇猛強悍和膽小怯懦對比懸殊,兩軍地勢一個道路平坦與一個地勢險峻,兩軍一方安逸和一方勞苦,以此來爭功取勝,司馬懿的部隊明顯占據有利形勢。然而司馬懿卻閉營不出只一味加固工事,不敢出戰,諸葛亮活著的時候,他因為懼怕諸葛亮而不敢進攻,諸葛亮死之后,看到諸葛亮的畫像,懷疑其有詐而退守不攻,他優秀將帥的謀略之才,在此刻就顯得遜色了!魏文帝之世,輔佐朝廷而權重,司馬懿在許昌受到了同當年蕭何一樣的重托,在崇華殿上得到了超過霍光所得到過的信賴。如果竭盡忠誠義節,他可與伊尹、傅說齊名。及至魏明帝臨終之時,把國家大事相囑托,他接受了兩位君主的遺照,輔佐了三代,既然承受了臨終前的重托,卻沒有以身相報。……即使是道行感動了四方,恩德遍布于眾生,但是上天尚未開啟時機,天子寶位還有阻礙,不能用智慧去競爭,不能用強力去奪取,雖然是福澤流傳于后代,自身卻一直北面稱臣。
【簡析】
《晉書》由唐太宗時期房玄齡、褚遂良等21位大臣編撰而成,唐太宗本人在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的本紀及陸機、王羲之的傳記之后分別寫了四篇史論,是為《制曰》。從李世民對司馬懿的這段總評來看,內容全面深刻,觀點既一針見血又高瞻遠矚,文字平正大雅、入骨三分,警醒十足。李世民在面對司馬懿這樣一個復雜人物之時,也是如臨大敵,凡出論斷、下文辭都經反復琢磨、推敲,務求切中要害而又避免過甚其詞。李世民這一段對帝王的評論,雖然見識和文辭均屬上上之品,但有些地方顯得滯塞、突兀。想必唐太宗蓄意為自己很感興趣的著名人物撰寫“總論”之時,也要常與房玄齡、褚遂良等人商討論辯,征求意見,反復修改,這才形成了處處文辭閃光、內容又經得起檢驗的中肯客觀的評論,堪稱晉宣王定評,足以流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