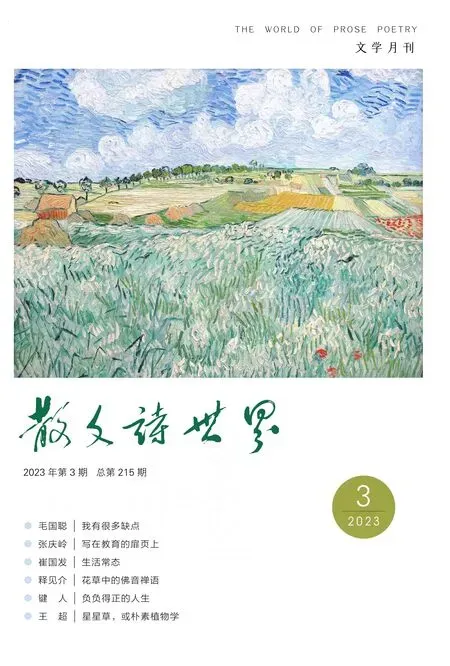甲板的幻象三章
2023-04-15 17:12:36獨孤赟吉林大學
散文詩世界 2023年3期
獨孤赟(吉林大學)
浪漫主義的六月船歌
我在冬日里時常想起,他,半個漁夫。
漫游于土壤和海洋之間,陌生又熟悉,徘徊游離。
獻給自然的旋律里,是他前半生的不羈,以及寓言式的自嘲。
在望不到岸的時候,度日如年。
破漏的船,是他珍視的寶物,刻滿字符的甲板,是記錄生計的片段,我以為,不過如此。
斑駁的痕跡,是魚叉下的歲月
……
海是存在主義的意義王國,海是唯美主義的純粹超然,海是神秘主義的意識經驗。
海是無盡的邊界,給予我尊嚴。
剩下靈魂扮演的角色,是另一重景觀的真實。
對抗者,“在悲傷中歡笑,與死神調情。”
只要內心足夠篤定,就能在風暴前迎接死亡。
對尚未滿足的渴望,標示生命的注解。
他來信說,海是六月那晚,我們數星星時,一起聽的船歌。
甲板的幻象
他通常在風和日麗的時候講起,那音信全無的同鄉身臨其境的往事。
那是匯集所有語言才能描繪的絕望。
秀色可餐的七色海,溫和地出現在沒有云朵的時候,邀請不知情的人做客。
抒寫英雄的史詩,把征服寫進美好的傳說,把經驗講成必經的歷程。
專注、沉醉、貪戀海洋,與受自由的蠱惑無異,淪為生命流逝的加速器。
快樂和快感之間,一時分不清美和欲望。
尚未確定,是波塞冬的使命,還是一次普通的襲擊。
鑰匙遲疑地留在海底最深處,而桎梏靈魂的枷鎖,卻被船運到了遙遠的天空。
波浪是風的附庸,不停地掙扎、擺脫月亮的牽引,卻不得不反復地認錯。重蹈覆轍,是黑暗的同色。
泡沫是故事的全部內容。
他,苦于談及過去。
海的時空
銀河是一片淺灘,看得見每一粒沙子。
清澈見底的海,找到丟失的那枚記憶。
在拋物線的弧度里,計算,光年或毫米的距離。
眼中釋放的光,剛好對沖在最亮的結點,成為馬里亞納的一抹余暉。
數字在物質中顯得沒有風度,刻板的,固定化,一副老態龍鐘的模樣。
你說科學不逾矩,時空不可逆。
執著于浪漫的人,不可獨活。
你在深海,我在彼岸。
一眼萬年也短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