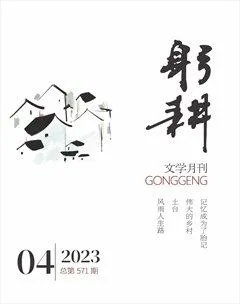淯水上的橋
陳鵬飛
知道南陽,是在翻看小說《三國演義》章節里的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知道南陽,是南陽有一所醫圣祠,擴建修復這座豐厚歷史內涵建筑的不是別人,正是出生在南陽南城門白河邊上的建筑大師楊廷寶先生。
那個年代,楊廷寶、梁思成、茅以升、崔宗培都是建筑界和水利界的大咖級人物。以建筑見長的楊廷寶、梁思成設計建筑了南京城和北京城聲名顯赫,以橋梁規劃設計見長的茅以升則主持建造了錢塘江大橋和武漢長江大橋而名滿中外,以水利工程建設見長的崔宗培參與主導設計葛洲壩、長江三峽、黃河小浪底和南水北調水利工程而載入史冊。
橋的功能其實很簡單,沒有那么復雜,建橋的目的就是為了使障礙和溝渠變坦途,便于出行,利于社會進步和城市發展。歷經塵煙,記錄變遷,一座橋的出現就是一種全新生活方式的開始和環境的改變。
站在獨山之巔,遠眺東北湍流的白河向南泄流,口中輕輕吟誦著李白《送友人》的佳句: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仿佛思緒回到了久遠的唐朝,這城郭,這白水,雖已歷經上千年,依然還是美不勝收。
這條白河,古稱“淯水”,亦稱“育水”。《三國演義》第十六回“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淯水”即是出自此處。發源于八百里伏牛山南麓,經嵩縣、南召縣流入南陽市區,穿市區而過后再流經新野、湖北襄陽,匯入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最終奔向萬里長江。
從當年進入南陽城區上學,再到河南省會鄭州上學和工作,多少年來,每次回到這里,都是要穿越白河跨橋而過的。
白河從上游鴨河水庫奔瀉而來后進入南陽市區,自東北向西南,自成半環形穿市而過,似一條銀綢素帶,波光閃閃,堤、林、路、島、橋、水相互協調,相映成趣,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自然生態系統,也成為南陽市區一道亮麗的旅游風景線,更是成為對外的一張生態名片。
白河的歷史有多少年,確切說并沒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但白河上的橋,是有數據可查的。
白河橋的這個名字,在我的成長記憶和歲月中是最為深刻的。1965年建成使用,2007年又重新建設使用,這座橋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味。
還是孩童的時候,那個時候村里的交通很偏僻,就沒有走出過鄉里的小山村,最遠就是鄉政府所在地的街上而已。雖沒有見過外面世界,但已經知道“白河橋”這三個字和名字,至于白河橋到底在哪里,那個時候就知道是在南陽城區里,可是沒有見過,更沒有走過。能見到最多的就是在一個小小的煙盒外包裝上,一個橢圓形的煙標圈著了一座河上的橋,這種香煙當時的名字就叫“白河橋”。
字面直觀的理解這就是一座橋,這完全沒有錯,因為在白河上建了一座橋,起名白河橋,白河橋是千萬南陽人一生中不能忘卻的一個年代符號和名稱。而另外一層含義里,它則是一款純粹的香煙名字,那個年代還真是家喻戶曉,名聲很響。至今我還能清晰地想起來,父親帶著我們下地干活,中途勞動休息時,他往往就會從煙盒里拿出一支白煙噙在嘴里的場景。
伴隨著改革開放那年出生的我,長這么大第一次進城離家三十多公里,見到白河橋就是在南陽上學的那一年。1996年的那個秋日,落日的余暉還沒有散去,一座橋在斜陽的映襯下矗立白河兩岸,我來到心中向往已久的白河橋上,站在這座橋上,來來回回走了兩趟。心里在想,哦,原來這就是白河橋呀,白河橋就是這個樣子,從那一刻起,算是有了走進城市的經歷,三年上學時光留在了這座古城中。
老子《道德經》第八章曰:上善若水。但凡有水的地方,就會有橋的存在。
如今,白河上除了白河大橋外,整個白河水域里還建有多座橡膠壩,水域面積大增,寬闊的水域,清澈的碧水,形成了天水一色的壯觀景象。
在南陽城區,幾座橋從北向南,依次為南陽大橋、光武橋、白河橋、仲景橋、淯陽橋、臥龍橋、雪楓橋。在這幾座橋中,名字都是有人文內涵和文化歷史的,其中的淯陽橋則是最有故事情節的一座橋。
保留淯陽橋的名字,就是為了保留住南陽古城南門淯陽門的歷史印記,特地留下這座文化城市的內涵和底蘊。以前的南陽城,淯陽門是白河的一古渡口,在這里乘船是可以揚帆到漢江,通達長江,最終進入到海上絲綢之路的。
去年有段時間能不時看到,淯陽橋新橋將在7月1日正式通車的新聞報道,當年題寫淯陽橋橋名的書法家周清渭老先生,今年雖已75歲高齡,得知我要寫淯陽橋的文章后,特地手繪了一張南陽白河段諸橋名略郵寄到鄭州供我詳讀,以此來表達對老淯陽橋的追思和紀念。
新建好的淯陽橋通車后,這里已經成為了一處網紅的打卡地。臨近年關,臘月二十這天的清晨,我在南陽出差,坐著45路公交車穿行在寬敞的淯陽橋上,看著橋下一河澄碧的清波,心中的情思久久揮之不去。
可以想象到,站在這橋上,倚欄遠眺,陣陣清風,淼淼淯水浩浩蕩漾,橋的風景,橋的精彩,全在這一城繁華的白河兩岸。
責任編輯 胡文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