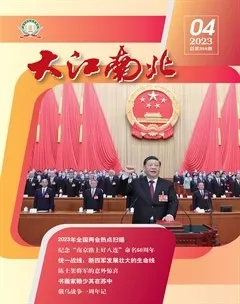謝覺哉倡導學以致用讀書法
錢國宏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謝覺哉,一生勤奮好學,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他始終手不釋卷,孜孜以讀。在長期的讀書過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的見解:不斷“補讀”,學以致用。
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謝老一直勤讀不倦。作為“延安五老”之一的他,對黨所安排的工作,保持著虛心態度和認真精神,通過增加讀書量,來不斷為自己“充電”,以彌補自己的欠缺。
謝覺哉常常思考:讀書,到底要怎樣讀?應該讀哪些方面的書?經過反復琢磨,謝覺哉覺得“補讀”很重要,因為他在工作過程中發現:每個人工作所需的知識千頭萬緒、處于變動中,若想全部掌握是很難的。因此,不僅要預先讀、時時讀、保持學識上的與時俱進,而且要對沒有學的內容進行“補讀”——搞清自己在哪些方面、領域存在不足和欠缺,然后有針對性地進行閱讀和補學。
他常常對身邊的同志說,讀書要堅持學以致用、多讀好書、持之以恒。首先,讀書對工作要有所幫助,“積累知識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搞好工作。”其次,讀書要注重消化吸收,多讀讓自己受益的好書。最后,讀書要持之以恒,點滴積累。
一次,一位年輕人因為平時忙忙碌碌,讀書很是雜亂無章,就專程請教謝覺哉。謝老沉吟片刻說:“你可以試試,晨思夜讀。”隨手就寫下了“晨思夜讀”四個字“。為什么要晨思呢?因為晨是一天的開始,在新的一天開始時不要急于做,而在于計,所謂一日之計在于晨,計就是思。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什么呢?你可以結合工作的特點去思,你覺得自己常常是雜亂無章,那就思如何才能變為有章,使工作效率高一些,一天抵兩天用,思的目的在于多得。夜讀,是根據你工作的特點,白天忙于工作,就得利用晚上,每晚抽它一兩個小時攻讀,長期堅持下去,不就有個完整的時間了嗎?時間對一個人來說是少,也是多的,會擠時間、會利用時間的人,可以把少變成多。相反,給你再多時間,你不去利用,就是少的。思是必要的,但思而不學則殆,危險!學而不思則罔,同樣也無用。思要讀,讀促思,讀得多,思則廣,思越廣,讀得多就更好。晨思夜讀是相輔相成的。”這個年輕人按照謝覺哉所說的讀書方法,果然后來有了很大收獲。
1948年8月,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謝覺哉擔任政府委員、司法部部長。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辦司法訓練班,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司法干部。他堅持親自寫講課提綱,并每天講課3個小時。新中國成立后,謝老兼任新中國第一所政法大學的校長,為全國培養大批司法干部。這期間,謝老又是把“補學”融入到了自己日常的每一天。
1959年3月,謝覺哉當選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到任后,他先是通過“補學”,使自己成為“行家”,然后提出要恢復法院的正常審判制度,把案子辦得更準確、更細致、更踏實,做到不縱、不寬、不漏、不錯。為實現這些要求,謝老不僅親自辦案,典型示范,還深入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親自看案卷,實行“實地補學”,從而在全國范圍內糾正了不少冤假錯案,使法院這一專政工具,更有力地打擊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護了人民的正當權益。
活到老,學到老,學以致用,是謝老的一貫讀書主張。逝世前幾年,謝老因腦血管栓塞導致半身癱瘓,右手不能動。在病榻上,他仍堅持學習。由于不能久坐,他就讓人買了一個放樂譜的鐵架子,把書放在架子上,頭靠著椅子閱讀。夫人王定國勸他少費神,說在病中看了書也用不上。謝覺哉回答:“怎么用不上?有人來問,我可以講。自己看得深一點,對人講得就會透一點。”
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之一的林伯渠曾這樣贊譽謝覺哉:“清詞如海復如潮,健筆春秋百萬刀。”謝老一生讀書不倦,不矜不伐,給后人留下豐厚的精神財富:從“五四”運動到逝世前,他留下了100多萬字的日記、1000余首詩詞和數十萬字的《謝覺哉文集》,并且成為新中國著名的法學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學界的先導、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