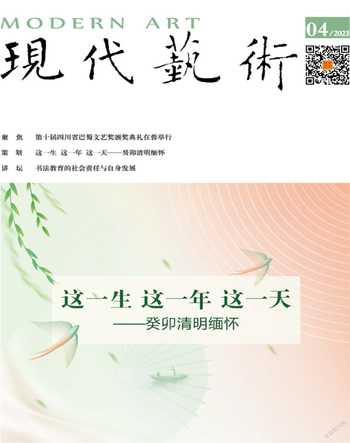樓頂曇花
黃紅軍
劉爺爺和王婆婆冬天要到兒子家過冬。他們一般在深秋或初冬啟程,走后樓頂的花草就拜托給我照料。曇花栽種在他們家樓頂的一個大花盆里。
劉爺爺是我大學畢業剛到單位時的領導,大名劉尚樂,時任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四川分會秘書長。有他本人在場,我們都規規矩矩叫他劉主任。本人不在時則稱老劉,有時候還得直呼其名,以便和別的老劉相區別。劉爺爺是隨著年歲的增長,在我們這代人的孩子出生后他獲得的一個更高級別的稱謂。
劉爺爺生于1931年8月,湖北鐘祥人,1947年漯河解放時參加中原野戰軍四縱10旅,1949年在粵桂邊戰役中立大功一次,1951在昆明立大功一次,1953年調13軍政治部干部處,1961年底任干部處副處長,1969年調13軍37師110團任副政委,1969到四川省委支左,任四川省委政治工作組組織副組長,兼三處處長。后回部隊,1981年轉業到四川省文聯,先后在文聯辦公室和民協工作。
部隊駐扎云南的時候,劉爺爺邂逅了彌勒縣姑娘小王,并結為伉儷,養育有一雙和我們差不多大小的兒女。小王姑娘現在已經是婆婆級別,我們都叫她王嬢。1986年7月,我到文聯報道時沒見到劉主任。其時,作為全國十大藝術集成志書之一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正在開展大規模的普查搜集。后來聽早我一步到協會工作的同事們說,我報道時劉主任正帶領他們在甘孜、阿壩采錄民歌,搜集故事。很快,我也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去過馬邊、平武、松潘、紅原等諸多地方采風。和劉主任共事的五六年間,他一直保持著部隊的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等光榮傳統,跟他一起去出差,基本上都是乘坐火車、公共汽車等交通工具。到川西高原藏羌地區去采風,同事們還和他一起搭順風車,坐手扶拖拉機。20世紀80年代,電視機還是個稀罕物,不是每家招待所的客房里都配得有,晚上閑聊時,他不止一次跟我講過去打仗的事情。我好奇他是否親手消滅過敵人,而他對這個問題總是不正面回答。他說,打仗才不像電影里演的那樣呢,電影是編的,那是藝術創作。
1992年,單位拆舊房蓋了一棟宿舍,已經退休的劉爺爺終于分到一套緊湊的四居室,不過是在七樓,再上面就是樓頂了。也正是得這樓頂之利,他和王孃才有了后來建設屋頂花園的場地。六十出頭的劉爺爺和王孃并沒有把爬七樓視作畏途,新家吸引著他們,就如辛勤的蜜蜂一般在樓道里進進出出,腳底下充滿了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就在這種美好的憧憬中,一盆盆花草伴隨著汗水滴落,有些是同花盆一起,有些則盆是盆,苗是苗先后上了樓,最終按照主人的旨意在樓頂的四周占好位,扎下根。進門的一個大盆里栽種的是一株黃角蘭,手腕粗細,雖還沒能枝繁葉茂,但開起花來一點也不含糊。從五月起在長達半年的花期里,它讓經過樓頂的風也充滿了馨香。曇花種在金銀花棚下的一個大陶盆里,蓬蓬勃勃一大籠,新長出的葉片都快夠著花棚了。有陽光的日子,光線透過金銀花的藤葉,撒在曇花油綠的葉片上,讓人的心也跟著亮堂。
在幫劉爺爺照料樓頂的花草之前,我對曇花的了解僅限于“曇花一現”這個成語。曇花長什么樣?一現到底有多久?則是相當模糊。但對生長于云南的王孃和曾在云南戰斗生活過的劉爺爺來說,曇花就像牧人心中的格桑花、馬蘭花,播在小園里,開在心田中。我曾留心觀察過兩位老人所種植的花、草、樹,除了已經寫到的黃角蘭、曇花、金銀花外,還有鐵樹三五株,銀杏、廣玉蘭各一株,大多帶有彩云之南的印記。
此前,王孃已多次邀我們上樓去觀賞曇花開放,由于要等,怕時間久了影響他們休息,一直沒去。后來上樓去澆水,見有花蕾萌出,心里就莫名的充滿了期待。在錯過好幾次曇花開放后,終于有一次機會,親眼目睹曇花開放。那年雨水豐沛,曇花枝葉長勢喜人,頭批花蕾萌發后我初略數了一下,竟有二三十個之多。幾天后的一個早晨,當我打開樓頂的房門,金銀花棚下的景象著實讓人吃驚,只見蓬勃的曇花枝葉上綴滿了花朵,這些花正處在不同的開放階段,有五六朵處于盛開的巔峰,有七八朵正在走向燦爛,大部分則激情漸退,欲語含羞。花香在樓頂彌漫,與門口的黃角蘭聯袂,讓樓頂氤氳一片。現在回想曇花綻放的那一刻,花瓣潔白、花絲玲瓏剔透、花藥鵝黃、花蕊纖毫畢現,純潔無瑕,真的是世間大美。
在侍弄樓頂花草的同時,劉爺爺的藝術園也筆耕不輟,他與人合作,寫作并出版了《懸掛在冰峰雪嶺上的馬道》《戰將楚大明》等書籍。樓頂的曇花現已被我分種移栽,在我現在的屋頂,在老家夾江,年年花開不斷。花種生根的地方,亦或是下一個輪回的春天。
(作者為劉尚樂下屬、同事、晚輩,四川省文聯民間文藝家協會駐會副主席、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