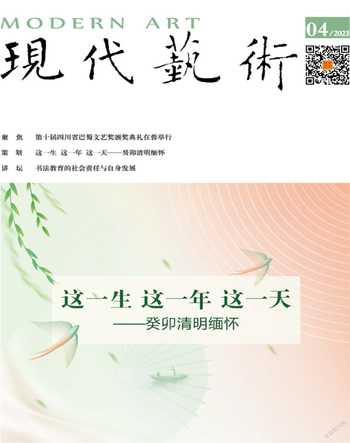鋒芒不掩 其文未湮
何民

2022年12月22日,這天是冬至,一個噩耗傳來,尊敬的張湮伯父走了。悲傷的淚水還在心中未干,轉眼清明節又到了,哽咽之時,一些記憶的文字不由自主地跳出筆端。
張湮叫我和及時君為賢侄,不光是我們和他子女親如兄弟姊妹,更多的是他對我和及時君在文字上的教誨。往事悠悠,張湮伯父擺龍門陣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
記得那年從都江堰檔案館得到一張《青鋒》報影印件,石印,16開小報,雖然年代久遠了,報上的字跡有的已經模糊了,但是報頭“青鋒”二字仍然那么剛勁有力,閃射著青春的活力。主編就是張湮。當我們把這張《青鋒》報的影印件給他看時,“青鋒”二字讓這個老報人激動地打開了歲月的記憶。
《青鋒》報是抗戰時期灌縣(今都江堰市)創辦的一份小報。
張湮先生主編《青鋒》報時,正是中國抗日戰爭處于最艱苦的年代。
在當時,作為全國抗戰的大后方,四川不僅有幾百萬將士出川,走上抗日前線浴血奮戰,還向全國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壯丁和錢糧。而留在后方的川人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支持和支援全國的抗戰。在灌縣就有一批熱血青年,如羊村、馬仁海、鮮裕龍、陳道謨、許伽等,他們雖不曾拿起槍桿子走上抗日前線,但他們用手中的筆為武器投身抗日戰場。陳道謨、許伽在成都聯絡安旗、賃常彬等辦起了抗戰文藝刊物《揮戈》;羊村、馬仁海、鮮裕龍等則在灌縣柳街創辦宣傳抗戰和進步思想的刊物《文藝堡壘》。
在全民抗戰愛國思想的影響下,正在藝專讀書的張湮也坐不住了。1941年他回到灌縣,在堂兄張瑞渝的鼓動下,他和幾個熱血青年在灌縣南門城門洞的墻壁上辦起了宣傳抗戰的大型墻報,一時間成了轟動縣城的大新聞。張湮回憶說:“我簡直成了主筆,從設計刊頭到編排繕寫,文章占了一半,在南門城門洞張貼了一大版。涉及的內容既有抗日殺敵的故事,又有歌頌都江堰的百行長詩,既有版畫,又有水墨,內容豐富多彩,是縣里空前壯觀的精彩大壁報。”
張湮先生的寫作、繪畫才能得到了鄉人的首肯,17歲那年(1941年)他就被聘到灌縣民眾教育館(相當于現在的文化館)當了一名干事,從事群眾文化宣傳教育工作。當時的民眾教育館就在現在的離堆公園內,館長叫周郁林,總務主任叫徐懋德,兩位領導都比較開明,這樣便給了青年張湮比較大的發揮空間。
在民眾教育館,張湮遇到了一位對他辦《青鋒》報影響很大的年輕人小徐。張湮回憶說:“我去后不久又來了一個有點‘獨特的人物,圓圓的臉,配上深度近視眼鏡。深入了解,才發現這個‘獨特的、二十幾歲的青年原來是共產黨人,縣里的黨組織被破壞后流亡在外,前兩年在劉文輝主政的西康省政府里躲了一段時間,終未找到組織關系又回到家鄉。他介紹的共產黨情況比許多傳說可信得多。我們很快成了朋友,除了文學,我們談得最多的就是共產黨在延安情況,共產黨的紀律、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等話題。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嚴明,比較民主。”這種進步思想后來直接影響了張湮主編的《青鋒》報。
在全民抗戰的大背景下,灌縣民眾教育館創辦了《青鋒》報,張湮任主編。“青鋒”即青年先鋒的簡稱,意思是青年要作抗日的先鋒,民眾的先鋒。當時的印刷條件十分有限,開始是油印,后來是石印(在石板上制版,一張一張地印),最后才改為鉛印。編寫人員也有限,張湮既是主編,又是主筆,整張報紙幾乎都是他一個人采、寫、編、校。十七歲的張湮正是風華正茂,在如火如荼的抗戰高潮中,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多才多藝,將一份石印小報辦得有聲有色。
張湮在他的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這是縣里出現的第一份公開的報紙,幾乎全是我一人的文章,我寫散文、報告文學,記家鄉風物,小故事。開始,《青鋒》是石印,我自寫自編,直至發行。從第三期后,這份四開的半月刊小報變為鉛印的十六開刊物了。
張湮主編《青鋒》報有一年多的時間,具體辦了多少期已記不得了。他后來離開了民眾教育館,《青鋒》報也停刊了。
從張湮的回憶中我們知道,這是灌縣第一份公開發行的報紙。《青鋒》報在那個特殊的年月一問世,就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關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它宣傳愛國思想,刊發地方新聞,鼓舞和激勵了灌縣民眾的抗日熱情和斗志。
張湮也是從《青鋒》報開始走上職業報人和文學創作之路的。
斯人雖逝,其文不湮。
(作者為張湮學生,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都江堰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