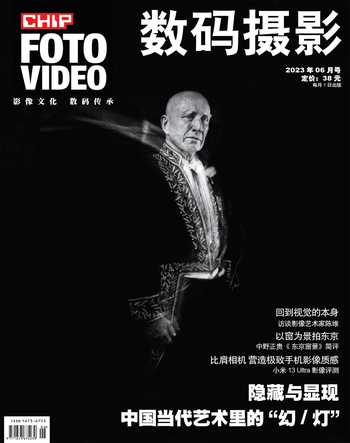回到視覺的本身
tasi



在4月28日下午,成都的氣溫變得濕潤涼爽,但成都當代影像館的學術報告廳里卻飄散著一絲緊張的氣息,第二屆“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的頒獎典禮正在這里舉辦。在典禮的現場,評委會主席栗憲庭先生講道:“本屆‘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的四位‘杰出攝影藝術家擁有一個統一的特性——開辟了新的工作方法。
他們通過攝影媒介的表達,讓人們看到今天年輕人對待現實的不同態度。其中,蔡東東創造了一種攝影裝置,讓老照片有了現代的態度;陳維的作品讓人深受觸動,通過工作室搭建出來的場景表達了城市化發展的矛盾、煩躁和焦慮;陶輝將短視頻和影像結合,避開了傳統攝影中的‘經典的瞬間,產生了陌生感……”在經過激烈而又縝密討論后,評委會最終認為:陳維的作品既有強烈的思想觀念性,也有高度的藝術性。由此,陳維榮獲了第二屆“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的大獎。
對話陳維
對于陳維, 其實我并不陌生, 早在讀書的時候就已經在關注他的影像作品了,從早期的行為記錄到房間內的簡單布景,再到工作室里的復雜景觀搭建……陳維的作品一直都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面對這些變化,自己一直都想找機會與其展開一些具體的討論,于是,借由其榮獲第二屆“金熊貓攝影藝術獎”大獎的這個機會,我們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
FOTO:您好像是攝像類的專業出身, 但現在的主要創作媒介卻是攝影,原因是什么?經過了這么多年的攝影藝術實踐后,你覺得攝影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陳維:其實,我最早是做音樂的——聲音方面,然后認識了很多杭州的當代藝術家,再然后,我們就一起參加活動,做展覽,包括跟他們一起工作………從中得到了一些經驗——好像自己不止能做聲音,也能嘗試其他的媒介,于是就發現朋友們的錄像作品很有意思,加上自己本來就有學習攝像的經歷,自然而然就有了自己創作的想法。但當時,錄像對于我個人而言還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它包含了很多東西,但攝影卻是一個比較容易實行的工具,于是,我就開始做攝影了。但做著做著就發現:作品剛完成時自己還挺滿意的,可過段時間之后,就覺得不滿意了,這就促使自己去不斷地深入。
在做了差不多10年后,我開始反思自己:是否該暫停一下?就這樣一下子做了10年,自己在其他媒介上的嘗試都比較少——雖然也做過一些現場的裝置。于是,我開始覺得:自己可能要將目光更多地放在展覽的現場,而這必將會讓自己去考慮更多裝置形態的東西。
FOTO:您的作品中顯現著一種強烈的敘事性,而且這種敘事性還是一種不完整的狀態——一種欲說還休的感覺,這種狀態/感覺是您刻意制造的么?此外,這種敘事性是否與電影有關?
陳維:我覺得這種敘事性是跟攝影這個媒介有關,它不像電影那樣,是一個非常連貫的過程,它的特點就是碎片化,把所謂的跟記憶有關的東西展開來,所以,我覺得攝影這個媒介本身可能就決定了其有一個非常強的“決定性”作用。當然,你也很難用攝影的一個定格去做一個非常完整的表達,那么,我們就把那個空間留出來好了。此外,我覺得每個定格可能都是一個視角——或者說,你可以把每個定格都想象成一個閃念,而閃念的由來肯定是一段經歷/一種印象,所以,我覺得當我們在面對碎片時,其實去面對碎片的本身就足夠了,因為完整的東西肯定會在觀者的腦海里最后完成。所以說,對于每個人而言,這些碎片就是一個個的小拼圖而已,而我也沒有想要它們來切斷什么。
對于電影,我覺得它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因為自己在大學里最喜歡的東西就是電影——雖然我們學的是電視行業,但大家的內心其實都有一個電影夢,所以在當時也看了大量的電影,然后還做了很多關于電影的作業。我覺得那段時間的訓練可能產生了很多影響,包括不同的電影導演對于畫面的處理,對于光影、調子的處理……但都是潛移默化的關系,而沒有非常直接的關聯。
FOTO:在頒獎典禮上,栗憲庭先生評價您的作品是“搜盡奇峰打草稿”,那么,對您來說,“奇峰”具體是指什么?您又如何將這些“奇峰”來進行藝術創作的轉換?
陳維:“奇峰”的大概意思可能是說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景象——不管奇特與否。我的創作方法不是用鏡頭去直接面對它們,截取它們,而是通過自己的觀看,然后在自己的創作中將自己看到的這些東西的形態/面貌進行重新編輯——這可能就是他說的“打草稿”了。這是一種工作的方法——當然,這種工作方法可能適合我,但不一定適合每個人。我不太喜歡直接攝影,因為在現場拍攝的時候會緊張,所以,自己還是要回到一個比較安靜的狀態,在沒有人催促的環境下,去慢慢地整理一些東西,創作一些東西——可能這個節奏會更適合自己。
FOTO:那么,促使/刺激您進行藝術創作的動力是什么?
陳維:我覺得是人生階段的不同。比如說,你20多歲的時候,可能更關注于自己在哪兒、別人怎么看待自己,或者說,自己要過什么樣的生活……我當時最先碰到的問題是:我要離開大學,要開始面對社會,要做一名藝術家這樣的職業……好像跟大家不太一樣,但是我沒有辦法投入到非常世俗的生活方式里,所以總是在掙扎——我不想過那樣的生活,也看不上那樣刻板與陳舊的生活,于是,就總想著表明自己是天馬行空的,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對所有結構的反對……當時其實挺朋克的。后來——2008年,我在28歲的時候搬到了北京,當時經歷了奧運會,就覺得北京的天非常藍,沙塵也慢慢在變少……所有的東西都在改善,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但在2008年年底,金融危機突然爆發了,雖然我當時對金融危機并沒有什么具體的概念,但整個社會(特別是藝術行業)的變化就發生在自己的眼前——很多人搬走了,畫廊也慢慢變得冷清……金融危機里的很多東西都給了我一些新的觸動——你好像遇到了一些新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慢慢地去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我覺得(動力)還是跟自己的生活階段有著非常大的關系,你會自然而然地關注它們,也會自然而然地感到恐懼。那么,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些問題?這些看似于社會性的、政治性的東西會跟我們越來越緊密。而且,它們其實一直都存在,只不過在不同的生活階段里,我們所面對的具體問題才會凸顯出來。所以,我在作品里就會考慮這些,我會關心事情背后的一些邏輯性和機制性的問題。當然,這些東西不會直接地投射到作品中,但是這些東西是我在創作過程中的一個基底——我是在這個基礎上來展開工作的,那在思考自己創作的時候,肯定也會受到它們的影響。
FOTO:在此次的《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獲獎作品展》中,主要呈現了您的《新城》系列作品,那為什么會呈現這個系列呢?能簡單聊聊這個系列么?
陳維:這組作品的創作時間已經很久了,本來,我計劃在2020年來完結這個系列——做了七八年的時間,我覺得它差不多完整了。在最初,城市給了我這樣一種感覺,就是作品《新城》一定要有一個彼岸,要有一個想象的存在,但在那幾年,很多東西已經開始往下走了,大家也已經失去了對于城市的想象——這是一種集體性的想象,當我感受不到那種非常強烈的、集體性的想象時,我就覺得它差不多該結束了。但是在2020年,卻剛好碰到了這個特殊的事件,那我就沒有辦法將《新城》作一個了結。
在那段時間的中段,大家都有了一種非常絕望的氣息,就好像我們在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突然之間一切都被切斷了——包括我們跟世界的聯通。當然,不僅僅是我們,那種灰暗是全世界范圍內的。所以,我就有了重新的思考:這樣的一個突發狀況——而且是一個時間跨度如此久的突發狀況——對于這個項目的影響是什么?此外,我們當時也一直在討論“全球化”的終結,這就意味著對于城市在別處的想象已經被完全地切斷了。所以,我就想之后要不要再做一點呢?在2020年年底,我就又創作了一些《新城》的新作品——雖然,這些作品里的一些是在特殊事件發生之前就有了計劃,但在那種特殊的狀態里,其所呈現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作品《新城》現在還是沒有完成,還是在持續。而且,今年的開放又是一個新的變化,這種新的變化不是計劃內的——所有東西都是在計劃之外,大家對于這種突發狀況的接受程度已經變得越來越大了,甚至已經開始麻木了。所以說,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城市又呈現出一個新的狀態……
在這兩年可能會把作品《新城》結束掉,其實它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接下來要做的也就是一些補充了——可能會將一些更能顯現人心理狀態的東西補充進來,然后,作品《新城》就結束掉。而參加這次展覽,是因為作品《新城》比較完整,也是比較近期的一組作品。
FOTO:在《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獲獎作品展》里,你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展覽呈現方式——燈箱和木框裝裱,這樣安排的原因是什么?
陳維: 自己本來是希望多用燈箱的,因為這里的空間都是黑的,如果是白空間,我反而不太提倡用燈箱。當時,我就說燈箱是最好的展現形式,但因為預算問題,后來只保留了兩個燈箱——那兩件作品必須以燈箱的形式來展現:一個是“大窗戶”,你看出去,其實就是光從燈箱的后面透進來,有一種半情境裝置的意思。雖然它比較簡易,但至少能讓大家感覺到:這是一個窗戶,可以往外看。雖然,往外看好像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看到一個模糊的城市——算是一件比較扣題的作品。另一個是一進展廳的那張“未來現代新城”,它是整個項目里最重要的一張作品,描繪了一個沒人居住的“鬼樓”,但其樓牌卻是亮的,這就顯得非常荒誕。而且,它是我在北京霧霾嚴重時期所創作的一個作品。當時,有兩個事情影響著我——一個是霧霾,另一個則是在霧霾里朦朦朧朧地看到的這些樓盤。樓都是黑的,我覺得它太荒誕、太超現實了,所以就想把它拍攝下來。于是,我將它們進行了重新設計,“未來現代新城”這個名字是我在網上搜索的——人們非常喜歡用“未來城”“新城”“現代城”這樣的詞匯,所以我就把它們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品。
另外的作品——“大窗戶”和“未來現代新城”之外的作品——在展廳中以照片的形式出現,我覺得也挺好,因為后來設置的壁紙讓它們之間有了新的呼應。而且,在設計展覽動線的時候,展覽前面本來就是比較暗的狀態,走到了后面才會逐漸變亮——因為有了燈箱。當然,如果完全讓我來設計,它會做得更復雜,但畢竟是一個獎項,要顧及其他的人,所以就簡化了。
FOTO: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從本質上講,你的作品是一種對于空間的凝固,但在展覽中,你又利用這種“空間的凝固”來制造了一個新的空間。你是如何看待這種關系的?
陳維:這就像是一個課題。七八年前,自己在創作的時候就不會考慮這么多,當時只會把照片/燈箱裝裱好,掛好,就可以了——裝置是裝置,照片是照片。后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其實很難讓大家去駐足,去在那邊靜靜地觀看作品——現代人的節奏就不是這樣的節奏,你不能將自己的意愿強加給別人。所以,我就想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例如通過改造空間,或者將整個空間視為一個裝置,然后再在這個裝置里去編排……如此,我們就不用去留人,而是讓大家能夠快速地get到一些東西,并產生所謂的互動跟交流。
此外,我覺得這里還有一個語言上的細節:展覽不只是照片跟照片的關聯,它還是一個語言——你在里面會讀到什么?當你進入一個空間,它可能是一個黑色或者白色或者其他什么顏色的環境,這樣,即使你沒看到任何的東西,但其實已經開始在閱讀和接收信息了。所以,我更加關注人們會怎么走,怎么閱讀,在閱讀過程中能得到什么?
它的里面其實是有音樂性的,對我來說,它是一個節奏,有時候我會故意地把它的中間掐斷,給它留白——這就像是一個靜止的音符,然后再走到下一個音符……但是,我又覺得這一切都是一種一廂情愿,因為我們也不知道觀眾到底會怎樣去具體地觀看。
FOTO:那么,作品《新城——桌面拼貼》里的圖片邏輯是什么?它是否是按照音樂的邏輯來進行的編排?
陳維:不全是。展覽里的那個形態其實是一個精美版的作品在工作室里的狀態。因為要為作品打樣,有時候則需要打印照片的局部——“拼貼”里面的一些照片就是作品的局部,所以,我的工作室里就會擺放很多的作品——有些是相同的,有些則是不同的;有些是作品的局部,有些則是完整的作品,有些又是作品在未裁切之前的狀態……有一天,我突然覺得它們在相互層疊后形成了一個新的作品形態,既像一個假的文獻,又像一種串聯出來的敘事。而在圖像語言的關聯性上,我有時候會讓其顯得突兀,有時候又會讓其顯得非常協調……
FOTO:能聊聊《舞池》《在浪里》《俱樂部》這三組作品么?它們似乎有一種關聯性,但各自又顯現了不一樣的氣質。此外,在展覽的現場,您其實還呈現了一張《在浪里》的作品,但展覽的標簽上寫的卻是《新城——在浪里#5》,所以,我覺得這三組作品與《新城》作品形成了一種“內外”互補的關系,它們是您對自身、對世界的兩種觀看與思考,是么?
陳維: 作品《在浪里》為什么會放在這里?我覺得:自己當年在創作《新城》的時候,《在浪里》是它的平行項目,而在創作《俱樂部》的時候,《新城》則是一個與其對應/呼應的項目。從某種意義講,《新城》是在地面之上的,而《俱樂部》其實是有點underground(地下)的味道——在夜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這些人會聚集在一起……從主題上看,《俱樂部》至少是一種熱鬧的狀態,它讓我們非常靜止/安靜的城市有了一個對照,它們形成了呼應。所以,在這次的展覽中,我就放了一張“跳舞的群像”,我覺得它可以作為作品《新城》的一個背景——而且,它也像墻紙一樣貼在了那里,然后上面放著《新城》的作品,這種畫面的交叉會讓觀者在閱讀上得到更多的信息。
在這樣的時代里, 我經常說作品《在浪里》其實是很恐懼的——它有一種自由,但更有一種恐懼,那幾年,我有一種非常深刻的感受——沒有安全感,就像自己在大海里游泳一樣。所有的人都向往在大海里游泳,因為它的風景和開闊感,遠遠超過了游泳池。但因為未知的恐懼和容易被卷走等原因的存在,在大海里游泳時你卻不敢向它的深處游,有時候,它還會形成一種暈眩感,而這種暈眩感就讓你既著迷又害怕。
那幾年,我覺得中國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我的創作和在北京的生活也都是慢慢變好的狀態……但仍然沒有安全感,大家都好像活在一種暈眩里,所以我就有了“在浪里”的概念。其實跳不跳舞不是問題,我只是想拍一群人,那么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拍攝跳舞——因為跳舞會讓聚集變得不那么敏感,不那么的突兀。對我來說,聚集只是一個概念,而在聚集的過程中,我能夠得到安慰,得到自由——雖然自己仍然沒有安全感,但這也是唯一的方式了。
FOTO:因為是“金熊貓攝影藝術獎”,那從藝術實踐的方式、藝術作品的線索等方面看,我會不自覺地將你與“金熊貓攝影藝術獎”的藝術總監王慶松聯系起來,您如何看待他的作品呢?您覺得你們之間的異同是什么?
陳維:在我看來,其實只有異沒有同(笑)。因為他們所經歷的時代,以及時代所賦予他們的東西,讓他們必須用那樣的方式來做出自己的反應/反饋,而像我這樣的反應在那個時期可能并不奏效——這就是時代性,一個無法回避的東西。
對于現在的我們而言,從小到大其實并沒有那么辛苦,也沒有那么殘酷,所以在藝術創作的時候,也就沒有那么多的傷痛——這是很不一樣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時代的洪流中,你所感受到的就是時代賦予你的。我也經常討論我們這代人:仿古我們仿不了,因為我們是看日本的《哆啦A夢》、捷克的《鼴鼠的故事》……長大的一代人,我們的教育也處于一種比較尷尬的狀態——傳統是無法去找尋的,它是自然存在的,就像你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去找出一個父親一樣。所以,對我而言,我們所接觸的東西都處于了一個錯列的時代。為什么錯列?因為上一代人還是比較完整的,但到了我們這里,其實已經被消解了很多,所有東西都是在變革,在變化。如果回歸攝影的角度,因為攝影自身比較簡單,它的創作方式/使用規則也就那些樣式,所以無論怎樣變化,總會有相似之處。
FOTO:那么,您覺得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個人性的觀看/思考,還是一種群體性/社會性的狀態?
陳維:我個人認為:沒有純個人,也沒有純集體的存在。因為你無法以個人的角度去發言,去代表集體,你代表不了任何人。一切都是一種想象,一種對群體的想象,或者是一種對所謂純粹個人的想象。這個東西其實很復雜,因為你是在這種持續性的影響里感受和發言,而很多感受其實是別人賦予你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創作《在浪里》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個人與集體的問題——我們到底要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作品《在浪里》是不需要獨立性的,反而需要一種集體精神,但是,我們的訴求卻是要得到一個更強的獨立性,而不是一種集體精神,所以這里就有了很多悖論。我覺得我們只能盡量以想象的方式來擴充自己的感受,因為個人太渺小了,而且個人的感受會有非常大/多的偏見,因為你會帶著很深的個人印記/個人喜好去判斷某件事情。所以,在創作的時候,我就會告訴自己盡量不要帶有情緒——情緒是很個人的,你如果帶著情緒去創作,就會完全地沉溺在自己的個人情緒里,作品就可能變得非常狹隘——那不是我想要的東西。當然,我們所謂的純粹客觀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客觀都是相對的。所以,你要在客觀的基礎上進行想象。
FOTO:你是否會在藝術史或者攝影史的維度里來觀看自己,或者觀看自己的藝術實踐?
陳維:我很少去想這個問題,自己平時很關注攝影的東西,但很少考慮諸如中國攝影史會是怎樣的之類的話題——從來沒有考慮過,因為我覺得攝影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都處于一種模棱兩可的狀態,它不像繪畫、雕塑等媒介,是一種在功能性與藝術性之間的游離。所以,很多作者也無法確定自己是藝術家還是攝影師。在這種糾結的過程中,我覺得大家可能還處于很初步的階段。
FOTO:最早接觸您的作品是在2012年,當時是比較簡單的“日常布景”系列——例如《破裂的魚缸》《永不消逝的電波》等等,您覺得,它們相較于現在的作品——例如《新城》《在浪里》等等——有什么變化么?
陳維: 對我而言, 變化還是蠻大的。最早的“房間”系列主要在杭州創作,當時更加關注那種故事性的效果——每一個畫面就像一個故事,考慮的都是故事的效果,包括視覺上的沖擊和戲劇性的張力等等。但所有東西都會指向一個不在場的人,這個人肯定是邊緣的,是不受接納的——因為我覺得自己也是這樣的人,就會不自覺地去探尋這些人的處境,所以在當時創作了很多那樣的作品。后來到了北京,又創作了一些類似“習作”這樣的作品——我嘗試不用復雜的物件來做一個構造,將所有的東西進行簡化,讓語義變得更加容易可見,或者更加明晰。作品《破裂的魚缸》便是當時的嘗試之一,對我來說,它算是一個相應的訓練,雖然當時還不成熟,沒有達到自己想要的那種簡練語言的效果。所以,我就一直在簡練語言這個方向上努力。以前,我總想把事情做得很復雜,把大家繞進去,但后來覺得:你在作品中看到了什么,它就是什么。我想提升自己的這種能力——讓大家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的能力。但是這個“什么”,能否引出觀者自己的空間,那在于你拍攝了什么——我們用了什么素材,用了什么東西去做結構……
此外,因為自己拍攝的對象大都是物件——人拍得很少,當所有的物件發生交集時,其各自附帶的信息就能夠碰撞出相應的敘事,所以要盡量少地使用隱喻,要讓其更加直觀地展現出來。因為,我覺得這里有一種更強大的東西就是共同經驗,我們有一個非常強的生活共同經驗——甚至說,如果它只對中國的觀眾有效,那我覺得就非常足夠了。要抓取這種具有共同經驗的東西,并將其呈現出來,而不是說這個杯子象征什么,然后把這些象征凝結在一起達成一種所謂的意義——我覺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作品。
FOTO:縱觀您的作品,我發現它們好像有三個變化/轉折:從早期在公共空間里的行為——例如《無數次站立》《午間失眠者》等,到比較簡單的空間布景——例如《廣播中的蜜》《永不消逝的電波》等,再到現在比較復雜、精致的景觀布景——《新城》系列等等,產生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陳維:如果借用我們早期對于“觀念攝影”的認識,其實我后面的作品很不“觀念攝影”,例如你剛才提到的《午間失眠者》里的那種表演狀態,一看就是我們所謂的“觀念攝影”——它帶有表演性,并混雜了一種行為,經過了精心的設計,跟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狀態;接下來的“房間”系列也是這樣的方式。但在后來的作品里,我可能拍攝一張鐵皮就是一張鐵皮——只不過在鐵皮上是有色彩的……它們看起來好像沒那么“觀念”了。我覺得那個“觀念”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我現在會把所有的東西進行簡化——語言上簡化,對物件不做太多、太離奇的改造,讓其回到地面,然后讓其更加直接地回到語言本身——你想講的是什么?
我對自己作品的要求就是“一語道盡”,不要那種含混不清,例如,我想要一個水坑發出金色的光芒,這種金色可能來自于黃昏,也可能來自于一個金色的游戲——我不確定,但是我有那種感覺——或者是那種記憶,我把它拍攝了出來,然后拿給觀眾看——這就是我拍攝的作品。當然,觀眾可能不會相信你,他們會詢問你——“為什么要拍它?”“你要告訴我們什么?”我沒辦法直接告訴他們什么,只有有共同經驗的人才能明白——我們家小區門口的地磚總要換,在南方,因為經常下雨就有積水,有時候地面上就會有油乎乎的東西,就會有各種的色彩……這就是共同經驗,它最后導向的是被你忽視的東西,當這些被忽視的東西在一個展覽中或者一本書里集結在一起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它是在講述被我們忽略的那些東西,而在這個城市里,我們好像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會回到《新城》的母體里面。
FOTO: 最后一個問題。當下, 隨著A I技術的日臻完善,它是否會對您現在的創作方式產生影響?您是否會采用A I技術,讓自己的藝術創作變得更加輕松。
陳維:對,我也問過一些幫我做影像的朋友—— “ 能否直接用A I 做照片?”他們說能,那我就說別拍了,我也想用AI來做創作,但他們又說影像的細節不夠好,我說那也還好,但這個問題終歸要被考慮到。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攝影的問題——在今天,什么樣的東西是攝影?以前,攝影可能就是照相機,但我們現在早就從照相機的束縛里脫離出來了,iPad都能拍攝,更何況手機中的照相功能——那就是照相機。那怎么辦呢?攝影好像沒有那種非常具有象征性和儀式感的東西了,它遍布于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的屏幕上。然后,在以前,觀看攝影的的媒介可能是雜志,但現在,我們隨時隨地閱讀、分享和展示圖片。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攝影行業沖擊很大的問題,因為攝影本來就是“平民產物”,是一種門檻很低的媒介工具,誰都可以去掌握,誰都可以去拍攝,去進行藝術創作。但整個攝影行業的狀態卻很落后,例如,大家還是在裝裱,掛作品,丈量作品的高度和作品與作品之間的距離……這太不夠了。其實,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的展覽方式,讀圖經驗已經被擴展到如此程度了,它應該有更豐富的展覽方式——我常說,生活已經遠遠地把所謂專業的、藝術的攝影拋在了身后,大家應該要努力地去重新觀看那些最平民化的使用方法——它們能否變成我們的材料或者方法。
現在AI 又來了,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東西,是無法抵擋的,我覺得A I 以后肯定會成為一個輔助工具,幫助我們做很多的東西。當然,這些東西也由媒介本身的特性來決定其內容——形式就是內容的一個部分。那我們要怎樣去看待這種形式呢?現在還不知道,我可能會先進行了解和實驗——原本想在今年用3D來做一些東西,但現在看來它也落伍了。
FOTO:那您覺得AI會對攝影/影像產生怎樣的影響?
陳維:其實跟當年的PS一樣,一個軟件的出現就讓攝影進入了所謂的“后攝影時代”,讓神秘的暗房工作變得可視和可操作,還引出了關于攝影真實性的話題……其實,它最大的挑戰在于對攝影固有的那種真實性提出了質疑,我覺得這很有意思。雖然,對我而言無所謂真實不真實,誰的感嘆不真實?誰的想象不真實?對吧,所有的想象都來源于現實,都來源于真實的世界,只是大家太把所謂的“決定性瞬間”當回事兒了,它好像成了攝影的一個救命稻草,但其實并不是,攝影能做更多的事情。此外,大家都太看重攝影的那些所謂的“高級意義”了,反而失去了很多語言本身的東西,在這個時代,語言被不斷地發展,攝影也被不斷地擴充,于是就形成了現在的樣子。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語言是過剩的,是被大家忽略的——因為大家覺得攝影不夠高級,它太平民了,但攝影本來不就是平民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