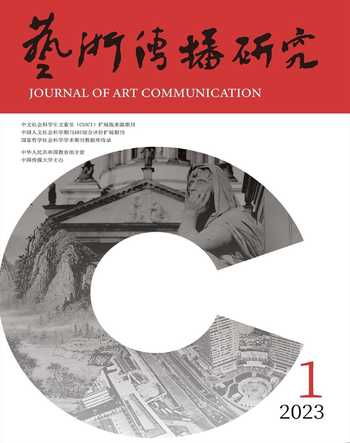電影接受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摘 要] 電影接受史是電影史研究中一個被人們長期忽視而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領域。它深受受眾研究傳統的影響,主張將觀眾的審美經驗納入電影史的研究視野。它與現有的電影美學史、電影批評史、電影傳播史、電影觀眾史等研究領域在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明顯區別。電影接受史研究應從接受主體、接受對象、接受時間、接受語境等多方面切入,綜合考察觀眾對電影的接受情況。它不僅可以彌補傳統電影史的不足,還能開拓一片新的研究領域,為電影史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
[關鍵詞] 電影接受史 接受美學 積極受眾
[基金支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一般項目“中國電影放映史(1897—1949)”(編號:21FYSB008)的階段性成果。
電影自誕生以來,已經走過一個多世紀的歷程,擁有規模龐大的受眾群體和極其豐富的接受實踐。從理論上講,任何一部影片只要進入消費市場,都有其接受史。而從世界范圍來看,無論是電影產量,還是觀眾人數,都不計其數,甚至單部影片的觀影人次都能達到上億,而每個觀眾對影片的接受狀況都不盡相同。因此,這種海量的電影接受實踐,無疑為電影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條件和堅實的基礎。
所謂電影接受史,是指觀眾對電影的觀看、接受和評價所構成的歷史。 林吉安:《〈小城之春〉的接受史及經典化研究》,《文藝評論》2022年第3期。進入21世紀以來,電影接受史研究日益引起學界關注,尤其是早期著名影人和經典影片的接受史已經成為研究重點。前者如李道新探討好萊塢明星哈羅德·勞埃德早期在中國的接受過程 李道新:《人生的歡樂面,他國的愛與恨——中國早期電影接受史里的哈羅德·勞埃德》,《電影藝術》2010年第2期。,陳國戰梳理卓別林在中國的百年接受史 陳國戰:《卓別林電影在中國的百年接受史——兼談跨文化接受史研究》,《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6期。;后者如鄭堅和楊建華梳理費穆電影及《小城之春》的接受歷程 鄭堅、楊建華:《影像·現代·民族——論費穆電影及其〈小城之春〉的接受歷程》,《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筆者也曾在梳理《小城之春》接受史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其經典化的原因。 林吉安:《〈小城之春〉的接受史及經典化研究》,《文藝評論》2022年第3期。然而,這些成果均為個案研究,并沒有對“電影接受史”展開深入的理論探討。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電影接受史”做初步的學理闡釋,探究其理論淵源、研究路徑與研究方法,以就教于方家學者。
一、電影接受史研究的理論溯源
作為一種從觀眾角度來研究電影史的方法,電影接受史研究深受西方受眾研究傳統的影響。受眾研究起源于20世紀20至30年代,廣泛涉及傳播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等多個學科領域。早期的受眾研究傾向于將受眾看作消極被動的信息接受者,但隨著人們對受眾主體性的重新認識,受眾研究開始從消極被動的受眾理論向積極主動的受眾理論轉變。 隋巖:《受眾觀的歷史演變與跨學科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年第8期。基于此,一些以受眾為中心的理論學說開始出現,比如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文學批評的接受美學理論、文化研究的積極受眾理論、媒介研究的參與式文化理論等。其中,接受美學理論和積極受眾理論對電影接受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接受美學作為一種現代文學理論流派,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聯邦德國。不同于傳統的文學理論以作家和作品為中心,接受美學以讀者為中心,主張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學作品,認為讀者不是被動的文本接受者而是主動的意義生產者;文學作品只是向讀者提供一個“召喚結構” “召喚結構”是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他看來,文學文本存在大量的意義“空白”和“不確定性”,并且其各級語義單位之間存在著連接的“空缺”,需要讀者調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去填補空白、連接空缺和確定意義。參見朱立元:《略論文學作品的召喚結構》,《學術月刊》1988年第8期。,作品的意義要由讀者通過積極的閱讀去賦予和填充。同時,接受美學還認為作品的意義和價值不是純客觀的、恒久不變的,而是會在不同時代語境下不同讀者的接受過程中發生變化。基于這種認知,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了一種建立在接受美學基礎上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 據陳文忠考證,“接受史”一詞并非姚斯首創。早在1937年,本雅明在《愛德華·福克斯——收藏家和歷史學家》一文中就已正式使用“接受史”一詞。參見陳文忠:《接受史視野中的經典細讀》,《江海學刊》2007年第6期。研究設想,主張文學史不應當只敘述作家的“創作史”,也應當包含讀者的“接受史”。也就是說,把文學史看作由作家、作品和讀者共同構成的關系史。這對傳統的以作家和作品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范式構成了挑戰。
盡管電影與文學是兩種不同的藝術,二者存在顯著差異——文學是以文字為媒介的藝術,需要讀者發揮主觀的想象力,而電影是以影音為媒介的藝術,直接訴諸人們的視聽感官——但作為審美性的藝術,它們仍不乏相通之處。正如“文學文本只有在讀者閱讀時才會產生反應”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金元浦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頁。,電影也只有在觀眾的觀看過程中才能實現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否則只是一連串流動的、沒有意義的圖像而已。也就是說,觀眾與讀者一樣,既是文本的接受者,也是意義的生產者。因此,在面對同一部影片時,不同觀眾由于文化水平、審美趣味和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差異,對影片的評價也往往會有所不同,有時甚至差異很大。另外,同文學作品一樣,人們對電影文本意義的闡釋和對價值地位的評判也會隨著時代環境、思想觀念和評價標準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在中外電影史上,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些作品雖然公映時好評如潮,票房很高,卻難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很快就被世人遺忘;而有些作品恰好相反,它們在問世之初反響平平,甚至默默無聞或是備受爭議,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其藝術價值反而愈加突顯,甚至被人們譽為經典;還有些作品則因借助官方宣傳而得到廣泛傳播以至于家喻戶曉,但隨著政治環境與社會心理的變化,其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見,不同時代的觀眾對同一部影片的接受也是有差別的。
基于上述種種原因,筆者認為姚斯所倡導的“接受史”理論同樣可以適用于電影史研究,從而開辟“電影接受史”研究的新領域。這種“電影接受史”研究將有助于彌補過去以影人和影片為中心的傳統電影史的不足,從而進一步完善電影史學體系。
除了接受美學理論外,電影接受史研究還深受積極受眾理論的啟發。積極受眾理論是英國伯明翰學派在吸收“接受美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種大眾文化理論,是對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論的反駁與超越。不同于“文化工業”論中完全消極被動而淪為媒介操控對象的受眾,這一理論中的受眾是具有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社會個體。正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工人階級受眾并非中產階級與大眾媒介可以加以規劃的空洞容器—— 一張白板——無論他們想要什么。他們并不僅僅是‘虛假意識或‘文化麻醉劑(cultural dopes)的產物。他們有其自身的‘文化。” [英]斯圖爾特·霍爾:《理查德·霍加特、〈識字的用途〉及文化轉向》,殷曼楟譯,https://ptext.nju.edu.cn/d9/ac/c13164a514476/page.htm,訪問日期:2022年10月25日。
基于這種積極受眾的觀念,伯明翰學派通過對電視等通俗文化的研究發現,受眾作為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并非完全消極被動地接受,而是會根據自身的社會立場和價值觀念對文本做出積極主動的個性化解讀。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提出,受眾在解讀文本時,可能會存在三種不同的立場,即主導—霸權立場、協商式立場和對抗式立場。 [英]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載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359頁。后兩種解讀立場,便鮮明地體現了受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后來,霍爾的學生戴維·莫利(David Morley)通過對電視受眾的民族志研究,不僅驗證了“編碼/解碼”理論的合理性,還對其做了進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他指出,受眾在解讀文本時,之所以會出現多種不同的解碼方式,除了受“社會立場”的影響外,還與其“特殊的話語立場”有關。這種“‘特殊的話語立場是境遇性的,受制于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受制于在其中受眾個體的情緒、意識、經歷等,因而它總是變動不居的,總是作為一個有待確定的問題”。 參見金惠敏:《走向社會本體論——試論戴維·莫利的積極受眾論》,《漢語言文學研究》2012年第3期。由此,對接受語境的分析被納入受眾研究。
這種積極受眾理論同樣被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所認可和吸收。他也主張受眾在消費文化商品時具有能動性和創造性,是“意義和快感的生產者”。在《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一書中,他指出文化工業不僅是一種“金融經濟”,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經濟”。其中,“在文化經濟中,流通過程并非貨幣的周轉,而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 [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而受眾通過對文本意義和快感的多元化生產,可以有效地“規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規訓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質性和一致性”,進而對抗文化商品“中心化的、規訓性的、霸權式的、一體化的、商品化的力量”。由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所有的大眾文化都是一場斗爭(的)過程,而這場斗爭,發生在社會經驗、人的個性及其與社會秩序的關系、該秩序的文本和商品的意義之上。” 同上書,第34頁。
無論是接受美學理論,還是積極受眾理論,都強調受眾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而根據這些理論可以推斷,觀眾在觀看電影時,同樣并非完全消極被動地接受影片所灌輸的內容,而是可以根據自身的立場對文本意義做出個性化的解讀,這就使得不同觀眾的接受必然會存在差異。而這正是電影接受史研究能夠成立的根本原因。
二、電影接受史:作為電影史研究的新領域
作為電影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電影接受史研究主張將觀眾的審美經驗納入研究視野,從觀眾接受的角度來研究電影史。它與電影美學史、電影批評史、電影傳播史、電影觀眾史等已有研究領域既有一定的交叉和聯系,也有顯著的區別。
首先,不同于傳統的電影美學史主要關注電影人的創作活動及其生產的影片文本,電影接受史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了觀眾身上,即從觀眾的角度來研究電影史。前者以創作活動為中心,主要分析電影人的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后者則以接受活動為中心,著重考察不同觀眾對影片意義的解讀及價值評判。在傳統的電影美學史看來,影片的意義是由電影創作者賦予的,并已事先灌注在文本內部,等待觀眾去挖掘和發現;而在電影接受史看來,觀眾才是文本意義的生產者,而且對于不同的觀眾而言,影片的意義和價值是有差別的。因此,電影接受史實質上是觀眾與影片的審美對話史,是電影文本的“召喚結構”與不同觀眾的“期待視野”相互交融后實現作品意義與價值的歷史。由此,在接受史的視野里,影片的意義和價值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會因人而異,且會隨著時代環境和審美觀念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要判斷一部電影的價值,不能只看一時一地的觀眾反應,而須從較長時間和較廣范圍來考察文本的接受情況。這就使得電影接受史不再像傳統的電影美學史那樣對影片的價值意義做靜態的定性分析,而是要動態地考察它在不同時空和社會語境下的接受狀況。
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羅伯特·艾倫(Robert C.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便在吸收接受美學觀念的基礎上,對傳統電影美學史所推崇的“唯杰作論”提出了質疑:“如果讀者或觀者對作品的理解要受歷史環境制約的話,那么選擇杰作所依據的標準是不是也易受到歷史變革的影響呢?” [美]羅伯特·C.艾倫、道格拉斯·戈梅里:《電影史:理論與實踐》,李迅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8頁。由此,他們主張打破這種“唯杰作論”,并結合符號學理論,“把美學電影史重新界說為作為表意實踐的電影的歷史和觀眾與影片在特定時代彼此抗衡的歷史,而不是僅僅把它看成是藝術電影的歷史” 同上書,第155頁。。他這里所說的“觀眾與影片在特定時代彼此抗衡的歷史”,其實指的便是電影接受史。
其次,與電影批評史相比,電影接受史雖然也考察影評人及其撰寫的影評文章,但二者在研究角度和研究重心方面均有明顯的區別。前者將影評人視為電影的批評主體,主要從批評目的、批評標準和批評方式等方面切入,考察其批評模式的歷史變遷; 李道新:《建構中國電影批評史》,《電影藝術》1998年第4期。而后者將影評人視為電影的接受主體,從審美接受的角度出發,考察其對影片的意義闡釋和價值評判。前者主要分析影評人的批評理路和批評話語,是一種對電影批評實踐的再批評與再思考;后者則主要比較不同影評人對影片意義的理解及其價值評判的差異,并剖析其原因。
除了考察影評人對電影的接受情況外,電影接受史還會考察電影研究者、電影創作者以及普通觀眾對電影的接受情況。同時,它不只關注觀眾對文本意義的解讀,還會考察觀眾的接受語境,即觀眾在什么樣的場所環境下、使用什么樣的設備、借助什么平臺進行觀看,有時甚至還要考察觀眾觀看的版本。此外,它還考察電影的輿論評價、流行程度、歷史地位及后世影響等各個方面。可見,相較于電影批評史,電影接受史的研究范圍更廣,考察對象也更為豐富多元。
再次,與電影傳播史相比,電影接受史雖然也研究觀眾對電影的反應,但其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前者主要關注文本對受眾行為的影響,屬于一種傳播效果研究;而后者更關注受眾對文本意義的解讀,屬于一種接受分析研究。同時,二者的受眾觀念也截然不同。在電影傳播史研究中,觀眾只是作為傳播的客體;而在電影接受史研究中,觀眾則是作為接受的主體。更重要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也有顯著差異。電影傳播史主要運用傳播學理論,研究電影的傳播制度、傳播媒介、傳播方式和傳播效果; 李道新:《建構中國電影傳播史》,《人文雜志》2007年第1期。而電影接受史則主要運用接受美學理論,考察不同時代和社會環境下的觀眾對電影的接受情況及其歷史演變,進而從中窺探社會審美觀念的變化。此外,不同于電影傳播史主要從共時性的角度考察電影在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傳播與接受狀況,電影接受史既包括這種共時性的研究,也包括歷時性的研究,即考察不同時代的觀眾對電影的接受之變化,并剖析其原因。
最后,與電影觀眾史 雖然觀眾研究早已成為電影學研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誕生了“電影觀眾學”這門學說,但它卻很少進入電影史的研究視野。目前僅有少數學者展開了電影觀眾史的專門研究,如理查德·布茨(Richard Butsch)的《美國受眾成長記:從舞臺到電視》(王瀚東譯,華夏出版社2007年版)、陳一愚的《中國早期電影觀眾史(1896—1949)》(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年版)、侯凱的《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中國電影出版社2020年版)等。相比,電影接受史在研究角度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區別。雖然二者都屬于受眾研究的范疇,但電影觀眾史更多是從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探討觀眾的社會構成、觀影習慣、觀影行為和觀影心理;而電影接受史則是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著重考察不同時代的觀眾對影片意義的理解及其價值評判的歷史演變過程,從而把握社會審美觀念和大眾審美趣味的時代變遷。
總而言之,電影接受史是電影史研究中一個被人們長期忽視而有待深入挖掘的新領域。在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它雖與傳統的電影史研究不乏交叉和重疊之處,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因而有待學界進一步展開研究。
三、電影接受史研究的路徑與方法
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電影接受史應當如何開展研究呢?它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路徑和方法?下面,筆者將對此展開初步的探討。
作為一種電影史研究,電影接受史研究當然要遵循電影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從研究步驟來看,至少應當包括兩個基本環節:一是文獻學意義上的有關電影接受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批評學意義上的有關電影接受史的回顧與闡釋。前者是研究的基礎,后者則是研究的重點。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充分地占有史料,電影接受史研究亦應如此。這種接受史料既包括影片公映時的觀眾反應,如觀影人次、票房收入、媒體和輿論風評、獲獎情況以及私人的觀影記錄等,也包括后世人們對影片的回顧和研究,如電影回顧展、經典排行榜,以及專家學者的研究著述等。全面掌握這些史料后,接下來則須對其展開深入分析,比較不同時代語境中不同觀眾對影片的理解和評價有何差異,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當然,除了運用上述常規的電影史研究方法外,電影接受史也有一些獨特的研究路徑。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從接受主體來看,由于藝術作品的接受主體包含普通大眾、批評家和創作者,因此其接受史研究也相應地存在三種不同路徑,即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以批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以及以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 參見陳文忠:《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芻議》,《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考慮到電影的接受主體同樣包含普通觀眾、電影批評家(研究者)和電影創作者,因此電影接受史研究也可大體從以下三種路徑入手:
一是以普通觀眾為接受主體的效果史研究,即研究不同時代的普通觀眾是如何觀看、解讀和評價影片的,從而窺探社會審美觀念和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它著重考察電影的流行程度和口碑變化。具體而言,可通過考察影片公映時的各方面受歡迎程度,以及后世觀眾對影片的印象、評價,分析影片的接受效果。其中,票房無疑是衡量影片流行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而評論反映的則是觀眾的認可程度及其對影片的印象。
二是以電影批評家為接受主體的闡釋史研究,即研究不同時代的影評人和專家學者對影片的藝術特色、美學風格、價值意義、影史地位等方面的闡釋和評價,從而揭示影片聲譽和地位的變化軌跡。這種闡釋史由于主要研究藝術電影,尤其是歷史上的那些經典影片,因而很關注作品的“經典化”問題,以至于有學者提出“接受史乃是經典生成史” 譚桂林:《接受史作為文學經典的形成史》,《江漢論壇》2018年第10期。。比如,費穆導演的《小城之春》雖然已被公認為中國電影史乃至世界電影史上的杰作,但這一經典地位并非與生俱來的,而是文本內外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是中外電影研究者對影片文本展開的深入重讀與重評,在其“經典化”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參見林吉安:《〈小城之春〉的接受史及經典化研究》。
三是以電影創作者為接受主體的影響史研究,即研究后世創作者如何看待前輩電影人的優秀作品,以及受到何種影響。在百余年的中外電影史上,已經誕生眾多經典影片,這些影片往往會成為年輕一代電影人學習和效仿的榜樣,因此也必然會對其創作產生某種影響。其中有些影響是顯在的,比如對某種創作手法的借鑒、對某個經典場面的摹仿或戲仿,或是直接翻拍某部優秀影片;也有些影響是潛在的,比如電影觀念的啟蒙、美學風格的傳承、創作靈感的激發等。對于前者,人們往往比較容易辨識;對于后者,則有時需要借助電影人的陳述或訪談才能做出準確判斷。以賈樟柯的電影創作為例,雖然人們很容易將其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和侯孝賢的電影聯系起來,但對于他具體受到何種影響則往往不甚了了。而倘若結合賈樟柯本人的相關陳述和訪談資料,我們便會發現原來是侯孝賢的《風柜來的人》和德·西卡的《偷自行車的人》對其電影美學觀念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此之外,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和布列松的《死囚越獄》也深刻影響了他對電影時空的理解。 2013年11月18日,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的一次學生見面會上,賈樟柯列舉了一長串他喜愛的電影導演及影片名單,并闡述了他所受到的具體影響。當談到侯孝賢時,他回憶了首次觀看《風柜來的人》的體驗,并稱正是該片啟發了他的電影觀念,使他“意識到個體經驗有多么重要”。同時,他也談到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使他理解了空間的意義,而布列松的《死囚越獄》則使他發現了電影的時間。(參見[法]讓-米歇爾·付東:《賈樟柯的世界》,孔潛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137頁。)在另一次訪談中,他又明確談到意大利導演德·西卡對其電影觀念的深刻影響。他說:“電影沒有單一的一個終極本體的概念,它的美究竟在哪兒?它的媒介特點在哪兒?每個人的理解都不一樣。而我自己的理念是經由德·西卡的電影及紀錄美學而產生的。”又說:“是他(指德·西卡)奠定了我對(電影)這個媒介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的影像喜好。”(參見賈樟柯、楊遠嬰等:《拍電影最重要的是“發現”——與賈樟柯導演對話》,《當代電影》2015年第11期。)顯然,這種影響史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電影歷史的傳承與發展,以及中外電影之間的影響互滲。
其次,從接受對象來看,由于觀眾在觀看了電影之后,不僅會對影片形成一定的認知,也會對創作者給予一定的評價,因此電影接受史也應包含兩方面:一是影片接受史,即人們觀看、解讀和評價影片的歷史;二是影人接受史,即電影人(尤其是導演和明星)在人們心目中的口碑和聲譽的升降變化軌跡。比如,前文提及的不同時期人們對《小城之春》的接受變化便屬于影片接受史的范疇;而哈羅德·勞埃德和卓別林在中國觀眾心目中的地位變化,便屬于影人接受史的范疇。當然,影人接受史和影片接受史并非截然分開的,二者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盡管人們對影人的接受可以通過多種渠道——既包括文本內的,也包括文本外的——來獲知,但影片始終是影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人們評價影人的主要依據。因此,人們對影人的接受,離不開對其影片的接受。甚至可以說,人們對影片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們對影人的評價。
再次,從接受時間來看,由于電影接受包括共時性的水平接受和歷時性的垂直接受,因此,電影接受史研究也可分為共時性的水平接受史研究和歷時性的垂直接受史研究。前者主要探討電影在公映時如何被本國乃至外國觀眾所接受,著重考察其市場反應和輿論口碑,這種研究與電影傳播史研究比較相似,也是當前學界研究較多的領域。 比如徐文明:《市場與文化的交響:戰后中國電影在新加坡的傳播及影響》,《當代電影》2017年第12期;熊鷹:《論民國時期德國烏發公司電影在上海的傳播與接受》,《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李雋、張黎吶:《“白話思潮”與“有聲電影”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江漢學術》2021年第6期。后者則主要從歷時的角度考察影片及其創作者在不同時代語境中的接受演變軌跡,進而揭示社會文化觀念和大眾審美趣味的變遷。這既是電影接受史研究的重心,也是它區別于電影傳播史研究的地方。因此,電影接受史研究往往會體現出一種歷史的縱深感。
最后,從接受語境來看,電影接受史研究還可以具體考察觀眾觀影時的場所(室內或室外)、環境(影院或流媒體平臺)、媒介(膠片或數字)乃至版本(原版、刪減版或配音版)等。這些因素同樣會影響觀眾對電影的感知和評價。比如,露天放映和影院放映便有很大的區別,雖然前者的影像、音質和舒適度均不如后者,但卻可以使觀眾感受到電影文本之外的豐富信息,因此與后者的觀影體驗截然不同。又如,李安導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針對不同影院的播放條件,分別制作了3D/4K/120幀、3D/2K/120幀、3D/2K/60幀、3D/2K/24幀等不同規格的版本,這些版本也給觀眾帶來了不盡一致的體驗。 李安:《每人心中都有比利林恩 花了三月調整各版本》,網易娛樂,2016年11月8日,https://www.163.com/ent/article/C5CJK8AU000380D0.html,訪問日期:2022年8月20日。同樣的電影內容尚且會因播放環境的差異而導致不同的觀影體驗,電影內容的調整或刪減則更是會影響人們的評價。在電影創作實踐中,有些電影會由于各種原因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刪減。人們觀看這種刪減版的電影時,可能會對其中的某些情節或人物感到疑惑,甚至對影片主題的理解產生分歧,進而對電影產生另外的印象和評價。此外,當我們觀看一部經過數字修復后的早期電影時,所看到的影像很可能與原初的版本并不一致,這無疑也會影響我們對影片的感知。因此,電影接受史研究除了考察觀眾對文本的意義闡釋和價值評價外,還要考察人們在觀影時的環境設施、媒介平臺乃至影片版本等。
結 語 電影接受史是在接受美學理論和積極受眾理論的啟發下提出的一種研究電影史的新路徑。它與電影美學史、電影批評史、電影傳播史、電影觀眾史等研究領域既有一定的交叉和聯系,也有顯著的區別。從接受主體來看,它可分為以普通觀眾為主體的效果史、以電影批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和以電影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從接受對象來看,它主要包括影片接受史和影人接受史;從接受時間來看,它可分為共時性的水平接受史和歷時性的垂直接受史;從接受語境來看,它可以具體考察觀眾觀影時的場所、環境、媒介和版本等。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過去所編的中國電影史甚至世界電影史,常常在編導、作品與觀眾所構成的三角關系中,抽去了觀眾這一至關重要的一角,使理論體系失去了穩固性。” 曾耀農:《電影研究與接受美學》,《藝術廣角》1999年第2期。因此,這種將觀眾的審美經驗納入研究視野的電影接受史研究,無疑可以彌補傳統電影史書寫的不足,從而使觀眾與創作者及電影作品一起構建一部更為完整的電影史。同時,它還可以開拓一片新的研究領域,為電影史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因而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作者簡介:林吉安,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影視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