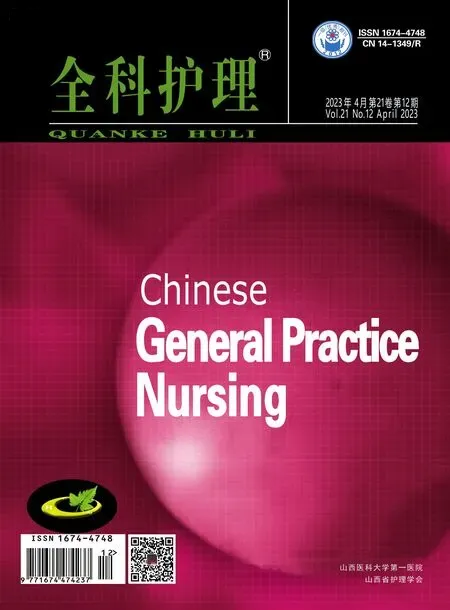基于動機性訪談制定的心理護理在晚期癌癥病人中的應用效果
張婉君,李潤花,王萌萌
疼痛管理作為晚期癌癥病人的主要護理內容是近年臨床研究的重點,現有的臨床調查顯示有超過80%的晚期癌癥病人伴有不同程度的癌性疼痛[1],對于晚期病人來說鎮痛藥物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生理上疼痛程度,然而除此之外疼痛程度與生存質量、焦慮抑郁情緒等均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疼痛管理應包含鎮痛治療和心理護理兩方面。臨床學者普遍認為通過改善病人的疼痛程度對于提高終末期生存有著直接的影響[2-3]。國內有研究認為,癌性疼痛管理障礙主要受家庭人均收入、文化程度、醫療付費方式、疼痛管理培訓以及疾病不確定感等多個因素影響[4-5],其中文化程度和疼痛管理培訓、疾病不確定感在通過相應的護理干預或健康教育后能得到一定的改善[6-7]。因此如何有效地改善病人對疾病的認知成為護理疼痛管理關注的焦點。動機性訪談是以病人為中心,具有方向性的協助模式,應用于臨床表現為醫護人員與病人合作、醫護人員引導病人探索矛盾心態,通過培養病人自身動機和改變的決心,在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心理干預方法,對于應對因文化程度差異或疾病相關認知導致的疼痛管理障礙有積極的作用。本研究通過對近2年晚期癌癥病人進行前瞻性對照研究證實了基于動機性訪談制定的疼痛目標管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現將相關研究內容和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9月—2022年3月本院收治的晚期癌癥病人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年齡18~60歲;②確診為癌癥晚期,并接受癌癥疼痛相關姑息治療;③意識清醒,可以自主清晰的語言交流;④預計生存期>3個月。排除標準:①中斷治療或轉院者;②研究期間并發其他疾病者;③自愿放棄或拒絕護理干預者;④存在嚴重焦慮、抑郁或精神障礙者。根據上述納入、排除標準,本次研究共收入病人112例,觀察組、對照組各56例,最終納入研究分析94例,觀察組46例,對照組48例。觀察組,男26例,女20例;年齡27~68(45.28±6.22)歲;癌癥類型:胃癌13例,肺癌15例,胰腺癌5例,乳腺癌13;癌癥分期:Ⅲ期25例,Ⅳ期21例。對照組,男25例,女23例;年齡25~69(46.02±6.46)歲;癌癥類型:胃癌15例,肺癌14例,胰腺癌3例,乳腺癌16例;癌癥分期:Ⅲ期25例,Ⅳ期23例。兩組病人在性別、年齡、癌癥類型以及癌癥分期分布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護理方法
1.2.1.1 對照組 ①疼痛治療:采用常規疼痛管理方案,入院后采用數字疼痛評分(NRS)對病人疼痛程度進行評分,鎮痛治療病人每8 h評估1次,評分超過4分病人則每30 min評估1次,直到評分降至4分以下。癌痛用藥采用三級鎮痛階梯法,輕度疼痛(NRS1~3分)以非甾體抗炎藥為主,中度疼痛(NRS4~7分)以弱阿片類藥物、低劑量強阿片類藥物為主,重度疼痛(NRS8~10分)在阿片類藥物基礎上可聯合非甾體抗炎藥及鎮痛藥聯合治療。對于鎮痛藥物引發的不良反應則給予對癥治療。住院期間護理人員根據病人的喜好和需求對非藥物鎮痛療法進行宣教,包括音樂療法、松弛療法或運動療法等。②心理護理:采用常規護理方案,入院時對病人癌性疼痛認知情況進行調查、癌痛管理知識宣教、自我疼痛評估以及分階段疼痛管理方法,住院期間個性化心理疏導(每周1次)、音樂干預(每天3次)、放松訓練(每天2次)等。
1.2.1.2 觀察組 ①疼痛治療同對照組。②心理護理:采用動機性訪談方案制定符合病人的個性化疼痛相關心理護理措施。組建訪談小組,按照動機性訪談的原則,以病人為核心,遵循一導入、二聚焦、三導出、四計劃的訪談流程制定相應的訪談大綱。導入:簡單說明訪談的目的,收集訪談相關的基本信息,以及病人過去的訪談經歷以及自身對于訪談后的作用或價值的評價;聚焦:基于動機性訪談的原則,聚焦疼痛管理中病人的矛盾心理;導出:通過溝通了解病人對疾病的認知、治療用藥、既往治療過程、癌性疼痛經歷、現階段的疼痛程度和特點以及采用的鎮痛措施等對病人的疼痛管理預期進行判斷。計劃:與病人一起分析癌性疼痛控制不佳的原因,確立正確并符合病人疼痛管理預期的疼痛管理目標及其相應的管理方案,同時預約下一次訪談。訪談每周進行1次,連續4周。
1.2.2 觀察指標 ①生存痛苦量表評分(Existential Distress Scale,EDS)包括無意義感(3個條目)、孤獨(3個條目)和低自我價值感(4個條目)3個維度,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評分法,從0分“無痛苦”到4分“難以承受的痛苦”,總分0~40分,評分越高提示自覺生存痛苦越嚴重,經漢化后該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92,重測信度為0.643[8]。②總體幸福感量表(GWB)涵蓋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2個條目,2~11分)、對健康的擔心(2個條目,1~16分)、精力(4個條目,3~28分)、憂郁或愉快的心境(3個條目,2~22分)、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3個條目,3~17分)、松弛和緊張(4個條目,3~26分)6個維度共18個條目,各條目評分相加即為GWB總分,滿分120分,評分越高表明總體幸福感越好[9]。③疼痛評估采用視覺模擬疼痛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病人根據自覺疼痛程度選擇相應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自覺疼痛越嚴重,0分為無痛,1~3分為輕度疼痛,4~6分為中度疼痛,7~10分為重度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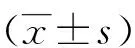
2 結果
2.1 干預前后兩組病人生存痛苦量表評分比較 干預后對照組孤獨感和生存痛苦總分相比干預前降低,觀察組無意義感、孤獨感、低自我價值感以及生存痛苦總分均較干預前降低,其中觀察組無意義感、孤獨感、低自我價值感以及生存痛苦總分低于對照組,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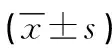
表2 兩組病人生存痛苦量表評分比較 單位:分
2.2 干預前后兩組病人總體幸福感評分比較 干預前兩組病人總體幸福感以及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對照組病人在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以及總體幸福感總分較干預前改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病人在對生活的滿足和興趣、對健康的擔心、精力、憂郁或愉快的心境、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松弛和緊張以及總體幸福感總分較干預前改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觀察組在對健康的擔心、對情感和行為的控制松弛和緊張以及總體幸福感總分高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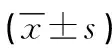
表3 兩組病人干預前后總體幸福感評分比較 單位:分
2.3 兩組病人干預前后疼痛控制情況比較 干預后兩組VAS評分均較干預前降低(P<0.05),詳見表4;其中觀察組干預后輕度疼痛人數相比對照組增多,中度、重度疼痛人數相比對照組減少,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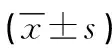
表4 兩組病人VAS評分比較 單位:分

表5 兩組病人疼痛程度比較 單位:例(%)
3 討論
癌性疼痛對于個體來說是一種新的、不可預知的體驗,對于疼痛的控制需要改變某些個體行為,而這種改變如果不具備個體需求,那么改變會顯得困難且不可持續。若改變的動機和目的可以達到個體的需求或預期,這樣的期望可以促使個體接受行為改變并且做好行為改變的心理建設,在此基礎上行為改變的計劃就會變得更加容易且可持續的實施[10-11]。在既往的癌性疼痛護理中,醫護人員往往更加注重疼痛管理的結果,即如何快速有效地鎮痛,而當藥物鎮痛不再具有時效性或藥物鎮痛受限時,常規的心理疏導或應用音樂、放松訓練等試圖通過轉移病人注意力來實現緩解疼痛的方法則顯得作用有限。而臨床實踐過程中也發現,個人喜好也是影響病人是否接受或采用鎮痛方案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見個體的需求和預期是建立癌性疼痛管理方案的核心。動機性訪談是將疼痛管理目的、個體需求和預期以及健康教育相結合的醫患溝通模式,在病人建立對醫護人員信任的前提下,按照動機性訪談的既定流程,引導病人討論自身的疾病狀態、疼痛程度以及對于疾病或癌性疼痛的矛盾心理,訪談人員在此過程中需要具備快速分析能力,發現導致病人矛盾心理的根源以及疼痛管理效果不佳的原因,進而基于病人矛盾心理來進行剖析,與病人合作確立符合自身需求的疼痛管理目標和計劃[12-13]。近年來動機性訪談護理方案已應用于臨床多個領域,并顯示出了顯著的護理成果[14-16]。本次研究將疼痛管理目標實施時間設置為1周,其原因在于短期判斷疼痛管理目標實施的有效性可以及時調整方案,病人在短期的應用過程中隨著身體或病情的變化也會產生新的需求。通過與常規護理管理模式比較,基于機動性訪談疼痛目標管理病人在實施4次訪談后病人的疼痛程度有顯著下降,在此基礎上病人還伴有自覺的生存痛苦減輕,總體幸福感提升,這一結果符合晚期癌癥病人的治療目的,既要有效減輕癌性疼痛,同時也需要改善病人終末期的生存質量。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該護理模式在具體實施和操作方面相比傳統的心理護理模式,動機性訪談并不具有可重復性特點,對護理人員的方案制訂、實時分析以及措施方案的執行等各個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17-19],這無疑考驗著現有的護理人員專業水平、醫患溝通方式、心理分析能力。然而個性化診療是未來醫療發展趨勢,也是終末期疾病病人及其家屬需求所在[20],因此基于機動性訪談流程不斷提高終末期護理專科水平才有助于護理質量質的飛越。
由此,本研究認為基于動機性訪談制定的心理護理措施在晚期癌癥病人中應用具有可行性,在緩解疼痛以及改善病人終末期生存質量方面具有顯著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