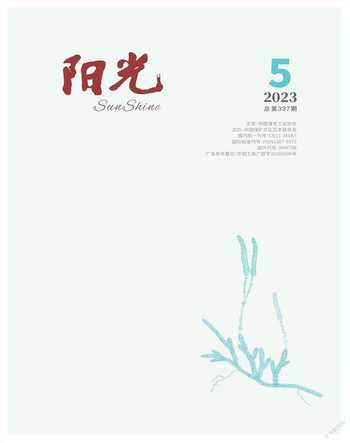坡東坡西
爬上坡梁,我身上多了九顆蒼耳,兩顆粘在褲腿上,三顆粘在襪子上,四顆粘在鞋帶上。這小東西很黏人,長得像棗核,渾身帶刺,一到秋天,就像地雷般埋在草叢里。我蹲下身,每摘下一顆,手指就刺痛一下。我早已習慣了這種疼,就像習慣了這道坡梁一樣。
這道坡梁,橫在梁西村和梁東鎮(zhèn)之間,一上一下十二里。自從到梁東鎮(zhèn)中學住校后,除了假期,我每周都要爬兩次坡。周五是開心的日子,我的書包里除了作業(yè),大多時候不會有其他東西,爬坡時雖然是黃昏,也格外輕松。我像一只歡快的田鼠,很快上到坡頂。坡頂是大口喘氣、大聲呼喊的地方,站在那里,會看到一輪將要熄滅的日頭,還有火紅的梁西村。村里有三十多戶人家,除去封門閉戶的一半,另一半里,只有我家的煙囪在冒煙。我能從那縷孤獨的炊煙里,嗅到山藥魚子的味道,那是母親特意為我準備的晚飯。周一是難過的日子,我的書包被母親塞得鼓鼓囊囊,十張起面糖餅,一大瓶腌芥菜,一小瓶蘑菇醬,爬坡時雖然是清晨,卻格外費力。到達坡頂時,梁東鎮(zhèn)已經(jīng)發(fā)亮,但我會回過頭,看一眼還在深灰色中沉睡的梁西村。好幾次,我動了原路返回的念頭,想鉆進被子睡個回籠覺,日上三竿時再起床,可這種待遇,只有假期才有。
我把摘下的九顆蒼耳,放進敖包的石頭縫里,這群鬼頭鬼腦的小東西不再煩人,成了獻給山神的祭品。敖包是老羊倌堆的,所有石頭都來自這道山坡。老羊倌一邊放羊,一邊撿石頭,長年累月,山坡上裸露的石頭幾乎被撿光,那些被壓迫的花草就快樂地生長。敖包也在生長,一天比一天高大,晴天時,站在梁西村,可以望見坡頂冒出個尖,像是奶嘴一般。老羊倌放羊時,敖包邊放著一個編織袋,袋子里裝著散落在山坡上的各種垃圾,有路人丟棄的礦泉水瓶,有大風刮來的塑料袋,還有莫名其妙上了坡的廢木料。我懷疑那些木料是棺材板,勸老羊倌不要撿,他搖搖一頭的亂發(fā),把木料裝進袋子里。這道方圓幾十里的大山坡,被老羊倌收拾得干干凈凈,除了花草,就剩羊群。粘在羊身上的蒼耳,也一顆顆被摘下來,放進敖包的石縫里,老羊倌說,這小東西進了石縫就像羊進了圈,不再滿山亂跑了。
老羊倌是我每次爬坡必遇的人,無論我周一起多早,也無論我周五回來多晚,都能在山坡上看見他。他夏天也穿一件棉軍衣,天涼后也是這件,記憶中,從未見他換過衣服。那件本來是軍綠色的大衣,被穿得油黑發(fā)亮。雖然總是碰面,我竟然沒注意過他的鞋子,只記得他的頭發(fā)又亂又長,與胡子連在一起,這就使他的眉眼也像鞋子那樣容易被人忽視,以至于我站到敖包前,也沒想起他清晰的模樣。或許是他乞丐般的樣貌引發(fā)了我的憐憫,或許是共處一座空曠的山坡有點同病相憐,在某個周一的清晨,他遠遠地向我打招呼時,我快步走過去,從書包里掏出一張?zhí)秋炦f給他。老羊倌沒接那張餅,為了說明不接受饋贈的理由,他敞開肩上的挎包。包里像是有許多東西,我只看清有饅頭和酒瓶。老羊倌順手從包里拿出個小籠子,是用馬蓮編的,由于是深綠色,等籠子里發(fā)出“吱吱”的叫聲,我才看清里面有只同樣是深綠色的蟈蟈。下坡時,我捏著那根馬蓮,馬蓮下吊著的籠子搖搖擺擺,蟈蟈一定是餓了,“吱吱”叫了一路。走到坡底時,我感覺有雙眼睛在背后盯著我,我回頭看見,老羊倌站在敖包邊向我揮手。
老羊倌十年前撿起第一塊石頭時,一定對放置地點做了精心選擇,站在敖包旁邊,既能看到梁東鎮(zhèn)也能看到梁西村。梁西村里,馮八家的房子清晰可見,那是老羊倌的住處。馮八一家在天津做生意,長年不回來,房子沒人看,羊也沒人放,就把二舅老羊倌請來打理。老羊倌是后草地人,從小給人放羊,沒成過家,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說去哪兒抬腳就走。外甥有求不能不幫,就這樣,一幫就是十年。十年里,梁西人不斷外出謀生,空房子越來越多,沒人照看的羊也越來越多,老羊倌的羊群便越來越壯大,有了五百多只。
自從老羊倌落腳梁西村,馮八家就亂成廢品收購站。院子里無法下腳,堆著撿來的舊輪胎、廢木料、破衣服、碎玻璃、空酒瓶、塑料袋等等。從院門到屋門,只留一條狹窄的過道,而就是這條僅有的過道,依然可以踩到舊鞋底、廢紙片之類的東西。屋里更讓人傻眼,地上柜上且不說,僅一盤大炕,就鋪攤得面目全非,被子、電飯鍋、插座、枕頭、改錐、火盆、褥子、羊鞭、飯碗等等,我甚至想過,老羊倌或許不需要下炕,就能把日子過下去。
聽母親說,老羊倌不需要撿垃圾和放羊也能過活。就在去年,后草地那邊給他辦了低保和醫(yī)保,他另有三十畝耕地,退耕還草后,每年可領到一筆不菲的補貼。但老羊倌平生最大的愛好就是撿垃圾和放羊,看見垃圾不撿他的手會癢癢,看見羊不放他會渾身難受。偶爾有陰天下雨,老羊倌不能外出,就憋在家里來回走動,急得抓耳撓腮,恨不能把羊趕進屋里放一放。我有時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的宿命是背著書包來回爬坡,老羊倌的宿命是放羊和撿垃圾,說白了,他就是為羊和垃圾而生。所不同的是,我厭倦了爬坡卻不得不爬,而老羊倌完全可以放棄羊群和垃圾,他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一個網(wǎng)癮少年迷戀電子游戲那樣。
日復一日的堅持,真能讓人成癮嗎?這次,當我即將結束爬坡的宿命,要和山坡說再見時,切身體會到了老羊倌的感受。我驀然覺得,這道山坡像是一塊磁鐵,每走一步,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蒼耳找到合理歸宿后,我繞著敖包走了一圈,忽然想到,每次匆匆趕路,與敖包擦肩而過,竟然沒站上過它的肩頭。爬上敖包,四處望去,竟然看到了梁西村的青石碾盤。我出生時,碾盤就放在馮八家院墻外面,我卻從未在山坡上注意到過。自從馮八買回了磨面機,他家的磨坊就更新?lián)Q代,磨盤被“請”出院子,成了村民閑聊的“座位”。磨盤邊,一度是村子最熱鬧的地方,地皮被磨得發(fā)亮,常年有煙頭和瓜子皮。退耕還草后,村民不種大田了,拿到補助后,紛紛外出打工。馮八也賣了磨面機,去天津做起了小本生意。磨盤邊逐漸冷清起來,由于沒有掉落的葵花籽,雞都不再過來。偶爾有某個夜晚,磨盤上會亮起一點火星,那是老羊倌坐在那里抽旱煙。煙火一閃一閃,像是在講述他孤獨、單調的人生。老羊倌對我說過,黑夜坐在碾盤上抽煙,是他一天最松快的時候,那個時候,羊都進了圈,一只不少,一只不多,不用再點數(shù)。老羊倌不識數(shù),他點羊時全靠記性,放了一輩子羊,他能根據(jù)每只羊的細微差別,認出群里所有的羊。他群里的許多羊,也便有了名字,比如楞頭、瘸子、歡實、歪臉等等。
老羊倌站在敖包邊大聲喊“歪臉”時,剛好是一個周五的黃昏。我顧不得和老羊倌打招呼,就跑過去看那只出了群的羊。我蹲下身仔細看,也沒看出那只羊臉是歪的。老羊倌鞋底磨著草皮走過來,一邊把歪臉趕進群,一邊對我說,放學了?每個周五,走進梁西村的地界,我聽到的第一句問候總是這三個字。老羊倌的口音很重,一直把“學”說成“宵”,這是他與梁西人不同的地方。我站起身,從衣兜里摸出一塊電池,用食指和拇指捏著,遞給老羊倌。那是一塊非常小的圓餅狀電池,放進老羊倌張開的手掌里,有些難以辨認。老羊倌的手掌很長,掌心呈醬紫色,橫七豎八全是深紋。老羊倌感覺電池放進手心后,就緊緊握住拳,慢慢坐到草地上,盤起腿。他的另一只手放下羊鞭,從懷里摸出一塊手帕。他把手帕鋪到草地上,再把電池放進手帕里,一只螞蟻窺探到草地上的動靜,伸著觸角闖過來。老羊倌摘下手腕上的電子表,用樹根般的手指摳后蓋,雙手不停抖動。
老羊倌說,他渾身上下就這塊電子表值錢,那是在后草地坐場放牧時,從貨郎手里八塊錢買的。那時的八塊錢,要放半個月羊才能掙到。那一年,他還年輕,后草地流行起很多東西,許多小青年下海歸來,穿著喇叭褲,戴上蛤蟆鏡,手提錄音機,腕子上戴著電子表,滿臉的傲氣。他別的都不羨慕,就愛戴個電子表,那東西套在手腕上,像母親的鐲子一樣,可以貼身帶進棺材。更神奇的是,安上電池就不停地走字,就像身邊多了個會說啞巴話的伴兒。老羊倌頭頂天、腳踏地,一個人獨來獨去,白天尚好,身邊有一群羊,夜里就實在難熬。有了這個貼身伙伴,睡覺都踏實。老羊倌看不懂數(shù)字,也不需要數(shù)字,日頭就是他的鐘表,有了電子表的他,依然靠日頭出工放羊。
我?guī)屠涎蛸膿Q了手表電池后,肚子咕咕叫起來,趁著太陽的余暉,一路小跑回家。好在是下坡,到家時飯還沒涼。當晚,老羊倌挪進我家院子,輕輕敲了敲玻璃,在屋里燈光的映照下,窗戶框子里那張笑臉像是一幅木刻畫。老羊倌是稀客,這么晚來必是有事,我和母親迎出去,往屋里讓。他死活不進屋,說一身的羊騷氣,鞋底上還粘著羊糞,還是在外面說話自在。他說話時低著頭,躲避著我母親熱情的眼神,吐字時有些結巴,樣子像是來賠禮道歉似的。簡短說了幾句話后,他把一串干蘑菇硬塞給我母親,扭頭匆匆走了。母親捧著蘑菇,嗅出是上好的口蘑,頗感意外。我解釋說,我?guī)退麖逆?zhèn)上捎了塊手表電池。母親搖著頭說,這老爺子,平時看著傻傻乎乎,原來還挺有心。
忘年交就這樣一天天結成了,就在這個敖包下,老羊倌把酒壺遞給我。我搖搖頭,表示我是學生,不能喝酒。老羊倌推了推酒壺說,就喝一次,喝了這次,朋友就算交定了,咱爺倆這輩子有緣,能在這荒郊野嶺遇見不容易。我接過酒壺抿了一口,學著電影里的樣子說,好酒!
那天不是周一,也不是周五,而是周日。我隨母親去了趟梁東鎮(zhèn)的新家,回來的路上,遇見老羊倌,母親打聲招呼就先回舊家了。梁東鎮(zhèn)的新居是二層小樓,那是為梁西村所有村民準備的。母親挑好了日子,下周二搬家。其實,所謂搬家也很簡單,只是把梁西村家中的那口鍋搬過去,其余家當早就提前擺進了梁東鎮(zhèn)的樓房里。按照壩上的鄉(xiāng)俗,只要鍋不搬就不算搬,鍋搬了,新居就算敲定。空了心的梁西村,不久會被全部推平,還原為耕地。
我和老羊倌坐在敖包下喝酒,一人一口,酒壺在兩個人手中輪流傳遞,不久我的臉就變成“公雞冠”,興奮得想要打鳴。我要求和老羊倌同唱一曲,算是對這座山坡的告別。我點了幾首曲目,老羊倌都不會,只能各唱各的。我站起身來,從老羊倌的編織袋里掏出根樹枝,跳大神似的舞動身體,唱了周杰倫的《雙節(jié)棍》。老羊倌也站起身,很認真地站直身體,手拿羊鞭對著坡西村,放聲唱起了《東方紅》。我打斷了他的歌聲說,唱《東方紅》應該面向東面,你站錯方向了,那邊是西。老羊倌手搭涼棚望了一眼太陽說,陽婆婆都五桿高了,哪還分東西南北,都能照見。說完,又站直身體接著放聲高唱。他的聲音嘶啞而高亢,驚起了草叢中的一只百靈,另有一只田鼠前爪放在嘴邊,直起身體向這邊張望,我沒想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竟然有這么大的肺活量,瞬間就能讓這座山坡生動起來。這本來就是他的領地,多年占山為王,冷不丁嚎一嗓子,自然會讓生靈們肅然起敬。
唱完歌,老羊倌轉過身,向梁東鎮(zhèn)遙望。梁東鎮(zhèn)北面,新蓋了小尾寒羊養(yǎng)殖基地,一排排羊舍很齊整,紅色的彩鋼瓦屋頂在日頭下反射出刺眼的亮光。梁西村搬遷后,村里的羊會全部放到基地圈養(yǎng),一只也不剩。那些羊從此可以吃白食,不用自力更生就能按飯點填飽肚子,整齊干凈的羊舍,遠比老羊倌自己壘砌的羊圈舒適。老羊倌望著基地說,都去吧,去吧,總算把你們打發(fā)到好地方了。我聽見老羊倌說完這句話,補了一聲重重的嘆息。他為啥要嘆息呢?那些像孩子一樣被他養(yǎng)大的羊有了歸宿,他可以安心退休了,再不用像我一樣爬坡,他應該像我一樣,如釋重負才對。
我成了鎮(zhèn)里人后,不再住校,每天可以吃母親做的飯。周一不需要犯愁,只需沿著平整的水泥路就能走進學校。路邊是挺拔的楊樹,葉子有綠有黃,色彩很有層次,看著就舒心。母親給我買了雙新球鞋,上學放學,一馬平川,鞋幫子上不會沾上泥土。然而,不到一周,這條馬路就顯得單調乏味,連蛐蛐的叫聲都聽不見。周五放了學,像是有什么東西推著我,一口氣跑出鎮(zhèn)子,鬼使神差地上了山坡。
爬上坡梁,我身上多了九顆蒼耳,兩顆粘在褲腿上,三顆粘在襪子上,四顆粘在鞋帶上。這些黏人的小東西,把我引到了敖包旁邊。我站到敖包上眺望坡西村,看到那些房子依然完好地長在地面上,像一片等待采摘的蘑菇。晚霞是絕美的染料,把所有的屋頂和墻壁都涂成紅色,也包括馮八家院墻外的碾盤。我沒有看到炊煙,一縷也沒有,但村莊依然被生氣籠罩。我仿佛透視到房子有人影晃動,一些人家的炕頭上,臥著各色花貓。我甚至隱約嗅到了莜面和柴火的味道,那味道是從某個鍋臺邊散發(fā)出來的。我分明知道,母親現(xiàn)在在梁東鎮(zhèn)的家中準備晚飯,但當我的視線落到舊居后,卻感覺那里還有一位母親。
感覺如此真切,以至于我不相信那是一座空心村。我快步下坡,向映現(xiàn)出海市蜃樓般幻影的村莊走去。我走進自家空蕩蕩的院落,外屋泥砌的鍋臺上,是一個黑色的圓洞,里屋土盤的大炕上,已經(jīng)沒了炕席。強烈的失落感襲上心頭,此時哪怕出現(xiàn)一只老鼠,都會讓我找回曾經(jīng)的親切。我快步向馮八家走去,那里有我最后的希望。我想,要是老羊倌還在,我會冒著被母親責備的風險,在他家留宿。
馮八家院子里的垃圾已被清理干凈,我只彎腰撿到一個螺母。屋里的雜物也蕩然無存,只殘留著一股羊膻味。老羊倌走了,后草地那么遠,我可能從此不會再與他相見。
我并沒有離棄爬過無數(shù)次的山坡,經(jīng)常會站在敖包邊向西眺望。那座村莊消失了,消失的地方長出莊稼,秋天里,麥田一片金黃。
我向馮八打聽老羊倌的消息,馮八告訴我,他二舅在后草地給人放羊。
張瑞明:中國作協(xié)會員,小說見于《長江文藝》《長城》《莽原》等刊,出版長篇小說《察哈爾部》。獲中國青年報鯤鵬文學金獎、燕趙文化之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