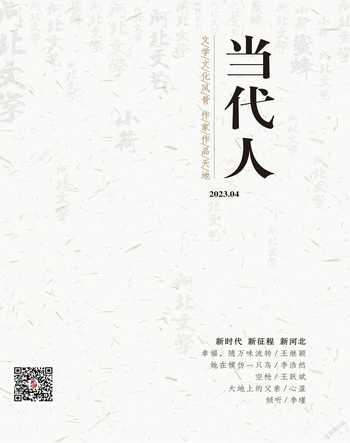在方寸間掙扎與超脫
《她在模仿一只鳥》是一篇可圈可點的小說。“我”八九歲的時候,姥姥來到“我”家,她的嘴巴尖尖的,長得像一只鳥。姥姥的到來打破了我家原本平靜的生活。她又哭又笑,到處亂跑,更怪異的是,姥姥認為自己是一只鳥,她經常在樹上攀上攀下,還筑了一只巢。直到一天,姥爺為姥姥針灸之后,姥姥來到院子里,開始迎著太陽飛奔,她身上長出羽毛,她飛過樹林,飛過田野,飛向未知的遠方。這篇小說在語言上同樣有著不可忽略的閃光點:“那是個初秋的午后,剛剛送走一場雨。”“父親則坐在客廳的小板凳上,從面前用鞋盒改裝的煙簍里取出煙紙和煙絲,面無表情地卷著煙卷兒,他把擔憂卷了進去,就著火柴頭上藍色的小火苗點著。”“他把自己抽成一座年久失修的煙筒,四處漏煙。”語言恰如其分、合榫合卯,猶如兩個武者對決,一招一式都透出干凈利落。其實,小說的語言首先要求的是這種恰當與準確,而不是光怪陸離,語言經得起推敲,才能給讀者以審美愉悅感。
李浩然的小說題材新穎、形式多變,常愛以瑰麗的想象力來承載人物和情節,頗能給人以耳目一新感。《不存在的人》中,主人公后半生在海上漂流,生命的最后一刻又在海上消失;《A面B面》以一臺錄音機串起了故事里的所有人物,酒吧老板將戒指藏在錄音機里,原想給妻子一個驚喜,不料被不知情的妹妹賣掉,“我”從酒吧買了這臺舊錄音機,又稀里糊涂地將它丟失;《妄湖水怪》分兩章,第一章的敘述者是小女孩,她父親一生都在尋找拖走母親的水怪,最終只在湖底找到母親的一只鞋子,第二章是以男青年的視角展開,男青年的前女友找到他,希望他扮演水怪來嚇退自己的現任男友,為了演得逼真,前女友還準備往水里扔一只鞋子。前后兩章相互映襯,互為表里。同樣,小說《她在模仿一只鳥》也勝在想象力,瘋瘋顛顛的姥姥認為自己是一只鳥,終日攀爬于各種樹上,最終變成鳥兒飛得無影無蹤。小說如果到此處戛然而止就顯得單薄了,在第二段出現了一只鸚鵡,“我”覺它很像我的姥姥,便把它買了下來。小說的最后一段,這只鸚鵡再次出現,它在籠中很不安分,時而蹬刨籠底,時而啄擊籠壁。這只鸚鵡的出現再次強調了人的異化,也給這篇小說增添了厚度和質感。
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部分需要用想象力來填充,靠思想來升華。莫言在復旦大學創意寫作班上演講時曾說:有一年,很多作家在一塊兒開會,給中國當代文學挑毛病。有人說我們的文學缺血性,有人說缺思想,有人說缺文化,我覺得還是更缺乏想象力。平時常有作者對我說,這件事就是真人真事,一點都沒有摻假。要知道,真人真事才沒意思呢,那是照搬生活,不叫小說,它缺乏藝術應有的輕盈、意蘊和美感。好在李浩然的想象力是不拘一格的,是天馬行空的,這也是他的作品常給讀者驚喜的一個原因。
《她在模仿一只鳥》是一篇寫人的異化的小說。在古今中外的文學長廊里,不乏異曲同工的作品:蒲松齡的《促織》中,孩子變成了蟋蟀;卡夫卡的《變形記》中,格里高爾變成了甲殼蟲;布魯諾·舒爾茨筆下的父親總是在變來變去,變成鳥,變成蟑螂,變成螃蟹。《她在模仿一只鳥》有別于經典的地方則是寫了兩個人的異化,在小說的結尾,母親得了老年癡呆,她總是臆想著自己是一條魚。此類作品中,人的肉身被社會擠壓,精神被現實禁錮,對俗世無法擺脫,對自由充滿向往,人似乎只有異化成動物才能逃離。在李浩然的筆下,常見人物掙扎的動作與痕跡,《她在模仿一只鳥》中的姥姥在現實、情感以及自己心靈之間掙扎,《不存在的人》中的主人公在紅塵俗世與精神世界之間掙扎。
其實,作家寫作也是一個于紙上掙扎的過程,人物的命運在筆下沉沉浮浮,作家的心靈幾經錘煉與搓打,才能逐漸從浮躁走向沉靜,從禁錮邁向超脫。經過生活的淘漉,李浩然的作品已擺脫了單薄與燥氣,有了豐富和沉穩,相信以后在這條道路上,他會走得更加堅定與從容。
(吳蘋,80后。作品散見《小說選刊》《紅巖》《西部》《四川文學》《安徽文學》《山東文學》《滇池》等,并多次入選年度選本。短篇《大鳥》《丟失的哪吒》入選2019年度、2020年度“城市文學排行榜”。)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