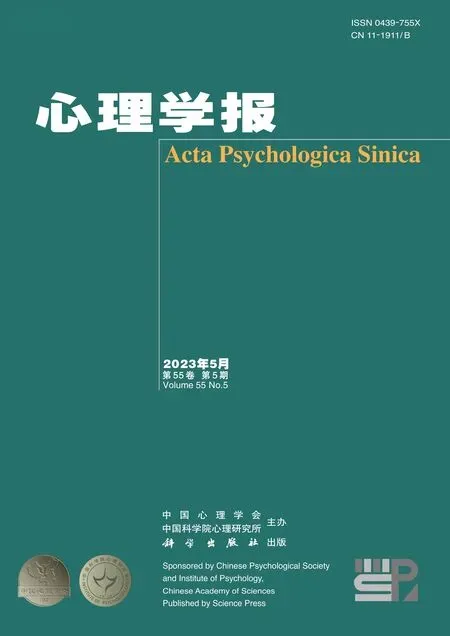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及其機制*
鄧 洵 龍思邑 沈依琳 趙歡歡 賀 雯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及其機制*
鄧 洵1龍思邑2沈依琳1趙歡歡1賀 雯1
(1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上海 200234) (2攀枝花學院就業指導中心, 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本研究基于共同內群體認同模型, 以醫務人員和患者及家屬為研究對象, 考察了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及機制。預研究通過問卷調查證明了醫患群體間存在競爭受害感; 實驗1采用共同內群體認同的操作范式, 發現共同內群體認同能夠有效減少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 實驗2A進一步發現, 權力需要在醫方和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不顯著。實驗2B采用更接近社會現實情境的重新范疇化范式, 結果顯示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 但與群體身份的交互作用顯著, 僅醫方權力需要的中介路徑成立。本研究揭示了共同內群體認同不僅能夠直接降低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 而且可以通過減少權力需要進一步降低競爭受害感, 從群際角度為緩和醫患之間的緊張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醫患關系, 競爭受害感, 共同內群體認同, 權力需要, 道德需要
1 引言
和諧醫患關系是保障醫療活動順利開展的基礎, 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 隨著醫改政策的不斷推進, 在醫療環境不斷改善和醫療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時, 我國的醫患關系卻日益緊張, 不良醫患關系引發的醫患沖突事件屢見不鮮(殷璐等, 2019)。如何加強醫患雙方之間的認同, 緩解醫患之間的矛盾, 推動和諧醫患關系的發展和建立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有研究者認為, 面對醫患沖突, 醫患雙方都會產生競爭受害感(Competitive Victimhood) (艾娟, 2018), 即群體成員認為自己所在的群體是沖突中的最大受害者, 并有策略地突出自己受到的傷害來證明自己的最大受害者身份, 以獲得第三方的同情和支持, 減少自己在群際沖突中的責任(Noor et al., 2012)。但目前仍缺乏更嚴謹的實證研究檢驗醫患之間的競爭受害感及其潛在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1.1 競爭受害感
競爭受害感是一種普遍存在于群際沖突情境下的心理現象(Young & Sullivan, 2016), 群體之間一旦產生沖突, 群體成員會認為內群體相較于外群體遭受到了更大的折磨和痛苦, 力圖證明內群體是群體沖突中的最大受害者, 不愿接觸外群體也不愿嘗試寬恕與和解, 且可以通過代際傳遞成為群體文化的一部分(Lupu & Peisakhin, 2017; Noor et al., 2012; Vollhardt & Bilali, 2015)。其產生有兩個基礎, 首先是群體之間存在社會資源的不平等, 群體雙方產生了相互競爭的傾向; 其次是對沖突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感知(Noor et al., 2008), 即競爭受害感是建立在人的主觀認知和體驗上, 而不是苦難本身的客觀嚴重程度, 強調社會對受害者身份的承認(de Guissmé & Licata, 2017)。
目前, 尚無對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實證研究, 但已有學者指出醫患沖突會使雙方產生競爭受害感, 醫方有可能強調患方在醫患沖突中對自己造成的傷害以及心理壓力(降海蕊等, 2022), 從而感知到群體受害者身份(汪新建等, 2016); 而患者作為疾病的承擔者, 有可能強調醫療資源的不平等、醫方診療行為的不恰當、態度的冷漠, 從而也參與受害者競爭(艾娟, 2018)。競爭受害感使醫患雙方對對方群體產生消極的刻板印象, 即使并沒有親身遭遇過醫患沖突, 也會在醫患互動中擔心對方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 醫患信任遭到破壞。
因此, 有必要探索有效的干預手段, 降低醫患間的競爭受害感, 促進醫患群體加強交流并就以往的矛盾達成和解, 從而減少醫患沖突、改善醫患關系。部分學者針對此問題做了研究, 如Noor等人(2012)提出增加有效的群際接觸可以有效降低群際競爭受害感, 即使是替代性的間接接觸(如想象接觸)也有同樣的效果(王珊珊, 2016), Adelman等人(2016)發現在報道中運用包容性的敘事方式也可以有效降低競爭受害感, 此外, 增進群際的共情和理解, 建立起共同的身份認同也是降低競爭受害感的有效措施(Shnabel et al., 2013)。在我國的醫療實踐中, 已有進行類似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嘗試, 如羅佳等人(2016)讓曾患乳腺癌并治愈的護士參與乳腺癌患者的術前安撫, 通過建立醫患雙重身份共情顯著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狀態, 由此可以推斷, 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干預措施適用于我國的醫患群體。然而該方法要求醫務人員要與患者有相同的病癥, 很難進行推廣, 因此有必要探尋更具有可行性的醫患共同群體身份建立方式。
1.2 共同內群體認同與競爭受害感
共同內群體認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提出, 通過重新構建社會身份, 改變對群體邊界的認知, 使沖突群體成員構建出共同的上位身份, 從“我們”和“他們”的分類轉向更具有包容性的“我們”的分類, 發展出新的共同內群體認同, 且出于內群體偏好, 群體成員對自己群體的積極情感和偏好也可能擴展到了共同的內群體, 不再關注于當前亞群體之間的沖突, 從而改善對外群體的態度(Gaertner & Dovidio, 2009)。這有助于減少消極刻板印象和群際偏見(Brochu et al., 2020), 以及因群際沖突產生的憤怒情緒(Dovidio et al., 2016), 使群際關系更加和諧。而對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啟動主要是構建一個共同的上位群體身份, 如當猶太人被鼓勵將自己和德國人看作一個上位群體(人類)時, 他們更愿意原諒德國人(Wohl & Branscombe, 2005)。當美國黑人和美國拉丁裔啟動上位群體認同(美國人)時, 對外群體的憤怒情緒降低(Ufkes et al., 2016)。同樣, Riek等人(2010)的研究也發現, 當美國黑人和白人啟動上位群體認同(美國人)時, 對外群體消極的刻板印象和群際焦慮減少。
根據CIIM模型, 建立共同的內群體認同有助于群體間態度的緩和以及競爭受害感的消除。例如, Shnabel等人(2013)發現在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間啟動共同的上位身份認同后, 可以同時滿足雙方的精神訴求, 從而增進接觸, 降低競爭受害感并達成和解; Andrighetto等人(2012)發現, 塞爾維亞人和科索沃人可以通過增進接觸和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來降低競爭受害感, 且該過程是通過增加對外群體的觀點采擇和信任實現的。雖然以上研究關注的沖突類型都屬于戰爭和民族沖突, 但仍可以從中得到啟發——如此激烈的群體沖突中產生的競爭受害感都可以通過建立共同的上位群體身份而得到減少, 那么對于我國的醫患群體而言, 該策略是否也可能有效呢?相比于戰爭和民族沖突, 醫患之間的沖突大多由相互不理解和工作或看病壓力等心理因素誘發, 其和解可能不太需要實質性的利益讓步, 僅僅是心理層面的干預就可能會有不錯的效果。換言之, 減少醫患群體間的競爭受害感對改善醫患關系可能有重要的意義。此外, 中華文化倡導以和為貴, 天下大同, 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的策略也可能更容易被我國醫患群體所接受。綜上所述, 本研究探索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啟動對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即在啟動了醫患共同的上位身份——醫患雙方作為人類共同對抗疾病的身份后(姚冰洋等, 2021), 可能會降低醫患間的競爭受害感。由此, 提出研究假設1:共同內群體認同能夠減少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
1.3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
Nadler和Shnabel (2015)基于需要模型(The Need?Based Model) (SimanTov-Nachlieli et al., 2013)提出,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是沖突雙方參與受害者競爭的基本需求。弱勢群體在群際沖突中失去了地位, 獲得較少資源, 通過突出受害者身份, 可能會獲得社會的補償和權力的賦予, 故表現出更多的權力需求(Kahalon et al., 2019; Solomon & Martin, 2019)。而優勢群體往往表現出更多的道德需求, 人們往往持有一種刻板印象, 認為優勢群體往往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或冷酷的(Fiske et al., 2002), 而弱勢群體往往是無辜的、高道德的(Branscombe et al., 2015), 所以優勢群體希望通過競爭受害者身份以恢復其道德形象, 獲得社會認同以及第三方的同情和支持, 并為群體采取暴力政策對抗敵對群體提供正當的理由(Bar-Tal et al., 2009; Belavadi & Hogg, 2018; SimanTov-Nachliel et al., 2013)。
以上理論也可應用于醫患情境中, 且醫患雙方地位具有雙重性, 雙方都既有優勢的一面又有弱勢的一面。從患方的角度出發, 醫方有更多的機會可以更便捷地獲得醫療資源, 自己處于劣勢地位, 而劣勢群體會渴望擁有權力以改善地位(Solomon & Martin, 2019), 并且在自身權力需要得到滿足時, 患方會有更積極的情緒體驗(徐簡, 2020), 因此患方有在診療過程中獲得更多權力的動機。同時, 在新聞報道中, 患方更多是以“傷醫者”的身份出現(周宏, 郝志梅, 2019), 因此有恢復其道德形象的需求, 以獲得同情和社會支持。另有調查顯示, 醫方群體也對自身權力現狀不太滿意, 對醫患權力互動的前景不樂觀(全鵬, 劉瑞明, 2016), 患方對權力需要的增加使醫方的權力受到了威脅, 削弱了他們在就診過程中的主導地位, 所以醫方也有掌握更多治療主導權的動機。此外, 醫患沖突中公眾對醫方形成了專業技術不足、過度診療、態度冷漠的刻板印象, 對醫方的道德水平持懷疑態度, 所以醫方也有恢復其道德形象的需求(呂小康等, 2019)。因此, 有必要同時檢驗醫患雙方權力和道德需要在競爭受害感產生中所起的作用。
此外, 研究證明共同內群體認同也能夠減少群體雙方的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Nadler & Shnabel, 2015; Shnabel et al., 2013)。在建立起共同內群體認同后, 醫方和患方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雙方都是對抗疾病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疾病才是共同敵人, 醫患雙方都希望能夠使病人恢復健康, 戰勝病魔, 這有利于醫患之間的平等合作。一方面, 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后醫患群體會傾向于尊重對方, 承認對方在醫療中的影響力和自主意識, 從而降低雙方對醫療權力的需要; 另一方面, 共同內群體認同意味著群體間的和解, 雙方將減少對另一方道德形象的詆毀, 那么醫患雙方的道德需要也會相應地減少(Nadler & Shnabel, 2015; SimanTov-Nachlieli et al., 2013)。綜上所述, 提出假設2: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醫方和患方作為研究對象, 在預研究基礎上通過3個實驗對假設進行驗證, 預研究通過向上海和四川3所醫院的醫務人員和患者及家屬發放競爭受害感問卷, 探討醫患間是否存在競爭受害感。實驗1探究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直接效應。實驗2A以及實驗2B在實驗1的基礎上, 進一步探究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是否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的效應中起到中介作用。
2 預研究:醫患間競爭受害感
2.1 目的
目前, 學界尚未有研究直接針對醫患群體的競爭受害感。因此, 本預研究使用Noor等人(2008)編制的競爭受害感問卷, 測量醫患雙方是否存在競爭受害感, 以及兩者間是否有差異。
2.2 方法
2.2.1 被試
本預研究招募被試265人, 其中上海和四川3所醫院醫務人員127人, 其中男性52人, 女性75人, 平均年齡為36.23 ± 9.65歲, 作為醫方的研究對象; 患者及患者家屬138人, 其中男性65人, 女性73人, 平均年齡為37.36 ± 13.91歲, 作為患方研究對象。因疫情原因無法進入住院部, 故所有研究對象都來自醫院的門診部, 患者及家屬在門診大廳和候診區填寫紙質問卷, 醫務人員在診療室和休息室填寫紙質問卷。采取自愿參與原則, 并在研究結束后, 贈予小禮物以表示感謝。
2.2.2 實驗材料
(1)競爭受害感問卷
根據Noor等人(2008)編制的問卷改編, 使其適用于醫患情境, 共有5個項目, 并根據被試所屬群體改變主語, 如:“在醫患沖突中, 患者及家屬受到的傷害比醫務人員大”, “在醫患沖突中, 和患者及家屬得到的關注相比, 醫務人員的遭遇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 采用7點計分, 從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取5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作為競爭受害感得分, 分數越高, 表明被試的競爭受害感越強。將得分與中值比較, 高于中值則說明存在競爭受害感(Noor et al., 2008)。本預研究中競爭受害感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為0.69。
2.3 結果
通過單樣本檢驗考察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與中值4的差異。結果發現, 醫方群體競爭受害感(= 5.60,= 1.00)顯著高于中值4,(126)= 18.02,< 0.001。患方群體競爭受害感(= 4.61,= 0.94)顯著高于中值4,(137)= 7.66,< 0.001。說明醫患雙方均存在競爭受害感。通過獨立樣本檢驗考察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的差異。結果發現, 醫方群體的競爭受害感顯著高于患方群體,(263)= 8.26,< 0.001, Cohen’s= 1.02。
2.4 討論
預研究的結果證明醫患之間存在競爭受害感,下面的實驗將討論如何減少醫患間的競爭受害感及其心理機制。根據共同內群體認同模型, 當沖突雙方群體建立起與群體沖突身份相關的共同內群體認同時, 可以降低其競爭受害感(Shnabel et al., 2013)。因此, 實驗1探討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3 實驗1:醫患雙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3.1 目的
預研究的結果表明, 醫患雙方存在競爭受害感。因此, 實驗1在此基礎上, 探究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3.2 方法
3.2.1 被試
通過G*power3.1計算實驗所需被試量。以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被試間方差分析作為統計方法, 設置參數中等效應量= 0.35, 顯著性水平α = 0.05, 統計功效1 ? β = 0.85, 計算得到至少需要樣本總量105人, 每組27人, 最終招募176人作為研究對象。
選取上海和四川3所醫院的醫務人員共90人作為醫方研究對象, 以及患者和患者家屬共86人作為患方研究對象。在醫患兩個群體中, 隨機將被試分配到共同內群體認同組和控制組, 其中, 醫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組共45人, 男性25人, 女性20人, 平均年齡為31.93 ± 8.87歲; 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組共45人, 男性21人, 女性24人, 平均年齡為35.38 ± 9.96歲; 醫方控制組共45人, 男性24人, 女性21人, 平均年齡為33.16 ± 7.12歲; 患方控制組共41人, 男性20人, 女性21人, 平均年齡為32.61 ± 10.05歲。
3.2.2 實驗材料及程序
(1)競爭受害感問卷
同預研究, 本實驗中競爭受害感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68。
(2)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
根據Shnabel等人(2013)的研究進行改編, 共同內群體認同條件下的被試閱讀一則文本, 描述醫患雙方是對抗疾病的共同群體, 都是抗擊疾病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控制條件的被試閱讀一則與醫患沖突及醫患身份無關的科普文本, 兩則文本字數都在200字左右。材料編制后請醫學專家對材料的合理性以及準確性進行評估并加以修改, 確定文本后, 邀請了11名心理學研究生對材料進行評定, 結果表明兩則材料的熟悉性、喚醒度, 效價均無顯著差異。
(3)實驗程序
采用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被試間實驗設計, 因變量為競爭受害感問卷得分。首先, 將被試隨機分配進到控制組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組, 閱讀相應的文本內容。隨后, 檢驗兩組的啟動效應。讓被試回答兩個根據Noor等人(2008)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問卷改編的項目如“醫方和患方共同構成了人類抗擊疾病的群體。我也屬于這一群體”, “同屬于抗擊疾病群體, 我為此感到自豪”, 采用7點記分, 取2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作為衡量指標。然后, 讓被試填寫競爭受害感問卷。實驗結束之后, 向所有被試發放小禮品以致感謝, 同時, 為了避免沖突材料帶來的消極影響, 向被試告知材料的非真實性。
3.3 結果與分析
3.3.1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操縱檢驗
通過獨立樣本檢驗考察醫患雙方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差異, 醫方群體實驗組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 6.51,= 0.62)顯著高于控制組(= 5.52,= 1.60),(88)= 3.86,< 0.001, Cohen’s= 0.82, 患方群體實驗組(= 6.47,= 0.63)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也顯著高于控制組(= 5.89,= 1.15),(84)= 2.92,0.005, Cohen’s= 0.63。這表明醫患雙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是有效的。
3.3.2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以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作為因變量, 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72) = 5.89,= 0.016, ηp2= 0.033, 醫方的競爭受害感(= 5.03,= 0.82)顯著高于患方(= 4.67,= 1.11),= 0.004, 95% CI= [0.18, 0.96];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顯著,(1, 172) = 16.58,< 0.001, ηp2= 0.088, 共同內群體認同組的競爭受害感(= 4.58,0.93)顯著低于控制組(= 5.15,= 0.96),< 0.001, 95% CI= [0.45, 1.20]; 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1, 172) = 2.66,= 0.105。
3.4 討論
實驗1通過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 對醫患雙方被試的競爭受害感進行測量, 結果發現共同內群體認同組的競爭受害感顯著低于控制組, 這說明共同內群體認同能夠有效減少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基于需要的模型提出,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是競爭受害感的產生基礎,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越高, 競爭受害感越強(Nadler & Shnabel, 2015)。所以在實驗2A中將進一步討論其中的機制, 檢驗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影響競爭受害感中的作用。
4 實驗2A: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分析
4.1 方法
4.1.1 被試
通過G*power3.1確定實驗所需被試量, 參數設置與實驗1一致, 計算得到至少需要樣本總量105人, 每組27人, 最終招募147人作為研究對象。
選取來自上海和四川3所醫院的醫務人員共71人作為醫方研究對象, 以及患者和患者家屬共76人作為患方研究對象, 患方去除問卷得分超過平均數±3個標準差的極端值3人, 剩余73人。在醫患兩個群體中, 隨機將被試分配到共同內群體認同組和控制組, 其中, 醫方共同內群體啟動組共36人, 男性14人, 女性22人, 平均年齡為30.58 ± 5.39歲; 患方共同內群體啟動組共37人, 男性18人, 女性19人, 平均年齡為31.00 ± 7.24歲; 醫方控制組共35人, 男性14人, 女性21人, 平均年齡為29.57 ± 4.71歲; 患方控制組共36人, 男性18人, 女性18人, 平均年齡為33.83 ± 7.97歲。
4.1.2 材料和程序
(1)競爭受害感問卷
同預研究, 本實驗中競爭受害感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62。
(2)權力需要問卷
根據Shnabel和Nadler (2008)的量表進行改編, 使其適用于醫患情境。共有4個項目來檢驗被試對權力的需要(如:我希望患者/醫務人員能對就診過程有更多的影響)。采用7點記分, 從1 (非常不同意)到7 (非常同意)。取4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計分。本實驗中權力需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78。
(3)道德需要問卷
根據Shnabel和Nadler (2008)的量表進行改編, 使其適用于醫患情境。共有4個項目來檢驗被試對道德的需要(如:我希望醫務人員/患者知道我的行為不是無緣無故的)。采用7點記分, 從1 (非常不同意)到7 (非常同意)。取4個項目得分的平均數計分。本實驗中道德需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84。
程序與實驗1基本一致, 被試完成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或控制后, 依次完成權力需要問卷、道德需要問卷和競爭受害感問卷。
4.2 結果與分析
4.2.1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操縱檢驗
通過獨立樣本檢驗考察醫患雙方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差異, 醫方群體實驗組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 6.71,= 0.50)顯著高于控制組(= 5.20,= 1.48),(69)= 5.80,< 0.001, Cohen’s= 1.37, 患方群體實驗組(= 6.05,= 1.03)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也顯著高于控制組(= 4.96,= 1.29),(71)=4.01,0.001, Cohen’s= 0.93。這表明醫患雙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是有效的。
4.2.2 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方差分析
對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40) = 7.96,= 0.005, ηp2= 0.054, 醫方(= 5.12,= 1.04)的競爭受害感顯著高于患方(= 4.67,= 0.98),= 0.016, 95% CI= [?1.00, ?0.10];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顯著,(1, 140) = 13.54,< 0.001, ηp2= 0.088, 共同內群體組的競爭受害感(= 4.60,0.92)顯著低于控制組(= 5.19,= 1.06),= 0.032, 95% CI= [0.04, 0.95]; 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1, 140) = 0.36,= 0.552。
對醫患雙方權力需要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40) = 12.80,< 0.001, ηp2= 0.084, 醫方(= 5.54,= 0.95)的權力需要顯著高于患方(= 4.06,= 1.04),= 0.022, 95% CI= [?0.97, ?0.08];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顯著,(1, 140) = 11.89,= 0.001, ηp2= 0.078, 共同內群體啟動組的權力需要(= 4.97,= 1.00)顯著低于控制組(= 5.52,= 0.99),= 0.009, 95% CI= [0.15, 1.06]。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1, 140) = 0.11,= 0.738。
對醫患雙方道德需要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進行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40) = 39.05,< 0.001, ηp2= 0.218, 醫方(= 6.42,= 0.67)的道德需要顯著高于患方(= 5.60,= 0.87)< 0.001, 95% CI= [?1.19, ?0.47];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1, 140) = 0.03,= 0.853。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1, 140) = 0.01,= 0.919。
以上結果表明, 與控制組條件相比, 共同內群體認同能夠有效降低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以及權力需要, 但對被試道德需要的效果不顯著。
4.2.3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
(1)各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本實驗中, 所考察的醫患雙方各變量之間的相關如表1所示, 醫患雙方共同內群體認同、權力需要和競爭受害感之間的相關顯著, 而共同內群體認同與道德需要的相關不顯著, 因此需探討權力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的中介效應(溫忠麟, 葉寶娟, 2014)。但為了更嚴謹地驗證本研究的假設, 將醫患雙方的道德需要也納入回歸方程中進行雙重中介分析。

表1 醫方(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權力需要、道德需要和競爭受害感的相關
注:*表示< 0.05, **表示< 0.01, ***表示< 0.001
(2)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雙重中介作用分析
通過PROCESS Model 4進行分析(Hayes, 2013), 分別考察醫患雙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影響中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在本實驗中,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不同操縱(共同內群體認同組、控制組)被編碼為1、0, 1代表共同內群體認同組, 0代表控制組。
醫方雙重中介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 其中權力需要的中介效應顯著, 估計值為?0.23, 95% CI = [?0.52, ?0.06], 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估計值為0.006, 95% CI = [?0.05, 0.08]。共同內群體認同對權力需要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64,= 0.006, 以競爭受害感為因變量,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48,= 0.042, 權力需要對競爭受害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0.36,= 0.003。而當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加入回歸方程之后,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預測作用不再顯著, β= ?0.26,= 0.273, 說明權力需要在醫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患方雙重中介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 括號中數字為患方路徑系數, 其中權力需要的中介效應顯著, 估計值為?0.25, 95% CI = [?0.55, ?0.01], 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估計值為0.002, 95% CI = [?0.10, 0.10]。共同內群體認同對權力需要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48,= 0.040, 以競爭受害感為因變量,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70,= 0.002, 權力需要對競爭受害感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0.52,< 0.001。而當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加入回歸方程之后,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仍然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0.46,= 0.014, 說明權力需要在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圖1 醫方(患方)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雙重中介作用圖
注:*表示< 0.05, **表示< 0.01, ***表示< 0.001
(3)中介模型的跨組比較
通過AMOS對以上中介模型進行了多群組路徑分析, 分別檢驗醫患雙方中介模型各個路徑系數的差異, 結果見表2, 各條路徑參數間差異的臨界比值絕對值均小于1.96, 說明群體身份并不調節該中介模型。

表2 中介模型在醫方和患方群體間的路徑系數差異比較
4.3 討論
實驗2A探討了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影響中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結果表明, 共同內群體認同可以有效降低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 這與實驗1的結果一致; 權力需要在醫方和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與競爭受害感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這揭示了權力需要可能是共同對抗疾病群體認同與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的潛在機制。權力需要的降低和共同內群體認同都減少了醫患間競爭受害感, 并且共同內群體認同在減少競爭受害感的同時, 減少了權力需要, 這與前人提出的理論模型相呼應(Nadler & Shnabel, 2015; SimanTov-Nachlieli et al., 2013)。然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不顯著。
5 實驗2B:重新范疇化范式的穩健性檢驗
5.1 目的
實驗2A的結果表明, 建立共同內群體認同可以通過減少醫患群體的權力需要來降低雙方的競爭受害感, 但仍有必要通過不同的方法再次檢驗其作用機制。因此, 實驗2B采用更接近社會現實情境的重新范疇化范式, 讓醫患兩個群體直接交流, 啟動醫患雙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 以檢驗中介模型的穩健性。
5.2 方法
5.2.1 被試
通過G*power 3.1確定實驗所需被試量, 設置參數與實驗2A一致, 計算得到至少需要樣本總量105人。最終選取被試108人, 每種實驗條件下27人。通過騰訊會議軟件進行線上實驗。
選取上海某兩所高校的醫學或護理學專業且有過醫院實習經歷的大學生為醫方研究對象, 以及非醫學相關專業且近半年有過就醫經歷的大學生作為患方研究對象。在醫患兩個群體中, 隨機將被試分配到共同內群體認同組和控制組, 其中, 醫方共同內群體啟動組27人, 男性6人, 女性21人, 平均年齡22.56 ± 1.22歲; 患方共同內群體啟動組27人, 男性7人, 女性20人, 平均年齡22.70 ± 2.69歲; 醫方控制組27人, 男性7人, 女性20人, 平均年齡22.70 ± 1.17歲; 患方控制組27人, 男性6人, 女性21人, 平均年齡20.63 ± 1.71歲。
5.2.2 材料和程序
(1)競爭受害感問卷
同預研究, 本實驗中競爭受害感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72。
(2)權力需要問卷
同實驗2A, 本實驗中權力需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80。
(3)道德需要問卷
同實驗2A, 本實驗中道德需要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α = 0.84。
(4)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
參考梁芳美等人(2020)使用的重新范疇化范式(Recategorization)啟動不同民族被試的共同內群體認同的方法, 即兩個小組討論寒冬野外生存問題, 并通過控制討論形式、小組名稱和虛擬背景圖片異同以操縱醫患雙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
(5)實驗程序
實驗準備階段:邀請12名有實驗經驗的心理學研究生參與預研究, 根據他們的建議對線上實驗的組織形式和流程進行了調整。
正式試驗階段:把醫患雙方被試隨機編入到36個小組中, 每組3人且所屬群體身份一致, 每次實驗由醫方和患方各一個3人小組共6人共同參與。
群體建立階段:利用騰訊會議完成線上實驗, 兩組被試和兩名主試進入到會議室, 使用騰訊會議的分組討論功能先進行兩組的組內討論, 要求被試打開攝像頭和麥克風, 并換上提前指定的虛擬背景圖片, 醫方小組為“星空”, 患方小組為“露珠”。討論開始前, 要求被試為自己的小組取一個有代表性的組名, 并將備注名改為“組名+昵稱”。接著第一輪討論開始, 兩組被試閱讀寒冬野外生存問題, 時間為7分鐘。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條件下的被試討論并自由發表對故事的看法; 控制條件下的被試討論并完成對12件生存物品重要性的一致排序, 記錄下結果。第一輪討論結束后, 告知被試他們即將與另一個小組交談, 并介紹該組的組名以及其作為醫方或患方的群體身份。
重新范疇化階段:兩組被試回到主會議室。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條件下, 主試告知6名被試“你們從墜機點逃出來后, 遇到了別的幸存者, 為了生存你們決定結伴而行, 現在請你們為自己的6人求生小隊重新取一個有代表性的名字”, 隨后再次要求他們修改自己的備注名, 并告知“現在, 由(第一組原名)組和(第二組原名)組重組而成了(新組名)組, 為了營造求生的氛圍感, 請大家把虛擬背景統一更換為‘原野’”, 之后對12件物品達成一致的排序結果, 時間為7分鐘; 控制條件下的被試不再統一組名和虛擬背景, 要求每組派一名代表向另一組匯報第一輪討論中的排序結果和理由, 另外兩人補充, 期間兩組成員只相互匯報, 不進行討論。
隨后讓被試完成操縱檢驗問題:“問題解決過程中, 兩組感覺就像一個團體”和“問題解決中, 兩組感覺就像兩個獨立的團體”, 采用7點計分, 從1 (完全不像)到7 (非常像)。隨后向被試發放權力需要問卷、道德需要問卷和競爭受害感問卷, 并告知被試實驗材料的非真實性, 發放一定數額的報酬。
5.3 結果與分析
5.3.1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操縱檢驗
通過獨立樣本檢驗考察醫患雙方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差異, 醫方群體實驗組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 4.94,= 1.49)顯著高于控制組(= 4.04,= 1.75),(52) = 2.05,= 0.045, Cohen’s= 0.55, 患方群體實驗組(= 5.06,= 1.48)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得分也顯著高于控制組(= 4.02,= 1.48),(52) =2.57,=0.013, Cohen’s= 0.70。這表明醫患雙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啟動是有效的。
5.3.2 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方差分析
對醫患雙方競爭受害感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04) = 26.52,< 0.001, ηp2= 0.203, 醫方(= 4.99,= 1.00)的競爭受害感顯著高于患方(= 4.11,= 0.83),< 0.001, 95% CI = [0.87, 1.83];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1, 104) = 1.58,= 0.212; 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顯著,(1, 104) =7.43,= 0.008, ηp2= 0.067。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 在醫方群體中, 實驗組的競爭受害感(= 4.65,= 1.05)顯著低于控制組(= 5.33,= 0.83),= 0.006, 而患方群體實驗組競爭受害感(= 4.24,= 0.96)和控制組(= 3.99,= 0.66)無顯著差異,= 0.301。
對醫患雙方權力需要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顯著,(1, 104) =24.48,< 0.001, ηp2= 0.191, 醫方(= 5.47,= 0.97)的權力需要顯著高于患方(= 4.52,= 1.06),< 0.001, 95% CI = [0.79, 1.86];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1, 104) = 1.64,= 0.204。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邊緣顯著,(1, 104) = 3.82,= 0.053, ηp2= 0.035。簡單效應分析結果顯示, 在醫方群體中, 實驗組的權力需要(= 5.16,= 1.18)顯著低于控制組(= 5.78,= 0.56),= 0.024, 而患方群體實驗組權力需要(= 4.58,= 1.05)和控制組(= 4.45,= 1.09)無顯著差異,= 0.634。
對醫患雙方道德需要進行2 (群體身份:醫方vs.患方) × 2 (群體認同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組vs.控制組)的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 群體身份的主效應不顯著,(1, 104) = 1.19,= 0.278, ηp2= 0.011;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1, 104) = 1.91,= 0.170; 群體身份和共同內群體認同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1, 104) = 1.36,= 0.247。
以上結果表明, 醫方群體中, 共同內群體認同能夠有效降低競爭受害感以及權力需要, 而在患方群體中該效應不顯著。而醫患群體之間、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道德需要都沒有顯著差異。
5.3.3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
(1)各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為了更嚴謹地驗證本研究的假設, 將醫患雙方各變量同時納入雙重中介模型中進行分析。
(2)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雙重中介作用分析
通過PROCESS Model 4進行分析(Hayes, 2013), 參數設置與實驗2A一致。

表3 醫方(患方)共同內群體認同、權力需要、道德需要和競爭受害感的相關
注:*表示< 0.05, **表示< 0.01
醫方雙重中介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 權力需要的中介效應顯著, 估計值為?0.12, 95% CI = [0.06, 0.26], 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估計值為0.001, 95% CI = [?0.07, 0.07]。共同內群體認同對權力需要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32,= 0.017, 以競爭受害感為因變量,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 ?0.34,= 0.011, 權力需要對競爭受害感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β= 0.36,= 0.009。而當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加入回歸方程之后,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預測作用不再顯著, β= ?0.23,= 0.10, 說明醫方權力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圖2 醫方(患方)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雙重中介作用圖
注:*表示< 0.05, **表示< 0.01
患方雙重中介分析結果顯示, 括號內為患方路徑系數, 權力需要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估計值為?0.02, 95% CI = [?0.14, 0.09], 道德需要的中介效應不顯著, 估計值為0.001, 95% CI = [?0.03, 0.06]。因此患方中介模型不成立。
5.4 討論
實驗2B使用重新范疇化范式實現了對醫患雙方群體的競爭受害感的啟動, 結果與實驗2A不同,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主效應不顯著, 但其與群體身份存在交互作用, 即在醫方群體中, 權力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但患方中介模型不成立, 可能是因為本實驗中的大學生患者被試與前幾個實驗中在醫院門診的患方群體被試有所差異, 本研究結果將在總討論中進行更詳細的論述。
6 總討論
6.1 醫患間競爭受害感
預研究發現, 醫患雙方都存在競爭受害感。醫患雙方本應是利益共同體, 都有著戰勝病魔、早日恢復健康的共同上級目標, 醫方精湛的醫療技術和患方的積極配合缺一不可。但如今, 醫療體制的改革加上媒體報道對醫患沖突事件的負面渲染, 使得醫患關系日益緊張, 醫患雙方站在了沖突的對立面, 都認為自己是醫患沖突中的最大受害者。
其次, 預研究也發現, 醫方的競爭受害感高于患方, 該結果在實驗1、2中也得到了證實。和患方相比, 醫務人員往往有更頻繁的醫患互動, 經歷醫患沖突的頻次更高。《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的數據顯示, 66%的醫師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醫患沖突(丁香予, 鄒軍, 2020)。《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也指出, 和患方相比, 緊張的醫患關系給醫方帶來了更多的負性情緒(王俊秀, 2018)。因此, 醫方可能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才是緊張醫患關系中處于弱勢的一方, 有更高的競爭受害感。但考慮到樣本量問題, 該結論不具有代表性, 未來仍需要更全面系統的研究進行驗證。
6.2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
當醫患雙方成員構建共同的上位身份, 發展出共同內群體認同時, 能夠有效減少彼此群體的競爭受害感, 這與以往研究發現相對一致(Andrighetto et al., 2012; Shnabel et al., 2013)。共同內群體認同使醫患雙方意識到彼此有著共同的對抗疾病的目標, 根據上級目標理論, 當兩個相互對抗的群體面對一個需要雙方聯合起來才能完成的共同目標時, 完成上級目標的需要比群際的敵對沖突關系更為重要, 群體雙方就會由對抗轉向合作, 緊張的群際關系也在合作過程中得到緩和(Sherif et al., 1961)。同時, 這種共同內群體認同模糊了群體雙方的邊界, 將內群體擴展到上位的共同群體, 對內群體的積極情感也擴展到了共同的群體, 群體成員不再關注于當前亞群體之間的沖突, 更多地看到對方群體的遭遇, 減少對外群體的消極刻板印象和偏見(Brochu et al., 2020)。另外, 共同內群體認同也增加了群體雙方的感知相似性, 由于相似的人總是相互吸引的, 進而增加了人際吸引(Alves et al., 2016), 促進群體雙方的心理融合(梁芳美等, 2020), 減少彼此之間的敵對, 從而降低競爭受害感。研究結果為共同內群體認同策略在我國醫患關系中的應用提供了實證支持和實踐依據。
6.3 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在共同內群體認同與競爭受害感之間的中介作用
實驗2A的結果表明, 權力需要在醫方和患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與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即和控制組相比, 共同內群體認同降低了醫患雙方的權力需要和競爭受害感, 權力需要的降低又進一步減少了競爭受害感。
對于醫方而言,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影響依賴于權力需要的中介作用。根據福柯的“權力—知識”理論, 醫方所掌握的專業醫學知識是權力的重要來源(袁曦, 2014)。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 患方獲得醫療知識的渠道增加, 對醫方的權力造成了威脅, 根據基于需要的模型, 醫方可能會出于維護權力的需要參與受害者競爭(Nadler & Shnabel, 2015; SimanTov-Nachlieli et al., 2013)。而共同對抗疾病的上級目標使雙方由敵對變為合作關系, 在給予了患方一定自主權的基礎上, 也保證了醫方在治療中的主導權, 使雙方矛盾的焦點從診療過程中的權力不均轉向共同對抗疾病, 減少了雙方在醫患互動中對權力的追求, 從而降低了醫患雙方的競爭受害感。另一方面, 對于患方而言, 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啟動意味著共享資源和共同合作的醫患互動模式, 使其權力需要得到了滿足(Robinson & Heritage, 2016), 減少了患方的消極情緒, 增加了對醫方的積極印象(劉陶源, 王沛, 2020), 也有助于競爭受害感的降低。
實驗2A同樣發現, 共同內群體認同與道德需要的相關不顯著, 道德需要不是共同內群體認同作用于競爭受害感的中介變量。這可能是由于, 與以往研究中難以解決的種族沖突和結構性不平等的背景相比, 醫患之間的關系雖然長期緊張, 但沖突是相對短暫、偶發的, 具有臨時性和個人性, 醫患雙方的互動和交往常常是一次性的。出于社會贊許性, 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 都希望樹立良好的道德形象, 給對方留下積極的印象, 在醫患互動中也是如此。這種社會贊許性作為一種人格特質, 是較為穩定, 難以改變的(Smith & Ellingson, 2002)。因此, 共同內群體認同并不一定能減少醫患雙方對于良好道德形象的需要。同時, 可能是由于醫患雙方都認為自己是沖突中的弱勢群體, 根據以往研究, 弱勢群體參與競爭受害感多是出于權力需要以恢復自己的地位, 獲取更多的資源, 對樹立良好道德形象的需要本就不高(Solomon & Martin, 2019)。
同時, 實驗2B通過更接近社會現實情境的重新范疇化范式, 進一步證明了醫方中介模型的穩健性。然而, 患方的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競爭受害感的作用以及中介機制都不成立, 這與實驗2A的結果不完全一致, 但也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示。數據結果顯示, 實驗2B中患方控制組的競爭受害感(3.99,= 0.66)顯著低于實驗2A的患方控制組(=5.02,=1.03),< 0.001, 且二者的差別在于前者雖然在近期有就醫經歷, 但已經離開了醫院情境, 而后者是在醫院門診環境下完成的實驗。由此可以推斷, 是否處于醫院情境可能對患者的競爭受害感產生了影響。當患者身處于醫院時, 或許會因對疾病的焦慮或排隊候診的煩躁而產生較高的競爭受害感, 而當其離開醫院后, 這種競爭受害感會逐漸降低。可能正是出于此原因, 才使實驗2B中患方控制組的基線競爭受害感水平較低, 實驗組結果難以與其產生顯著差異。同樣的, 對于醫方群體而言, 因其工作和學習環境都與醫院情境息息相關, 社交圈子也大都是同行, 所以兩次實驗中醫方控制組的競爭受害感不會因為暫離醫院環境而降低。綜上所述, 醫院情境可能對患方群體的競爭受害感具有獨特的作用, 可以通過諸如優化掛號流程、改善候診體驗等措施降低其競爭受害感。
6.4 貢獻與不足
本研究借鑒了前人關于群際沖突及和解的對策, 創新地將其應用于醫患領域, 探索了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影響和權力需要的中介作用, 為改善當今緊張的醫患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研究從三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CIIM模型的理論內容:首先, 本研究首次證明了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群體競爭受害感的顯著影響, 將CIIM模型的適用范圍從不同民族拓展到醫患群體上; 其次, 本研究證實了CIIM模型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可推廣性, 為共同內群體認同干預方法的本土化提供了實踐基礎; 最后, 實驗2A和實驗2B分別證明了閱讀文字材料以及重新范疇化范式的有效性, 豐富了CIIM模型的啟動范式。
本研究對促進良好的醫患關系富有積極的實踐啟示。建立共同的上位群體認同是一種有效的醫
患關系干預方式, 可應用于真實的醫患環境中。例如, 山東某醫院推行了暖文化服務, 其中的“親情服務關懷”和“醫患公益座談會”可以視為是建立醫患共同內群體的操作(李冠軍, 2020); 南京某醫生利用休息時間自發組織病友登山會, 在醫生與患者的關系之上又建立了朋友這層上位身份認同。其次, 鑒于權力需要的中介作用, 有必要尊重和保護醫患雙方的基本權力。一方面要保證醫方在治療中的主導權, 加強對相關醫療知識的宣傳(呂小康等, 2019), 避免患方產生如過度治療等誤解; 另一方面也應給予患方一定的自主權, 如在合理范圍內選擇某種治療方案、共享醫療信息等。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 本研究的被試僅選自上海市和四川省的3所醫院, 醫患間競爭受害感的程度可能受到地域和醫院類型因素的影響。后續研究應當擴大樣本來源, 并適當增加樣本量, 加強對不同級別城市和不同級別醫院醫方與患方的研究。同時, 由于醫沖突經歷會引發患者更多的負性情緒, 并損害醫患關系(He et al., 2020), 因此, 未來研究可以把被試過往就醫經歷納入考量, 考察就醫沖突經歷對競爭受害感的差異影響以及對共同內群體認同的干預作用。第二, 本研究采用的文字材料啟動法和重新范疇化范式是啟動共同內群體認同較常見的方法, 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更加豐富化的啟動方法, 例如, 外顯啟動法 (Glasforda & Dovidiob, 2011)和內隱啟動法進一步檢驗和提升研究結果的信效度。第三, 本研究對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測量主要基于已有的量表。未來可以嘗試探索基于我國醫患群體的權力和道德需要的心理結構, 開發出更完善的測量工具, 也可嘗試開發更加有效的實驗范式直接操作醫患雙方的權力和道德需要, 進一步檢驗中介模型。此外, 本研究僅探究權力需要和道德需要的中介作用, 未來研究有必要考察感知群際威脅(Demirda & Hasta, 2019; Riek et al., 2010)、群體信任和群體共情(Andrighetto et al., 2012; Noor et al., 2008) 等變量在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的作用。
7 結論
本文在預研究基礎上通過3個實驗探討了共同內群體認同對醫患競爭受害感的影響及機制, 得到如下結論:(1)共同內群體認同可以顯著降低醫患間的競爭受害感; (2)權力需要在醫患雙方共同內群體認同和競爭受害感之間起中介作用; (3)重新范疇化范式驗證了醫方群體中介模型的穩健性。
Adelman, L., Leidner, B., UNal, H., Nahhas, E., & Shnabel, N. (2016). A whole other story: Inclusive victimhood narratives reduce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10), 1416?1430.
Ai, J. (2018). Intergroup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doctor?patient conflicts.(1), 63?73.
[艾娟. (2018). 醫患沖突情境下的競爭受害者心理及其對策.(1), 63?73.]
Alves, H., Koch, A., & Unkelbach, C. (2016). My friends are all alike—the relation between liking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 in person perception.103?117.
Andrighetto, L., Mari, S., Volpato, C., & Behluli, B. (2012). Reducing competitive victimhood in Kosovo: The role of extended contact and common ingroup identity.(4), 513?529.
Bar-Tal, D., Chernyak-Hai, L., Schori, N., & Gundar, A. (2009). A sense of self-perceived collective victimhood in intractable conflicts.(874), 229?258.
Belavadi, S., & Hogg, M. A. (2018). We are victims! How observers evaluate a group’s claim of collective victimhood.(12), 651?660.
Branscombe, N. R., Warner, R. H., Klar, Y., & Fernández, S. (2015). Historical group victimization entails moral obligations for descendants., 118?129.
Brochu, P., Banfield, J., & Dovidio, J. F. (2020). Does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reduce weight bias? Only when weight discrimination is salient., 3020.
Ding, X. Y., & Zou, J. Media performance in doctor-patient conflict and its improvement strategies.(17), 41?42.
[丁香予, 鄒軍. (2020). 醫患沖突中的媒體表現及其改進策略., (17), 41?42.]
de Guissmé, L., & Licata, L. (2017). Competition over collective victimhood recognition: When perceived lack of recognition for past victim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another victimized group.(2), 148?166.
Demirda, A., & Hasta, D. (2019). Threat perceptio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as mediators between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evalua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Gezi park protests.(5), 953?971.
Dovidio, J. F., Gaertner, S. L., Ufkes, E. G., Saguy, T., & Pearson, A. R. (2016). Included but invisible? Subtle bias, common identity, and the darker side of "we".(1), 6?46.
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2002).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6), 878?902.
Gaertner, S. L., & Dovidio, J. F. (2009).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 categorization-based approach for reducing intergroup bias. In T. Nelson (Ed.),(pp.489?506). Psychology Press.
Glasforda, D. E., & Dovidio, J. F. (2011). E pluribus unum: Dual identity and minority group members'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contact, as well as social change.(5), 1021?1024.
Hayes, A. F. (2013)..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He, W., Wang, X. L., Zhou, X. C., & Xu, L. L. (2020). Negative expectations and bad relationships: Effects of negative metastereotypes o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1), 103?108.
Jiang, H. R., Yu, X. H., Gao, S., Shang, P. P., Cao, P., & Qiang, B. Y. Z. (2022). Influence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on perceived stress of grassroots medical staff in Jilin province.(8), 105?109.
[降海蕊, 于洗河, 高尚, 尚盼盼, 曹鵬, 強巴玉珍. (2022). 醫患關系對吉林省基層醫務人員壓力感知的影響.(8), 105?109. ]
Kahalon, R., Shnabel, N., Halabi, S., & SimanTov-Nachlieli, I. (2019). Power matters: The role of power and morality needs in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mong advantaged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452?472.
Li, G. J. (2020).(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李冠軍. (2020).(碩士學位論文). 上海師范大學]
Liang, M. F., Xiao, Z. L., Bao. Y., & Fang, Y. (2020). The promotion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on psychological compatibility.(5), 1147?1153.
[梁芳美, 肖子倫, 包燕, 趙玉芳. (2020). 共同內群體認同對心理融合的促進效應及其機制.(5), 1147?1153.]
Liu, T. Y., & Wang, P. (2020).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consistence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on the expression of doctors’ stereotypes.(2), 413?417.
[劉陶源, 王沛. (2020). 信息一致性和決策權力對醫生刻板印象表達的影響.(2), 413?417.]
Luo, J., Yu, L., Yang, Y., & Wu, H. Y. (2016). Psychological influence of doctor-patient dual identity empathy pre-visit on breast cancer patients.(24), 117?118.
[羅佳, 余雷, 楊英, 吳荷玉. (2016). 醫患雙重身份共情法術前訪視對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影響.(24), 117?118.]
Lupu, N., & Peisakhin, L. (2017).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violence across generations.(4), 836?851.
Lyu, X. K., Fu, C.Y., & Wang, X.J. (2019).Effe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refutation texts on the trust and moral judgment of patients.(10), 1171?1186.
[呂小康, 付春野, 汪新建. (2019). 反駁文本對患方信任和道德判斷的影響與機制.(10), 1171?1186.]
Nadler, A., & Shnabel, N. (2015).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Instrumental and socio-emo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needs-based model.(1), 93?125.
Noor, M., Brown, R., & Prentice, G. (2008). Prospects for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repar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Chile. In A. Nadler, T. Malloy & J. D. Fisher (Eds.),(pp. 97?1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or, M., Shnabel, N., Halabi, S., & Nadler, A. (2012). When suffering begets suffering: The psychology of competitive victimhood between adversarial groups in violent conflicts.(4), 351?374.
Quan, P., & Liu, R.M. (2016).Self-cogniti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doctors' power.(8), 67?69.
[全鵬, 劉瑞明. (2016). 醫生權力現狀和前景自我認知分析.(8), 67?69.]
Riek, B., Mania, E., Gaertner, S. L., McDonald, S., & Lamoreaux, M. (2010). Does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reduce intergroup threat?(4), 403?423.
Robinson, J. D., & Heritage, J. (2016). How patients understand physicians' solicitations of additional concerns: Implications for up-front agenda setting in primary care.(4), 434?444.
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1961)..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Shnabel, N., Halabi, S., & Noor, M. (2013). Overcoming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facilitating forgiveness through re-categorization into a common victim or perpetrator identity.(5), 867?877.
Shnabel, N., & Nadler, A. (2008). A needs-based model of reconciliation: Satisfying the differential emotional needs of victim and perpetrator as a key to promoting reconciliation.(1), 116?132.
SimanTov-Nachlieli, I., Shnabel, N., & Nadler, A. (2013). Individuals’ and groups’ motivation to restore their impaired identity dimensions following conflicts.(2), 129?130
Smith, D. B., & Ellingson, J. E. (2002). Substance versus style: A new look at social desirability in motivating contexts.(2), 211?219.
Solomon, J., & Martin, A. (2019).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s a lens to reconcili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black lives matter and blue lives matter movements.(1), 7?31.
Ufkes, E., Calcagno, J., Glasford, D., & Dovidio, J. F. (2016). Understanding how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undermines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disadvantaged-group members.26?35.
Vollhardt, J. R., & Bilali, R. (2015). The role of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victim consciousness in predicting intergroup attitudes: Findings from Rwanda, Burundi, and DRC.(5), 489?506.
Wang, J. X. (2018).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俊秀. (2018)..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Wang, S. S. (2016).(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王珊珊. (2016).(碩士學位論文)南京師范大學.]
Wang, X. J., Chai, M. Q., & Zhao, W. J. (2016).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group victimhood on collective guilt of medical workers.(1), 125?132.
[汪新建, 柴民權, 趙文珺. (2016). 群體受害者身份感知對醫務工作者集體內疚感的作用.(1), 125?132.]
Wen, Z. L., & Ye, B. J. (2014).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5), 731?745.
[溫忠麟, 葉寶娟. (2014). 中介效應分析: 方法和模型發展.(5), 731?745.]
Wohl, M., & Branscombe, N. R. (2005). Forgiveness and collective guilt assignment to historical perpetrator groups depend on level of social category inclusiveness.(2), 288?303.
Xu, J. (2020).(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徐簡. (2020).(碩士學位論文). 上海師范大學.]
Yao, B. Y., Fu, H., & Chen, Q. J. (2021).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octor-patient destiny community in COVID-19.(4), 489?491.
[姚冰洋, 付航, 陳清江. (2021). 新冠肺炎疫情中醫患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思考.(4), 489?491.]
Yin, L., Zeng, R. H., Gao, X., & Gu, J. D. (2019). Analysis on the status-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the IIIA hospital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octors, patients and family members.(12), 67?70+74.
[殷璐, 曾日紅, 高熹, 顧加棟. (2019). 三甲醫院醫療糾紛發生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醫、患、家屬三方視角.(12), 67?70+74.]
Young, I. F., & Sullivan, D. (2016).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30?34.
Yuan, X. (2014). The application of foucault’s philosophy: Analysis on micro-power i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11), 54?56.
[袁曦. (2014). 福柯哲學應用:醫患關系中的微觀權力分析.(11), 54?56.]
Zhou, H., & Hao, Z.M. (2019).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disturbance based on the report of Alexa domestic comprehensive ranking top 3 websites.(12), 70?71.
[周宏, 郝志梅. (2019). 基于Alexa國內綜合排名前三網站報道的“醫鬧”發生情況分析.,(12), 70?71.]
Influence and mechanisms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on competitive victimhood i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
DENG Xun1, LONG Siyi2, SHEN Yilin1, ZHAO Huanhuan1, HE Wen1
(1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2Career guidance Center,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Competitive victimhood i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pervasive on both sides of an intergroup conflict; it implies that one person believes their group suffers more than the other does.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growing barriers to positive intergroup relations globally, competitive victimhood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competitive victimhood in Chinese hospitals, wher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increasingly tense.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holds that by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 and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of conflict groups, members can develop a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This identity improves attitudes toward outer groups, which may help reduce competitive victimhood. The need-based model argues that power and morality are ingroups and outgroups’ basic needs. Members of both sides are threatened by power or morality and are motivated to restore their identities, affecting competitive victimhood. Therefore, it is worth studying whether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competition victimiz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what roles power and moral needs play.
In Study 1, 90 doctors and nurses and 86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three hospitals in Shanghai and Sichuan were selected in a 2 (group: doctors vs. patients) × 2 (common identity: control group vs.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design. A brief story about doctors and patients fighting disease together was used to improv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Then we used a questionnaire about competitive victimhoo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ffected competitive victimhood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Study 2A, another group of participants was selected, including 71 doctors and nurses along with 73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three hospitals in Shanghai and Sichuan. Participants underwent the same procedure as in Study 1, then completing the power and moral needs questionnaires. Study 2A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on victimhood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roles of power and moral needs. To further test the hypothesized model, we selected 54 medical students with hospital internship experience and 54 non-medical students with recent treatment experience in Study 2B, where we activated common ingroup identities using a re-categorization strategy.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In Study 1, ANOVA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s, groups with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reported lower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group and common identity. (2) Study 2A showed that power need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competitive victimhoo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ower need was significant. The moral need was irrelevant to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and is not a mediator. (3) Study 2B reconfirmed the model for doctors but not for the patients group.
Based on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this study proposed and confirme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model in the doctor-patient field in China. Additionally, the study proposed new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s should focus on other mediators, such as empathy and trust in different group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ompetitive victimhood,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ower need, moral need
B849: C91
2022-04-1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醫患關系的影響機制和干預策略研究” (項目編號:17BSH093)資助。
趙歡歡, E-mail: hhzhaopsy@shnu.edu.cn; 賀雯, E-mail: hewen@sh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