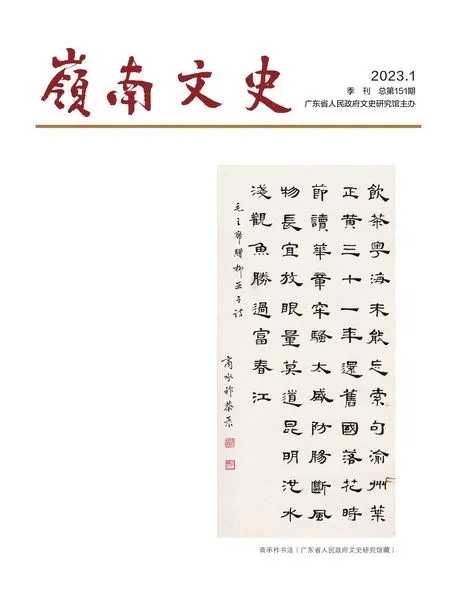中共三大:黨對形勢研判的偉大嘗試
余宏檁
黨的“三大”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發展進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特別是對廣州在近現代革命史上的貢獻有著深遠的歷史影響。從中國革命進程的角度看,“三大”是大革命的開端,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并推動了工農群眾運動的蓬勃發展;從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發展的角度看,“三大”確立了黨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在黨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長足進步,并在會后開始了武裝斗爭的嘗試,黨的“三大法寶”初具雛形;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反映了當時廣州在全國革命形勢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廣州成為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為工農運動中心和北伐戰爭的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譜寫了廣州歷史上的輝煌篇章。
一、正確分析和認識革命性質
能否正確認識形勢,能否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方針,是新成立的黨能否生存、發展的根本所在。中共三大是至今為止唯一一次在廣州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黨成立不過兩年,黨還處在幼年期,但在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面前,面臨急切需要解決一些重大問題:當時歷史時期是搞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國民革命?是推翻資產階級,還是反帝、反封建?是排拒中國國民黨還是聯合中國國民黨?中共三大圍繞這些問題進行商榷和辯論,從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全國革命形勢出發,正確地認識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工人和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做出與中國國民黨建立聯合統一戰線的重大決策,成功揭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序幕。中共三大與在1922年黨的干部會議、第一次全國“勞大”和團的一大等重要會議連續在廣州召開,體現了廣州在當時中國革命發展征途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即存在相距甚遠的兩種運動:一種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族主義運動,另一種是由中共領導的工農大眾解放運動。后者可以而且應當與前者成為聯盟,但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必須保持獨立性,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用第一種運動來控制第二種運動的企圖。隨著黨的一大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明確了本黨是革命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但對于革命性質、革命路線策略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晰的認識。“我黨同志當時都抱樂觀態度,以為可以不經過國民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可以馬上成功”。[1]中共創立伊始,即已領導農民運動,在海豐,彭湃于1922年7月促成誕生了第一個農會——赤山農會,農民運動在南方各省開展起來。但初期的農運,不斷遭到軍閥和地主的摧殘。
1922年6月,第二次護法運動又遭失敗后,孫中山認識到,要取得革命的勝利,用依靠軍閥打軍閥的辦法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必須尋求新的道路和方法。他決定改組中國國民黨,醞釀其一生中最偉大的政治轉變。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顯示中國工人階級已登上了政治舞臺。但京漢鐵路工人1923年“二七”大罷工被軍閥鎮壓后,工運暫時轉入低潮。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和現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批判了“在時局問題上封建軍閥所散布的反動論調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持的錯誤主張”,指出“解決時局問題的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治”。還指出,“為了完成無產階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主張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反對共同的敵人,使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狀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起點”。[2]在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共從實踐中認識到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并采取積極步驟,以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希望經過中國國民黨來實現工人階級與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以推動中國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1922年7月,黨的二大召開,充分分析黨所處的歷史時期,對革命的進程和目的作出科學的判斷,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規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明確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認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動力,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主張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討論中國問題,指出:“我們有可能在國民黨組織內進行工作”。[3]同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馬林的提議,做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認為“中國唯一重大的國民革命集團”,“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但共產黨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4]該“決議”對中國共產黨實行黨內合作的形式做出肯定。

1922年7月全國各地中共黨員人數狀態圖
而真正明確革命的性質,真正把革命的任務細化落到實處的是黨的三大。歷史選擇了廣州,廣州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黨、團組織發展較快的地區之一。1920年秋,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成為國內6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一。中共一大后,中共廣東支部正式成立,積極發展黨、團力量。1922年7月廣東的黨員人數僅次于上海,全國排名第二。時任中共廣東支部書記的譚平山寫給團中央負責人的信,提到廣州已有團員400多人,為全國領先。可見,當時廣東已經成為全國黨、團組織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廣州也是孫中山長期進行革命活動的大本營,具備革命發展的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1923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重建革命政權。同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遷駐廣州,著手準備在廣州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6月,陳炯明部在廣州發動叛亂,孫中山輾轉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永豐艦指揮平叛,后因孤立無援,被迫撤往上海。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擁護孫中山,反對陳炯明。此前后,李大釗與孫中山逐漸接觸并在孫中山的邀請下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最早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人。1923年3月前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維經斯基對廣州的判斷是相反的:馬林認為,廣州是唯一勿須打擾當局就可以建立常設代表處的城市,在廣州有充分的行動自由,而且只能在這里公開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和勞動大會;而維經斯基則認為:“在廣州召開一個規模較大的全國性代表大會是做不到的”,同時“反對將中央遷往廣州”。[5]1923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駐廣州。中央機關刊物和黨的理論刊物《向導》《新青年》等也隨之南遷廣州。
為進一步在全黨醞釀和確定黨的統一戰線方針,1923年6月12—20日,中國共產黨在孫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問題。會議在傳達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指示后,對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把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改造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可能性進行討論和分析。經過討論,三大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等一系列文件,認為:“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6]決定同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同時“保持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其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7]。并強調:本黨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8]第一次使用并賦予“國民革命”新的內涵。“國民革命”本是孫中山對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表達,中共三大黨綱更賦予“國民革命”以新的含義,科學地描述了其性質和任務、步驟和前途,即“中國處在現時的這種狀況之下,資產階級不能充分發展,固之無產階級自然不能充分發展,階級分化不充分的全國人民,皆受制在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之下,不能不要求經濟發展而行向國民革命。第一步且僅能行向國民革命,這種革命自屬于資產階級的性質”。[9]大會達成一致統一:鑒于國際及中國經濟社會的政治狀況,鑒于中國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業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有一個國民革命。為此,全黨當前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內外壓迫。
同時,也批評了中國國民黨依賴“外力”(即列強援助)和“專力”(單靠)軍事行動的兩個舊觀念,要求予以改變。對于工農民眾的宣傳與組織,是中共的“特殊責任”,[10]而引導工農參加國民革命,更是中共的中心工作。大會通過《勞動運動決議案》,做出關于開展工人運動的重大決策,有力地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會議還通過關于農民、婦女、青年運動等重要決議案。中共三大宣言正確地確立了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政治舞臺迅速擴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為波瀾壯闊的國民革命指明了方向和做了準備。
正是由于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狀況的正確分析,正是由于對“國民革命”性質的準確定位,才有黨的策略方針的轉變,才有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才有國民運動的興起。
中共三大確定中共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方針與具體形式,是與孫中山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針。國共統一戰線建立后,革命運動開始高漲。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實現了對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使他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賦予三民主義新的含義,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和大會“宣言”的發表,標志著大革命時期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正式建立,這成為中國革命高漲的起點。此后,中國共產黨通過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廣泛發動工農群眾,組織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裝,團結各革命階級和各族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斗爭,取得一個個勝利。
二、正確認識工農運動地位
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和發展事業的最基本力量。中共三大之后,國共兩黨密切合作,東征西討,完成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各地群眾運動的發展,顯示出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力量。
中共三大正確考察和分析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創造性地提出以黨內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主張,使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中共三大系統闡述了國民革命的依據、任務、性質、動力、步驟和前途等一系列問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形態。首次將農民革命問題寫進黨綱,通過了關于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創造性地發展了農民革命的理論。
能否正確看待農民,是幼年共產黨必須解決和面對的嚴肅問題。在黨的一大、二大上,對農民問題及農運組織還沒有過多的闡述,但當時中國大地上特別是在廣東海豐地區,農運已開展得有聲有色。據張國燾回憶,農民問題是中共三大新提出來討論的問題。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曾說:在此之前“我們很少注意農民運動”“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才注意這個問題”。[11]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全國人口很大比重,國民革命如果沒有農民的參加,是很難想象的!中共三大指出:“農民當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也很難成功。”[12]會上,毛澤東作了農民運動報告,徐梅坤介紹了農民運動的情況,農民問題提上議程,最后通過《農民問題決議案》,對農民問題提高到一個新的認識高度,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對牽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13]首次把工農聯系在一起,指出“擁護工人農民的自然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勿忘的;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14]到三屆一中全會,黨進一步指出:“農民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是最大的動力”[15]。
中共三大和中國國民黨改組后,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校,培養了大批軍事、政工干部,對建立國民革命軍、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戰爭起了重大作用。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了對工農運動的領導,全國工農運動又逐漸恢復和發展。1924年7月,廣州沙面工人罷工改變了自“二七”以后工運的消沉狀態,沉重打擊了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震動了省港。這次罷工的勝利,推動中國國民黨成立廣州工人代表會,工人還建立了工團軍,這對中國中部和北部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農民運動也迅速蓬勃發展。1924年5月,彭湃等以中國國民黨農民部農民運動特派員身份,在粵北山區廣寧縣建立支部,這是成立較早的農村黨組織。至次年5月,廣東各地已有22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達21萬多人。在此基礎上,召開了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廣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廣東農民運動終于發展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先導。
國共統一戰線建立直接推動整個革命形勢新的高漲,全國性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把革命高漲推上頂峰。1924年7—9月,全國各地都召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群眾大會。這次運動規模宏大,反帝性質明確,是在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指導下取得的。“國民會議”原是1923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號召召開的國民會議,是反對軍閥政權提出的,當時認為只有國民會議才能真正代表國民,才能制定憲法,才能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并建議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取締北京已淪為北洋軍閥傀儡的國會,產生新的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產生新的人民政府,掃蕩全國軍閥及援助軍閥的外國勢力,最終統一全國。孫中山也從歷次政治斗爭的實踐中認識到,護法口號已不能代表人民的要求,而贊成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1924年后,國民會議運動遍及全國,成為人民反對軍閥的民主運動。國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引起軍閥內部的分化,直系馮玉祥開始傾向革命。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自己的部隊改稱國民軍,并在國民會議運動發展的情況下,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在中共的幫助下,決定離粵北上,于11月10日發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宣布決不與軍閥妥協,號召全國人民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召開國民會議,以共同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北上宣言”一定程度反映出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因與中共合作,其主張由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發展到人民民主共和國,有了根本的轉變。
三、正確認識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初建時,在中共一大上,“不同其他政黨建立任何關系”“對現有政黨,應采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16]已成為既定路線。后來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下,逐步與其他政黨及派別有了聯系,但在對象的選擇上先是把偽裝進步的吳佩孚和陳炯明作為對象,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干預和牽線下,開始與中國國民黨接觸。在選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是經過艱難抉擇的,從堅決反對到采取“黨外聯合”、保持共產黨獨立地位、與中國國民黨“平起平坐”,到“中共少數負責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再到“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其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較長時間的爭論和斗爭的。從1921年7月黨的一大,到1922年4月的廣州會議,到7月黨的二大,再到8月的西湖會議,甚至到中共三大和中國國民黨一大之后,這一問題還在繼續爭論。陳獨秀在中共三大報告中所闡述的“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實際的,以后我們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17]在認識中國國民黨和最終選擇國民黨,是經過爭論和深刻分析后決定的。中共三大之所以偉大,一是承認中國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袖地位;二是承認“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廣大群眾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三是承認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曾感此必要”。[18]以共產黨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是當時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能夠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是一個大黨和一個黨員相對少得多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懸殊決定的。中共三大,在正確認識中國國情的基礎上,正確地認識革命性質,正確地認識農民地位,正確地認識中國國民黨,從而實現了對中國革命的性質、階段、方法、目的的準確判斷,完成了對中國國民黨從反對聯合到同意合作,從主張“平起平坐”的“黨外合作”,再到采取“以個人身份加入”的“黨內合作”的轉變過程。這一過程,反映了黨的策略思想的不斷深化、提高和成熟,體現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成果。這一成功嘗試,直接迎來了國共合作的建立與轟轟烈烈大革命時代的到來。
中共三大通過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明確指出:聯合并不是融合,共產黨仍然是獨立的;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改組國民黨為左翼的黨;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要利用條件先擴大國民黨;把國民黨左派吸取到我們的組織中來。“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取真正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嚴謹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19]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實際工作的正確道路”[20]。
雖然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但前進也不是一路坦途。當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之時,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廣州,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出任大元帥府宣傳委員會委員長,孫中山給宣傳委員會下撥了辦公費,中共黨員陸續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有的人并擔任了政府和黨務工作。貌似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然而,中共三大閉幕不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一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于1923年7月間回國,向俄方提出停止援助孫中山的建議;二是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回上海,大元帥府宣傳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離開廣州;三是孫中山下令撤銷宣傳委員會。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國民黨、蘇俄和中共之間,還有許多未達成一致的地方。中共三大建立國共合作的策略,任重道遠。
經過1923年七八九三個月的磨合,終于有了轉機。1923年10月,蘇俄派鮑羅廷代替馬林,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換成為李大釗,代表人的切換多了重新溝通的機會。廣州共產黨地方組織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溝通撮合作用,短時間內介紹了大批工、農、學生加入中國國民黨;協助組建并帶頭參加“國民義勇軍”,奔赴東江前線與陳炯明的軍隊作戰,保住了廣州城的穩定。這些促使孫中山轉變態度,終于達成了改組中國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共識。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會上,孫中山表明:廣州是辛亥革命的起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我們要拿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為中華民國開一個新紀元。這樣,危機終于解除。
這段歷史演變表明,廣州在1922年召開過三個重要會議,在1923年6月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三大,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一大才有完美的結局。
正是因為中共三大正確分析了革命的力量及其所處的形勢,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認識基本符合實際,確立了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策略,奠定了國民革命的基礎,并通過統一戰線,宣傳貫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各項具體政策,發動工農大眾,從而大大加速了中國革命的發展步伐。中共在革命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力量迅速壯大,擴大了社會影響,組織能力特別是對革命的領導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1925年1月,為迎接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同盟軍問題。“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中共三大首先提出并付諸實踐,進行艱苦探索和總結,造就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