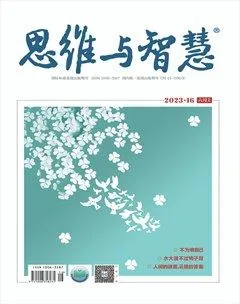跪著起花生的父親
張淑清
夜露已經被陽光吸干,風一下一下就把稻穗吹黃,把枝頭的果子吹紅了,花生蔓也日漸枯萎。父親四點鐘就醒了,醒了的父親窸窸窣窣穿好衣服,翻了翻墻上的日歷表,距離國慶節還有幾天。父親輕輕開門,在屋檐底摘了一柄月牙鐮出去了。連日來,父親都是這時候去房后的花生地轉轉。今年開春,父親在鎮種子站,買得四粒紅花生種,說是一枚花生能結四五粒花生米,屬于豐產且成熟時間短的那種。父親毫不遲疑拎了幾斤花生種回來,一樹槐花開的季節,父親將房后那塊地深挖細犁,點了花生種,就去醫院手術了。住院期間,仍不忘在電話里叮囑母親,看管好花生苗,別讓野雞田鼠糟蹋。母親找來父親的一件舊褂子,砍了一根刺槐,釘成一個十字架,用完整的葫蘆當人頭,穿上父親的衣裳,埋在花生地中央,遠遠地很像一個人站在那里。
母親呢?沒叫父親失望,為轟趕鳥雀,她到集口扯了一條幾十米的尼龍繩,選了一只音量很大的鈴鐺,鈴鐺和繩子拴在稻草人身上,另一端牢牢攥在堂屋燈繩上。哪天,母親累了,不必去花生地巡視,拉一拉燈繩,那邊就會丁零零地發出清脆悅耳的響聲,鳥們自然被驅散。
花生苗吹吹風,淋淋雨,曬曬日頭,一地月色陪伴;一滴滴露珠滋潤,一天的星斗促膝交流,有時還來幾只青蛙、一群螞蟻,在花生棵下安一個家,同花生談一場愛情,雖然是曇花一現的激情,絲毫不影響植物和小動物們熱愛生命抱團取暖的信心。當然也有母親的參與,母親給花生苗拔草,施農家糞;旱了,在坡下的一道溪流內挑水,一擔一擔地爬坡,澆花生苗。有蟲子吃花生葉片,母親頂著烈日捉蟲子。母親和父親一樣,對花生苗的感情很深。后來,父親終于出院回來了。父親的身體不允許他干重活了,他的左腿,股骨頭壞死,蹲下身十分費勁,每蹲一回,疼得他滿頭大汗。父親回來的第一件事,是到花生地走走。
八月的花生地,綠黃相間的花生棵,壟上有的花生棵裂口了,父親明白,今年的花生又是豐收。干瓜澇棗,這爿地是沙質土,適宜栽紅薯、種花生。父親是懂土地的人,他知道哪塊地該種什么,不該種什么。他是清楚土地脾氣的,父親自醫院回屯那日開始,早晚來花生地撒目一番。花生收了后,他要平均分配的。父親想好了,一部分上等的花生,留著來年做種子。一部分年底到醫院復查,帶給劉教授。一部分給兒子、女兒。最后少留一部分他和母親吃。父親一輩子不肯虧欠任何人,他覺得劉教授是給他第二次生命的人,是恩人,他送包花生,不僅是出于感恩,更是一份尊嚴。
父親這么想著,心底便有一股河流般的暖,在蕩漾,在澎湃。人有了精神原野,就升起一團一團的動力。父親來地里巡邏一遍,坐堤壩,摸摸口袋,沒帶煙。想起醫生叮嚀,不準抽煙喝酒。父親突然濕了眼眶,煙酒像他的老兄弟,跟著他幾十年。現在,他不得不放下它們,煙癮來了,就沖著花生地唱支曲子,酒癮上來,他猛灌白開水。父親,就這么安靜地守著,直至把花生守到月末,守到成熟。
父親的眉眼欣喜無限,飯桌上,父親說:“北風一陣比一陣緊了,也硬了,數數日子,該起了。”母親說:“你說哪天起,就哪天起,咱家你說了算。”
父親擇了農歷八月二十四起花生,四平八穩,事事如意,這是父親認為的。起花生,趁北風。風一刮,花生上的泥沙就干燥得快。父親沒坐馬扎,動手前,父親閉上眼,虔誠地拜了拜蒼天,才慢吞吞跪向大地。他股骨頭壞死的左腿,不能咕咚跪下,唯有慢慢地,試探著跪。父親跪在一大片花生面前,眸子里閃耀著星星般的光輝,他雙手拔起一棵花生,白晶晶的花生,像碧流河里一條條白條魚,令父親滿眼驚喜。父親是跪著,一點一點朝前挪騰。母親怕累著父親,勸父親歇一歇,父親喜滋滋地說:“花生高產,豐收了,高興著呢!不累!越起越開心!”父親剝開一枚,好家伙!居然有五粒花生米,且個頂個飽滿,圓潤!羅鍋的花生特別多,在北方,人們將多籽粒的花生,叫羅鍋。四粒紅花生,羅鍋占三分之一!父親笑得臉上的褶子像一朵綻放的菊花,顧不得跪著的膝蓋有些難受。五分地的花生,父親跪著起,母親坐著起,兩個人談笑風生。麻雀飛來,喜鵲飛來,湊熱鬧似的,啾嘰一會兒,撿一兩粒落花生,嘗嘗。母親想攆走鳥雀,被父親阻止了,豐收了,總得給鳥們留口吃的。
起出來的花生棵,先在地里晾曬一上午,待日落西山時,再扎成捆,扛到前院石頭墻繼續曬。父親時刻關注天空,一旦有烏云壓來,趕忙把花生收拾到廈子內。
五分地的花生,父親跪著起了兩天,大功告成!那晚,父親吩咐母親用柴火煮了一缽子花生,一彎月牙懸在樹梢。父親倒了一杯老窖酒,倒在地上,祭祀上天。他沒呷酒,聞一聞酒香,吃一粒花生米,再吃一粒花生米,聞一聞酒味。父親的思緒,鋪了一地銀白的月色。
(編輯 高倩/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