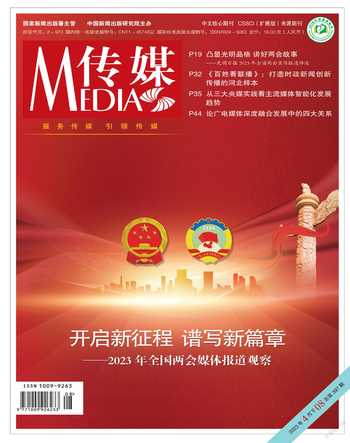“太行山經驗”在全黨辦報方針確立過程中的作用
喬傲龍 段利軍 付慧
摘要:全面抗戰初期,山西黨組織的新聞傳播以“借口說話”為主要策略,通過對敵后辦報的探索,在全黨動員和群眾參與方面積累了初步經驗。“晉西事變”之后逐步建成了獨立的、體系化的黨報網絡,并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淬煉出組織形態的武裝化、輕裝化,以通訊網支撐內容建設,以交通網和讀報組織支撐信息傳遞的“太行山經驗”,并提出“太行山經驗”為《解放日報》改版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最終沉淀為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基本路線和黨報傳播的優良傳統。
關鍵詞:山西抗日根據地 太行山經驗 《解放日報》改版
全面抗戰期間,以呂梁、太行、太岳、北岳為依托的“晉”字號根據地,背靠中共中央,近接綏、察、冀、豫,遠通熱、遼、魯、皖,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山西抗日根據地形成、鞏固和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傳播實踐經歷了“借口說話”“公開發聲”“眾口傳播”三個發展階段,凝練出一整套經驗體系,筆者稱之為“太行山經驗”。它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逐步形成的毛澤東新聞思想的實踐樣本,在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體系形成和全黨辦報方針確立的過程中曾發揮重要作用,并影響至今。
山西抗日根據地開辟之初,嚴酷的內外部環境嚴重制約著新聞事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自辦的報刊不但數量少,且多屬非公開性質,帶有較強的組織內傳播色彩。而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以下簡稱“犧盟會”)和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動總會”)卻擁有自成體系的宣傳陣容,是抗戰初期山西乃至華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傳播主體。
山西黨組織充分利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將辦報人才安排進犧盟會和戰動總會的傳播機構,借他人之口傳播自己的主張。如犧盟會長治中心區機關報《戰斗日報》,1938年7月創刊時即設有黨支部,該報發行量5000余份,幾乎覆蓋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東的山西全域。1939年《戰斗日報》停刊后創辦的《黃河日報》,工作人員以犧盟會中的中共黨員為主,發行量攀升至萬余份,是當時山西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就“晉西事變”前夕言論的立場來看,它實際上傳播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
由于當時的黨組織尚未公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自辦的報刊,“都是秘密印刷和發行”,且“發行的范圍就很狹小,數量也不大”,只是在“黨內及革命者中間輪流傳誦”。這些報刊以傳達組織信息、開展黨內教育為主要功能,以黨支部和黨小組為單位訂閱,讀報屬于“嚴格的、經常的組織生活”,具有鮮明的組織內傳播特征。還有一些報紙,借用犧盟會或戰動總會的名義公開發行。如沁源縣的《生力報》,原本是“中共沁源縣委的機關報”,只是抗戰初期“以沁源縣犧盟會名義出現”。
此類報刊是山西歷史上第一次對大眾媒介的廣泛使用,“借口說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背景下開展新聞傳播的策略選擇,既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也堅持了“以我為主”的獨立原則,在特殊條件下實現了傳播效果的最大化,為此后在根據地獨立開展新聞傳播積累了經驗。
1939年12月爆發的“晉西事變”是抗戰期間山西戰局的分水嶺。隨著國共關系的急轉直下,統一戰線范圍內的進步報刊被迫全部停刊,但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山西的行動“不需要像過去那樣,太多地考慮閻錫山及其舊派的感受”。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各根據地相繼創辦的報刊,逐漸形成縱橫交錯的新聞傳播網絡,獨立地將黨的聲音傳向四面八方。
1.“太行山經驗”的初步探索。《新華日報》(華北版)創刊前,太行山根據地的黨組織已在敵后新聞傳播方面積累了初步經驗,其精髓是全黨動員和群眾參與。
1938年5月1日創刊的晉冀豫省委機關報《中國人報》,在敵后辦報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一是內容的地方化色彩,在國際和國內新聞之外,尤為重視本地軍民開展對敵斗爭和減租減息等方面的報道。二是初步建立了通訊網,在幾乎沒有自采力量的情況下,依靠通訊網成功開展了本地新聞報道,可以說是根據地全黨辦報的最初嘗試。三是廣泛組織各地的《中國人報》讀者會,密切聯系群眾,為之后根據地的群眾辦報積累了初步經驗。該報是華北新華日報社和《新華日報》(華北版)創辦的重要基礎。
與《中國人報》同時創刊的晉冀特委機關報《勝利報》,在沒有電臺作為信息來源的條件下,通過發展通訊隊伍補充自采力量,有效解決了稿源問題,在敵后游擊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也在通俗化、大眾化方面積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經驗,是“全國各級黨報中富有濃厚地方色彩、反映強烈的一張人民的報紙”。地方內容、社會稿源、戰時傳播,以上報紙的新聞實踐為“太行山經驗”的探索、發展、推廣奠定了實踐基礎。
2.根據地新聞傳播集群的形成。《新華日報》(華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也是抗戰期間華北敵后最有影響力的報紙。1939年1月1日,以漢口總館和西安分館派到太行山的職工、原《中國人報》全體職工及其記者訓練班學員為班底,《新華日報》(華北版)在山西沁縣后溝村正式創刊。當時,各根據地的黨報社都兼具新聞采訪和編輯、圖書編輯與出版、書報刊印刷與發行、物資生產乃至設備研發等多種功能。就華北新華日報社而言,1941年成立的新華社華北總分社是報社的通訊聯絡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報社的叢書編輯部,新華書店華北總店原為報社附屬書店,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北方辦事處依托報社成立,晉冀魯豫各地的重要黨報,如《太岳日報》《冀南日報》《冀魯豫日報》等,皆系該社派出的骨干力量創辦。
除黨報外,邊區政府、八路軍部隊、各群眾團體和基層組織也有自己的報刊,由此形成了以黨報傳播集團為核心,黨、政、軍、群的報刊和基層報刊共同組成的、覆蓋全域的新聞傳播集群(見表1)。在惡劣的游擊環境和艱苦的物質條件下,這些報刊既呈現出戰時傳播因陋就簡、講求實用的特征,同時也洋溢著革命年代不畏艱險、朝氣蓬勃的精神氣質。大部分報刊油印,少數石印,個別鉛印,一塊鋼板、一臺油印機往往就是全部家當,印刷用紙更是五花八門,白報紙、麻紙、粉連紙都有。發行量有的上萬份,有的只有幾百份。報紙種類之多、隊伍之眾、參與之廣,可謂空前。
“太行山經驗”是山西敵后各根據地游擊辦報經驗的“最大公約數”,是戰爭環境淬煉而成的制度化經驗體系,其核心是以武裝化、輕裝化為特征的組織形態,以通訊網為支撐的內容建設,以交通網和讀報組織為支撐的信息渠道。
1.敵后求存的智慧結晶——輕裝游擊。由于日軍頻繁“掃蕩”,報社普遍具有濃厚的軍事化色彩,對員工進行軍事訓練并適量配備輕型武器,以備遇敵時自衛。如華北新華日報社向所有工作人員配發軍裝,配有警衛排,對外以代號相稱,且“機關代號經常變換,保密唯恐不嚴”。各根據地的新聞機構大同小異。
1942年5月反“掃蕩”中,面對日軍的清剿搜山、去而復來,數百名新聞工作者穿梭其間、迂回兜轉,對敵軍搜山規律的諳熟和能跑、能藏的生存能力,無不歸功于平時訓練所得的軍事素養。此次反“掃蕩”雖蒙受重大損失,但華北新華日報社仍然組織精干力量隨北方局堅持戰時出報,其他人員就地分散轉移,8個大大小小的印刷廠隱蔽在各地,戰時可就近出報而無輜重拖累,其“戰時油印版”與晉察冀日報社的“八頭騾子辦報”共同創造了太行山游擊辦報的奇跡。
2.全黨辦報的制度架構——通訊網。通訊網作為全黨辦報的制度架構,不僅是群眾辦報的初始動力和黨報理論轉化為傳播實踐的現實基礎,還是我黨成功進行敵后新聞傳播的重要因素,深遠影響了此后黨的新聞宣傳事業的發展。

抗戰前期,稿荒是根據地報刊普遍面臨的問題。各報在創刊之初,自采力量均嚴重不足,不得不大量采用新華社及其他境內外通訊社的稿件,從而導致新聞宣傳脫離群眾、不接地氣。毛澤東同志批評《抗戰日報》“為新華社辦報”而非“為晉綏人民辦報”,部分原因是理念的偏差,根本則在地方稿源不足。
一方面,在專職記者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報社十分重視通訊員和通訊網的建設,設有專職部門負責在機關、部隊、學校及各縣區發展通訊組織,建立通訊網,編印通訊刊物,向編輯部收轉、推選稿件或直接編輯通訊員來稿,并通過來稿發現新聞人才、補充采編隊伍。如《新華日報》(華北版)在各區村犧盟支部、農工青婦區村分會、區村公所、各級學校等建立了通訊堡壘,用通訊、贈報、稿費等方法提高通訊員采寫新聞的興趣。該報還曾公開招請“抗日救國通訊員”,并號召各地組織讀者會,集體讀報、集體寫稿。
另一方面,各級黨組織也對通訊網的建設給予大力支持。1940年初,楊尚昆在《新華日報》(華北版)撰文批評各地黨組織“未能給報紙以應有的幫助”,要求“每個同志都應該幫助《新華日報》華北版建立通訊工作,組織各地的通訊網”,幫助該報“在廣大的民眾中建立‘讀者會’”。又如,1938年8月,晉冀豫區黨委明確要求各級宣傳部“尋求約定與指定《中國人報》通訊員,建立通訊網”“各級宣傳部門應經常檢查督促執行其任務”“各宣傳部長為特約通訊員,必須經常寫通訊”。1940年9月再次下達通知,對地方黨委在報紙內容建設方面應負之責作出明確規定。1941年,進一步要求各縣委宣傳部每月至少投稿兩次,收集各方面對報紙的反映和意見,至少每月向區黨委報告一次。
以各級黨委宣傳部及其指定、約定的通訊員為核心,以分布在軍政民學機關和工農青婦等群眾救國組織中的通訊員為外圍,以地方報紙及其通訊網作為基層架構,黨報通訊隊伍在太行山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新華日報》(華北版)1939年初創刊時只有少數知識分子通訊員,當年底發展到500人左右,1941年9月發展到720人。進入“太行版”時期,規模達到2000人左右,年均來稿數量超過1萬篇。
1942年《解放日報》的改版拉開了延安新聞界整風的帷幕。4月,陸定一擔任《解放日報》“學習”版主編輯,8月被任命為總編輯。陸定一早年曾在團中央從事報刊編輯工作,遵義會議后出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后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并以中共中央北方局黨報委員會主任身份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在太行山根據地與日寇周旋3年之久。期間,他撰寫了《晉察冀邊區粉碎敵人進攻中的幾個重要經驗》《目前宣傳工作中的四個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對游擊辦報的具體措施、如何建設通訊網開展全黨辦報、如何動員群眾從讀報識字到自覺參與辦報等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宣傳工作進行了系統論述。
《解放日報》改版方案是陸定一對“太行山經驗”的延續和升華。改版后的《解放日報》不再“替外國通訊社作義務宣傳員”,根據地成為報道主體,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方針得以確立,廣大通訊員成為辦報主體。1942年10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對西北局的決定“仿此辦理”。《解放日報》改版的局部經驗迅速擴大到各根據地。可以說,《解放日報》最終成為“完全的黨報”,全黨辦報方針的最終確立,“太行山經驗”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解放日報》成功改版后,作為改革成果和全黨辦報規范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關于〈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基本未超出太行山根據地新聞實踐的范圍。
1943年,《新華日報》(華北版)停刊,改由太行區黨委出版“太行版”,根據地的新聞事業也隨抗戰局面的扭轉進入“眾口傳播”階段。隨著根據地政權的鞏固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群眾的文化覺醒推動著工農通訊員隊伍不斷壯大,基層民眾的辦報熱情被點燃,鄉村黑板報成為這一時期的獨特景觀。由邊區鉛印報、縣級油印報、鄉村黑板報共同構成的三級報網,標志著距離群眾“最后一公里”問題的根本解決。在此后的解放戰爭時期,伴隨著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群眾性新聞傳播得以在更大范圍內和更高層面上付諸實踐。
作者喬傲龍系山西傳媒學院教師、高級記者
段利軍系中共山西省委黨刊社新媒體室主任、副編審
付慧系山西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本科生
本文系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山西敵后的宣傳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20YJ2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楊尚昆.閱讀黨報推銷黨報應當是每個黨員的責任——為《新華日報》華北版一周年紀念而作[N].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01-01.
[2]中共晉冀豫區委對黨報的決定(1938年8月1日)[J].戰斗,1938(04).
[3]楊奎松.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山西農村的較力——側重于抗戰爆發前后雙方在晉東南關系變動的考察[J].抗日戰爭研究,2015(01).
【編輯: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