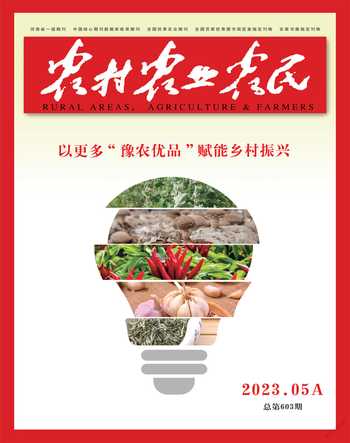李渡口筆記
高春林
一
藍河,似是從北方迤邐而來,而后在河南省郟縣冢頭鎮李渡口村村西的寨門外停泊,泊出一個水泊碼頭。站在寨墻上,看那蜿蜒而來的河流泊就的一湖碧水,或可想象一下歷史的蜃景——霧鎖遠山,行船如梭……每一只啟航的船皆是時間長河的浪花。夜幕下,點點星光悄然照臨登岸的遠航人,他們暫且結束了旅途的日月之行,踏上碼頭,匆匆地走進這個渡口村寨,有一種歸夢般的迷離之感。在我的想象里,這是一個迷離的時刻。
藍河是郟縣的三大河流之一,汝河浩蕩流長,青龍河以清澈之水注入城池,藍河來自大禹之都。《水經注》記載,藍水“出陽翟縣重嶺山”,大致發源于禹州市文殊鎮,穿過郟縣安良鎮以北的山系。及至李渡口已有大水泱泱之闊。歷史上,李渡口和中原大地上所有的農耕村落一樣,土墻灰瓦,逐水而居,人們開荒刨食,生生不息。相傳,這個村落的神奇在于建造在龜背之上,并有“五龍纏龜”之說。一個神秘的地理傳說,契合了中國古文化中趨吉避害的精神向往。
這個小村莊當地人叫“列埠口”,整個村莊西鄰藍河,據說明洪武年間依河建起了一個渡口碼頭,史稱藍河碼頭。后來,一個迄今聞名的國際商道——萬里茶道途經這里,茶船停駐成埠。萬里茶道是一條中俄茶葉之路,貫通南北。南起武夷山,途經大半個中國以及蒙古國,抵達俄羅斯恰克圖,從清朝咸豐時日益興盛。無論怎么說,藍河悠悠,綠水長流,一個水道圍攏的村寨,開啟了李渡口商運、交易、客居的碼頭繁華。
二
建筑是凝固的時間。而時間長河中每一處的建筑都在記錄著人類過往、興衰的表情和姿態。河南大大小小的村子幾乎都有一段歷史,皆可稱“古村落”。一些共同的建筑元素,譬如石墻、棚門石、把石,尤其是棚門石及其所衍生的寓意門庭顯貴的“丈石”,構成了不同的村莊石語,很多村莊都有石頭筑起的寨墻。李渡口就是這樣的所在,不同的是一條漕運泊于寨外,多出了一個碼頭,這也意味著多出了一種來自四方、山水朝供的水運繁華。
喧囂褪去,歲月變遷,鉛華洗盡,那些石頭與古磚、灰瓦所解構的樓宅庭院,歸位于一種樸素的風景,令人回味和追問,我們能感受到的是時間之流長、萬物之靈韻。我下意識里對這種樸素的古典美心生情愫。一棵百年老榆樹,一條青磚墻面的老街,讓我有一種歸來般的恍惚感。這種感覺奇特而悠遠,使我感到這樣的造訪或曰行走帶來的是身心安寧。
一個長滿青草的院子,就是李義仁故居。庭院已然不見院墻,房上的瓦松、門前的古樹、磚石筑起的房舍,在訴說著歲月滄桑。門前那一丈多的鋪門石,雖有斷裂和風化之痕,但依然顯露出顯赫的氣勢。一個有著“丈石”的庭院,是一種家族勢力甚至人格力量的象征。李義仁就具有這種人格而被后人所記起。據載,他是清乾隆年間的一個監生,當時黃河決口,他受命治水患于郟縣段,日夜苦干,大功告成,授皇封車輦——“天下第一監生”。具體的細節以及勞苦已不得而知,而久遠的時間里,村莊還記著這一段歷史。他們的記憶里深藏著敬畏和看不見的驕傲。
在一個叫作水一方居的院子,我看到了中原建筑中帶有“卍”圖形的石雕窗戶。這種帶有“卍”圖樣的石雕建筑在河南村莊比較少見。這是佛教的一個吉祥標志,起源于古印度,在傳說中有金光,如來佛胸前就帶有“卐”符號。一說是太陽或火的象征。唐玄奘、鳩摩羅什將其譯作“德”,意味著吉祥以及一些善果緣于德。學者菩提流支則譯作“萬”,意思是萬物吉祥而有永恒。武則天于長壽二年(693)將其定為“萬”來讀,即“吉祥萬德之所集”。古代用在窗戶上,便有了“萬字窗”之說。在這個古老的庭院里,在一個石雕的萬字窗前,光透過樹梢晃動的葉子散落下來,一個院子似乎瞬間澄明起來。
三
一個雨天,我在李渡口街道慢步,雨水淋漓地下在石板路上,發出清脆的聲響。我走進一個古老的院子,一個獨立的三間架構的房屋,在雨中頗有幾分遺世獨立的味道。門前屋檐下有一席空地,屋門“吱呀”一聲打開了,一個老者從屋里走來,說:“屋里坐吧。”我連忙拱手:“不了,借你的地兒躲會雨。”他笑說:“哪呀,大家的地兒。”我問:“這屋有名字嗎?”他回答:“明代,官家的。”我仰望上方,看到“德產百祿”的雕刻文字。
在明代,官邸都有著精美而優雅的裝飾、色彩,規整的院子、樓宇、廂房、景山,一應俱全,尤其是明中期建筑結構嚴謹,且有等級規制。這個房舍看上去頗有明代的建筑風格,一個標識牌上標記著:官宅屋。院墻已消失,寬闊的空地上一個孤立的房屋似有無限蒼涼之感。
這是一個時間深處的建筑,立柱、棟梁以及構造使我想到明代建筑的隱喻之詞——棟梁之材。我不由仰望屋頂——柱子上邊是一個抖拱,柱子頂著大梁,大梁撐著棟椽……棟梁,就這樣撐起一個房屋、大廈。
墻倒屋在。通俗的說法“墻倒屋不塌”。這是建筑的藝術,有人說,建筑是一種生命的再造。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這樣的村莊一種木質建筑體系的魅力——平衡、穩固與堅定。我曾有過震撼,是麗江的一次地震,在那個自然帶來的災難中,現代鋼筋水泥鑄就的房屋坍塌了,古街上的老建筑卻神奇地矗立著。我也看過河南偃師興福寺那個獨特的木質廟宇,幾乎就是研究豫西佛教建筑的一個標本。還有河南臨潁的洪山廟,十六根立柱,重梁起架,屬于典型的“墻倒屋不塌式”建筑。這種文物遺存在鄉村罕見。而在李渡口,一個題作“德產百祿”的明代屋宇屹立在這天地一隅,經風霜雨雪幾百年,構成了一個恒久的存在,似乎在講述著中國古典建筑的藝術美和生命力——歷史在風雨中飄搖,而建筑在風雨中獨立。
四
李澤之是愜意的。在為自家山墻做出那個叫歇山花的浮雕圖案時,他一定看了很久,一定興奮不已。作為一個秀才,他長時間里內心都有一個欣欣向榮的夢境,并為這個夢境去行走,甚至奔波一生。我想,這個山花就是他夢境的一次描繪和講述。李澤之沒有想到的是,山花竟然爛漫了幾百年,之后還被稱為“中原第一花”。
記得小時候家里蓋房子,我在山墻頭的滴水檐下做過一種花繪,當時什么也不懂,但依稀記下了房子上的彩繪,知道了什么是山花。現代建筑中的山花統指傳統建筑中歇山式屋頂兩側形成的三角墻面那個浮雕繪圖。我在李澤之的宅院看這些山花時心生疑問:歷經風雨幾百年,這些山花為什么依然完整而鮮亮?這里的山花有著水花的幻影——一些造型看上去皆是白色浪花幻化而成?
忽然想起這原是個水寨。對于李渡口人來說,水是他們的福祉,這個山花以水花為造型在預示這里有一條母親般的河流——藍河,這里是一個水色世界。重要的是人們在祈愿一個世界萬物滋長,源遠流長。在中國,水也是德的象征。由德而生“百祿”一直是這個村莊崇尚的一個傳統。村人說這些山花都是水洗過的。我一時有些迷茫,什么叫水洗過?原來是說山花皆是水洗的材質(水中沉淀的石灰)輔以水熬的上等糯米磨成的粉漿,然后浮雕出來的,即可一任風雨而不變形色,歷久彌新。
如此說著,不由對那山花多看了幾眼。在李渡口,每一個山花構圖各異,但都蘊含著一種市井繁華的人間況味。你看那麒麟與鳳凰呈祥而動,麋鹿、雙魚、蓮花、牡丹,還有壽桃、如意等圖案融為一體,渾然成趣,且各有寓意。它們構造了一個象征的世界,也幾乎匯集了人類的一個個夢想。如此看,山花就是一個祥瑞圖。一個光明般的圖譜,懸浮在山脊之上,寓意著祥瑞在昭示著世界,也在寤寐之間照拂著一個家族以及行走的旅人。
責任編輯:王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