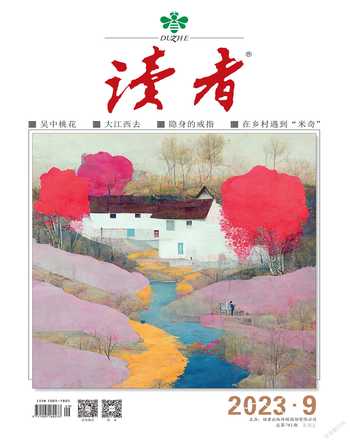隱身的戒指

24歲的杭州女孩鄭靈華,曾拿著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來到病床前向爺爺報喜,沒想到照片流出后,她因染粉色頭發而遭遇大規模網絡暴力。有人造謠“老少戀”,咒罵爺爺;有人以“發色鑒人”,拋出“一個研究生,把頭發染得跟酒吧女郎的一樣”等荒謬言論……在經歷網暴后,鄭靈華患上抑郁癥,最終離開人世。
在2022年7月經歷網暴之后,鄭靈華一邊記錄網暴者的言論作為證據,一邊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然而,在無數人為其加油鼓勵之時,她向網絡平臺發起的投訴卻屢屢失敗,網暴者也無處可尋。艱難的取證與維權之路讓鄭靈華更加抑郁,這或許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看到鄭靈華的遭遇,人們不免會問:難道我們的法律對于網暴者,真的無能為力嗎?
當然不是。對于網絡暴力,無論是《民法典》《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刑法》,都有相應的處理措施。
名譽權的本質是對他人人格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人性的幽暗體現在,我們喜歡通過指責他人的錯誤來獲得一種道德平衡感,甚至這種指責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犯過同樣的錯誤。
法律對于名譽權的保護是比較充分的,無論是侮辱,還是誹謗,都要承擔法律責任。
在網絡空間,我們很容易把他人符號化,從而忘記對方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我的同事寫過一篇文章,文中有這樣一段值得引用的話:“在網絡時代,我們似乎開始漸漸喪失了對復雜情感的體察,喪失了對他人境遇的體諒。空洞和淺薄,又最終導致了觀點的極端和情緒的殘暴。”
美國法學家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一書中,將這種現象描述為“群體極化”,即團體成員中一旦開始有某些偏向,在群體商議討論后,人們就會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非常極端的觀點。更可怕的是,如果這種極端意見集中于某個個體身上,就很容易演變成對他的網絡處刑。
這也是互聯網時代網暴滋生的深層原因。我們的情緒非常容易被極端意見挑動,也越來越傾向于對他人進行非黑即白的評判。而這種情緒和判斷,最終又會像利刃一樣刺向身處輿論旋渦的個人。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舉過一個隱身人的例子:一個牧羊人有一天走進一道深淵,發現了一枚可以使自己隱身的戒指。他利用這枚戒指勾引王后,然后跟她同謀殺掉國王,奪取了王位。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人們擁有隱身的戒指,所有的不法行為都不受懲罰,人性深處的幽暗就會被無止境地釋放。
很多人把網絡當作隱身的戒指,在這個空間中無限地釋放自己內心的幽暗。
但是,事實上,網絡從來不是能讓人隱身的戒指,人們的真實身份信息是可以被捕捉的。如何讓法律責任落到實處,讓維權之路不再遍布荊棘,是所有網絡暴力受害者的共同心愿。
不少被網暴者在尋求法律幫助的時候,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無法獲得施暴者的真實姓名,以致他們只能對著空氣戰斗,無法傷及躲藏于黑暗處的施暴者。
其實,無論是法律規定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還是刑事責任,受害者都可以通過正當的渠道來主張權利。
比如,張三同學被網暴,聯系了羅老師。羅老師建議他采取如下維權步驟。
首先,保留證據(最好在公證機關的公證下),對于所有侮辱誹謗的侵權行為通過截屏固定證據。不過這需要受害者有強大的內心,才能面對鋪天蓋地的惡意,所以也可以把這些工作交給律師等專業人士完成。
其次,走司法程序。這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讓隱蔽的網暴者現身。比如,張三同學認為網絡“大V”李四嚴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于是到法院——可以是張三同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第一步是立案,因為只有成功立案,案子才能進入司法程序。但是,這時張三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不知道網暴者的真實信息,比如姓名、電話、聯系方式,缺乏這些東西,可能無法立案。
有時,當事人或律師可以向法院申請調查令,再持調查令去各大網絡平臺調查網暴者的個人信息。在司法實踐中,有些法院出具過這種調查令。但是,也有很多法院認為,調查令在立案之后才能出具,既然還沒成功立案,又如何簽發調查令呢?所以這個法律問題,亟待解決。
所以,如果張三沒有申請到調查令,心情沮喪,那么羅老師建議張三走另外一條路,即給網絡平臺發律師函,要求網絡平臺提供網暴者的個人信息。有些平臺可能會提供,但是如果平臺不提供,張三該怎么辦呢?網絡平臺其實也很糾結,因為他們負有保護個人信息的責任。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到法院起訴網絡平臺,這些網絡平臺的信息是可以查到的。將網絡平臺作為被告,同時把“大V”李四作為共同侵權人,要求網絡平臺提供李四的個人信息。一般來說,法院就會依照職權,要求網絡平臺提供李四的個人信息。獲得了李四的個人信息,就可以去法院對李四提起訴訟,主張法律責任。
所以,如果法院可以在決定是否立案時普遍實施調查令制度,也許可以節約訴訟成本,避免殃及沒有正當理由不能隨意泄露個人信息的平臺。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到公安機關報案。既然公然侮辱、誹謗可能屬于行政不法行為,如果有足夠多的證據,那么也可以讓公安機關直接依照職權查詢違法行為實施者的個人信息。
如果要提起刑事自訴,相關步驟也可以按照剛才說的兩個方案分別進行,首先要獲得施暴者的個人信息。網絡不是能讓人隱身的戒指,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網暴案件中,很多施暴人最后也被網暴。當人們獲得某種復仇的快感時,需要思考的問題是,離開了正當的程序,我們追逐正義的初衷是否會事與愿違呢?當然,我們也希望法律提供這樣一種正當的程序,來抹去那些被傷害和被侮辱者的淚水。
村上春樹在其短篇小說集《列克星敦的幽靈》中描寫過一個遭遇集體孤立的中學生。在小說的結尾,主人公這樣說道:“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無批判地接受和全盤相信別人說法的人,是那些自己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隨著別人聽起來順耳且容易接受的意見之鼓點集體起舞的人。他們半點兒都不考慮——哪怕有一閃之念——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有錯,根本想不到自己可能無謂地、致命地傷害了一個人。真正可怕的是這些人。”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在鄭靈華同學孤獨地戰斗的時候,你我都在袖手旁觀。或許,比罪惡更可怕的,是我們對罪惡的麻木與漠然。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是平庸的幫兇。
(酣 歌摘自微信公眾號“羅翔說刑法”,本刊節選,劉 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