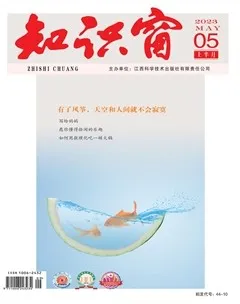在梅邊
胡新波

這段時(shí)間,我常去梅湖走走。聽人說(shuō)景區(qū)里有幾棵梅樹,我雖然不是愛花之人,但是經(jīng)歷了整個(gè)寒冬,對(duì)春的期待一點(diǎn)也不假。
那就去看花吧,在花開的時(shí)候!乍雨,乍晴,天際掠過飛鳥。此時(shí),草木青青,楊柳依依,涼風(fēng)下亭臺(tái)幾粒,游人如線。
廊橋臥波,左邊是湖,右邊還是湖。我對(duì)南昌城的印象,就是水多極了,內(nèi)四湖,外四湖,洪城的別稱名副其實(shí)。
梅湖,在洪城以南,與之西北相望的是梅嶺。這一嶺一湖,據(jù)記載是因西漢的南昌縣尉梅福而得名,這梅湖又因“八大山人”修道于此,更添幾分人文底蘊(yùn)。
過了橋,游客便多了起來(lái)。我小時(shí)候可愛熱鬧了,讀書時(shí),歷史課本上有《清明上河圖》,我記得畫中場(chǎng)景是北宋東京的初春之景,畫作兼具自然風(fēng)光與集市熙攘之貌,讓年少的我向往不已,期望能學(xué)會(huì)《聊齋志異》里的入畫術(shù),可以進(jìn)入圖中吹一吹北宋的風(fēng),聽一聽集市的吆喝聲,嘗一嘗孫記羊肉鋪的羊湯。
時(shí)過境遷,人到中年,未改的還是愛熱鬧。你瞧這一幅《初春梅湖圖》!草地上是一些帳篷,母親張著嘴給放風(fēng)箏的孩子拍著照,從口型來(lái)看,想必她說(shuō)的話是“別摔跤”。我費(fèi)了些功夫才找到父親,他正躺在兩棵樹間的吊床上,趿著一只鞋。此時(shí),風(fēng)動(dòng)床動(dòng),床動(dòng)腳動(dòng),好不愜意。賣糖葫蘆、棉花糖的攤子邊聚集著大娃小娃,另一邊排著掏出手機(jī)、掃碼支付的父母。不對(duì),還漏了個(gè)低頭大哭的紅衣小娃,原來(lái)是糖葫蘆掉地上了!
有人無(wú)花不算春。《初春梅湖圖》的下筆者想必覺得有些單調(diào),便輕沾些紅墨,灑在西南的廉政園。進(jìn)了這個(gè)拍照打卡地,我遠(yuǎn)遠(yuǎn)鑲在一邊,瞅著三兩棵紅梅,既心動(dòng)又眼紅,好不容易走近,腦海里涌現(xiàn)王安石的“墻角數(shù)枝梅,凌寒獨(dú)自開”,嘴里回味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dòng)月黃昏”。我正準(zhǔn)備品鑒懷古一番,發(fā)現(xiàn)周邊安靜下來(lái),大家似乎在等什么?我恍然大悟,原來(lái)在等我擺好姿勢(shì)拍照。獨(dú)行的我訕訕而退。
人在花中,花在人中,我把自己擺入《初春梅湖圖》,心緒不免有些起伏:對(duì)作家而言,文章有讀者的品讀,才算完成創(chuàng)作的最后一環(huán),這初春之梅想來(lái)也是如此。
在梅邊,除了看湖,看人,還能做些什么呢?野地上有三兩人在摘菜,小菜碧綠細(xì)長(zhǎng),香氣陣陣,原來(lái)是野生小蔥。我擼起袖子,掐了些蔥段裝進(jìn)塑料袋里,想著晚上叫愛人煮上一碗拉面,置牛肉幾片,撒小蔥若干,滋溜一口,挺美。目光再放長(zhǎng)遠(yuǎn)些,我小心翼翼將野蔥拔起,瞅著小蒜般的蔥根,這要植到家里陽(yáng)臺(tái),或許得改名為家蔥了。
為了看梅花,我決定,明年要來(lái)得比其他游客都早。不!我要來(lái)得比這梅花還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