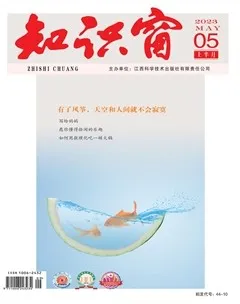泡菜釀詩
余康妮

泡菜是成都人吃飯的陪客、常客。成都人愛說“像養花一樣養泡菜”,這話聽起來很像一句詩。
成都人講究吃,吃飯當過節,做飯勝釀詩。過節不興冷清,食材自然要歡聚一堂。不搞得五花八門的、熱熱鬧鬧的,怎么能算過節!釀詩不興隨意,有咬文嚼字之工。拿什么罐,加什么料,光陰幾成,溫度幾分,心中都需有張明明白白的譜。
我早聽聞外公的老友老唐叔愛玩、會玩,他是教古漢語的老學究。那天,我見他在朋友圈里曬墨寶“不擇貴賤,皆入我甕”,以為他在講收徒,有教無類之說。外公卻笑道:“他在說他的泡菜呢。”
“不擇貴賤,皆入我甕。”原來,這八個字展開來說,應當是“不擇蔬菜貴賤,皆入甕”。老唐叔家世代生活在成都,成都的冷風一吹起,老唐叔就要開始為吃泡菜做準備。后來,有一回我們趕巧途經成都,他便邀我們去他那坐坐。
“我這一壇子喲,包羅萬象!”談起泡菜,老唐叔面龐一紅,起身領我們去廚房看他的作品。廚房里的寶貝不少,被收拾得井井有條,我一眼就看見了他的泡菜罐子。我湊近那幾壇玻璃罐子,感覺自己正置身于一個泡菜藝術館。真的,這些隔著玻璃的各式泡菜鮮亮色澤,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藝術,這是一種很天然的、很動人的視覺藝術。
原來這就是“不擇貴賤”,這些“巴適”地窩在罐子里頭的食材,平時看著灰頭土臉,毫不起眼,這會兒卻晶瑩鮮妍,像寶石,像玉帶,像綢緞,各有各的美,又是那樣的樸實。大概這就是農作物,總把光鮮的一面深掩,畢竟誰是靠光鮮勝出的呢?它們在地里時,早就被教導,要謙卑,要謙卑。
“泡萵筍條條、泡青菜梆梆、泡蘿卜纓纓、泡蘿卜皮皮、泡蓮花白腳腳。都好吃!”老唐叔像是在喊自家娃娃。“都是些大自然的東西,好東西!”爸爸感嘆道。老唐叔還在招呼大人,我和弟弟好奇地纏著老唐叔的愛人問這問那。他愛人是極熱心的人,總是笑盈盈地回答我們。她抱起一只汁水豐盈的紅皮蘿卜,教我們一劃成四,泡進壇里,剩下的事情只管安心地交給時間。待幾日過后,蘿卜就會由里到外變成粉紅色。
我的心真實地被打動了,是被這做飯的、吃飯的認真勁兒,還是被大自然積極參與,相互作用的整個醞釀過程?大概都有吧。恰如每個漢字無貴賤,各種蔬菜也很平等地被拾掇妥當,而后交給光陰封存,交由時針寫詩。晝是留白,夜是濃墨。
次日清晨,老唐叔招呼我們吃早飯,桌上一碟爽口的泡菜令我至今還覺余味猶存。原來,那是老唐叔夫婦昨晚特意為我們準備的“洗澡泡菜”。經二人用心料理,加一夜時光醞釀,我們才有享用這新鮮撈出來的佐餐的口福,咬上一口,脆生生,久久回甘。
平凡的清晨,飯桌上的笑聲和著香味在這間蜀地人家一方小桌的碗筷間流連。這樣的場景,日日在這里的許多人家上演。把平淡的日子釀成值得細品的回味,正如將普通的蔬菜變成各式佳肴,這正是千百年來巴蜀人擅長和推崇的。
如今,成都川菜博物館里還居住著不少老四川的、老成都的寶貝。一個天青色的泡菜壇子,外頭鋪著水墨江山,里頭裝著千百年來蜀地人做飯的、吃飯的“講究”。這些如同釀詩一般的講究,飄著泡菜獨有的醇香,還蘊含著千古江山悠悠的文化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