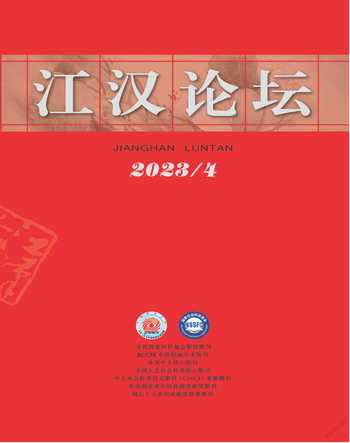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與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超越
摘要:后發(fā)國家的現(xiàn)代化總體上呈現(xiàn)出邊緣性和依附性,存在被遺忘的現(xiàn)代化角落,以偏遠(yuǎn)農(nóng)村和城市貧民窟為空間承載的現(xiàn)代化角落生存著大量權(quán)利貧困的農(nóng)民和貧民。權(quán)利貧困是交換權(quán)利與可行能力的組合貧困,一些后發(fā)國家權(quán)利貧困的政治根由是“不自由的民主”,而基于私有制的社會保障則是導(dǎo)致權(quán)利貧困的政策因素。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xiàn)代化,其光芒之所以能夠照耀每一個角落,就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zhí)政對邊緣空間和弱勢群體的權(quán)利賦予,相應(yīng)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通過全面脫貧、鄉(xiāng)村振興和社會保障,國家資本取代私人資本實(shí)現(xiàn)對現(xiàn)代化角落生產(chǎn)和生活要素的持續(xù)輸血和合理賦值,杜絕逐利資本無序擴(kuò)張對邊緣空間和原子化個體的剝奪和排斥;以最廣泛、最真實(shí)、最管用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shè)來盡可能地創(chuàng)設(shè)機(jī)會平等和權(quán)利均衡。中國式現(xiàn)代化實(shí)現(xiàn)了對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將為后發(fā)國家跳出現(xiàn)代化角落的窠臼貢獻(xiàn)中國智慧和中國樣本。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中國式現(xiàn)代化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新時代縣域政府治理效能評估及提升路徑研究”(項(xiàng)目編號:20AZZ011)
中圖分類號:D61;D50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23)04-0051-05
一、問題的提出:現(xiàn)代化角落與權(quán)利貧困
現(xiàn)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yuǎn)并且無可逃避的長周期社會變革,而“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對因素能以同等速率適應(yīng)這些變革,社會動蕩可能會變得不可收拾以致廣泛的暴亂突如其來,大批大批的人被迫出走”(1),這將徹底瓦解傳統(tǒng)社會長期封閉和靜止的穩(wěn)態(tài)。現(xiàn)代社會的個體相應(yīng)地日益原子化,即“脫離了傳統(tǒng)共同體的系留之地,除了直系親屬外,他和其他人都隔離了。在這種境遇下,孤獨(dú)、不安全和人際密切關(guān)系的削弱,使個人喪失了宜于心態(tài)穩(wěn)定的環(huán)境”(2)。而且,即使經(jīng)濟(jì)增長實(shí)現(xiàn)了總量提升,“有些階層也仍有可能遭受極為嚴(yán)重的絕對貧困”(3)。事實(shí)上,現(xiàn)代性的自由與平等理念雖是批判封建特權(quán)的利刃,但它不意味著對物的平等占有,而僅是指人們享有占有的平等資格。同時,市場自由競爭的“優(yōu)勝劣汰”和結(jié)果的“贏家通吃”必然生成實(shí)質(zhì)不平等。西方的道德觀念為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作了詭辯:“有勞動能力的人失業(yè)永遠(yuǎn)是咎由自取”(4),“清教把任何窮人都視為好逸惡勞或者罪犯”(5)。這種道德觀念亦得到了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理論的支持,譬如薩伊定律就強(qiáng)調(diào)供給會創(chuàng)造需要,自動實(shí)現(xiàn)市場均衡,而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并不存在,所謂失業(yè)僅為摩擦性或自愿性失業(yè)。
歷史與現(xiàn)實(shí)證明,無論是主動擁抱還是被動裹挾,傳統(tǒng)制度延存、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薄弱和資本積累匱乏的后發(fā)國家的現(xiàn)代化總是外部呈現(xiàn)出邊緣性和依附性,內(nèi)部制造著被遺忘的現(xiàn)代化角落,即以偏遠(yuǎn)農(nóng)村和城市貧民窟為空間承載,生存著大量權(quán)利貧困的農(nóng)村居民和城市貧民。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累積,形成了貧富分化和社會對立,民主衰敗和政治動蕩,經(jīng)濟(jì)停滯和福利低下。權(quán)利貧困是貧困的深層內(nèi)核,其實(shí)質(zhì)是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的組合貧困。交換權(quán)利是指一個人在市場經(jīng)濟(jì)中可以將所擁有的商品通過貿(mào)易、生產(chǎn)或者兩者兼有的方式轉(zhuǎn)換成另一組商品的能力。(6)事實(shí)上,正是由于除勞動力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出賣的工人階級不斷壯大,造成了“不依賴貿(mào)易的保障”的普遍缺乏,這導(dǎo)致在一個龐大的工資勞動者階級出現(xiàn)之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階段更容易發(fā)生饑荒。(7)可行能力則是一個人所擁有的有理由享受和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shí)質(zhì)自由,貧困就源于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而不能按照通行標(biāo)準(zhǔn)將其簡單地歸為收入低下。(8)可行能力方法的提出超越了對生活手段的關(guān)注,而轉(zhuǎn)向?qū)嶋H的生活機(jī)會的視角。(9)因此,社會個體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的欠缺源于生存資源的社會剝奪和排斥、獲取機(jī)會平等的能力不足和社會權(quán)利的相對缺失,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不在于一個人事實(shí)上最后做什么,而在于他實(shí)際能夠做什么,而無論他是否會選擇使用該機(jī)會”(10)。如果不抑制資本的無序擴(kuò)張,不規(guī)范財富的積累形式,則“企業(yè)家不可避免地漸漸變?yōu)槭忱撸絹碓綇?qiáng)勢地支配那些除了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人”(11),后發(fā)國家也必然淪為“金融資本的仆從,變成了從屬于金融資本的債務(wù)國家”(12)。
基于此,本文試圖以拉美國家為例來分析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的政治根由和政策因素,并揭示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如何跳出現(xiàn)代化角落的窠臼,從而實(shí)現(xiàn)對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的。
二、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的政治根由和政策因素
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源于硬性照搬西式民主而形成的“不自由的民主”窘境,而基于私有制的社會保障則成為權(quán)利貧困生成的政策因素。這表明,權(quán)利貧困的治理需要政治秩序和政治民主的實(shí)現(xiàn),需要作為共享機(jī)制的社會保障來促成權(quán)利的均衡賦予。
(一)權(quán)利貧困的政治根由:硬性照搬西式民主而生成的“不自由的民主”
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的消解,需要實(shí)現(xiàn)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的均衡配置,而均衡配置的實(shí)現(xiàn)依賴于幾種工具性自由,阿馬蒂亞·森將其劃歸為政治自由、經(jīng)濟(jì)條件、社會機(jī)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hù)性保障五種,這幾種工具性自由有助于形成社會個體的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他認(rèn)為,“自由不僅是發(fā)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fā)展的主要手段……政治自由有助于促進(jìn)經(jīng)濟(jì)保障。社會機(jī)會(以教育和醫(yī)療保健設(shè)施的形式)有利于經(jīng)濟(jì)參與。經(jīng)濟(jì)條件(以參與貿(mào)易和生產(chǎn)的機(jī)會的形式)可以幫助人們創(chuàng)造個人財富以及用于社會設(shè)施的公共資源”(13)。透明性保證所涉及的是滿足人們對公開性的需要:在保證信息公開和明晰的條件下自由地交易。防護(hù)性保障可以提供社會安全網(wǎng),以防止受到影響的人遭受深重痛苦甚至挨餓和死亡。(14)不同類型的自由可以相互補(bǔ)充,并相互強(qiáng)化。從根本上講,民主政治“有助于防止饑荒或其他經(jīng)濟(jì)災(zāi)難……民主政府需要贏得選舉并面對公共批評,從而有強(qiáng)烈的激勵因素來采取措施,防止饑荒或其他類似的災(zāi)難。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發(fā)生在有效運(yùn)行的民主體制中,不管是經(jīng)濟(jì)富裕的國家,還是相對貧窮的國家”(15)。
問題在于后發(fā)國家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民主體制衰落,無法生成工具性自由,不能實(shí)現(xiàn)對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的培育,從而形成了嚴(yán)重的權(quán)利貧困。以拉美國家為例,其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民主化事實(shí)上將建立民主與維護(hù)民主完全割裂。周期性的選舉活動表明民主制度建立了,但在投票結(jié)束后,選舉期間相互爭論的諸多議題似乎在驚人的默契之下被束之高閣,并沒有多少人關(guān)心議題能否進(jìn)入政治議程和得到解決。從世界范圍看,后發(fā)國家對西方選舉制度的模仿,如果沒有帶來令人滿意的民主治理績效,就只能說建立了選舉民主體制,但并沒有形成維護(hù)這一體制的能力,選舉并沒有為民主體制輸入足夠多的正當(dāng)性。事實(shí)上,選舉政治對復(fù)雜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問題的折射功能在弱化,這集中反映在政黨政治的深刻變化上,即政黨的組織動員功能日益讓位于媒體,政黨體系日益碎片化,公眾的政黨傾向日益轉(zhuǎn)向?qū)φ稳宋锏恼J(rèn)知和認(rèn)可,公眾對政黨的信任感下降,這勢必造成政治精英和政治權(quán)力的個性化,使政治人物放棄本應(yīng)關(guān)注的深層政治、經(jīng)濟(jì)和社會問題,而將能否討好媒體與選民、能否騙取曝光度和選票作為政治議題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
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經(jīng)濟(jì)增長當(dāng)然可以提供部分政治合法性,特別是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時,社會公眾可能并不在意民主參與問題,但如果出現(xiàn)了普遍性的經(jīng)濟(jì)衰退或重大突發(fā)自然災(zāi)害,“民主的保護(hù)性力量——如在民主國家防止饑荒中所起的作用那樣——就被強(qiáng)烈地懷念了”(16)。“經(jīng)濟(jì)的激勵因素盡管是重要的,卻不能取代政治的激勵因素,而且,如果缺少適當(dāng)?shù)捏w系來提供政治的激勵,由此造成的空白是不可能由經(jīng)濟(jì)激勵機(jī)制的運(yùn)行來填補(bǔ)的”(17)。消解權(quán)利貧困,生成交換權(quán)利和可行能力,當(dāng)然需要市場交換來提供經(jīng)濟(jì)自由,也需要政治自由所創(chuàng)設(shè)的程序正義和實(shí)質(zhì)正義來促成工具性自由中的社會機(jī)會和防護(hù)性保障。
(二)權(quán)利貧困的政策因素:基于私有制的社會保障
經(jīng)濟(jì)富裕與實(shí)質(zhì)自由并不必然呈現(xiàn)簡單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社會弱勢群體的受剝奪程度與發(fā)展中國家相差無幾。這就需要關(guān)注社會組織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包括公共衛(wèi)生、醫(yī)療保障、學(xué)校教育、社會凝聚力與和諧程度。我們是只看生活的手段,還是看人們實(shí)際享有的生活本身,這兩者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18)。在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初期,當(dāng)然也存在著大量的失業(yè)或不充分就業(y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卻會被農(nóng)業(yè)部門所緩解甚至掩飾。在較低發(fā)展國家,城市工人通常不割裂與鄉(xiāng)村共同體的聯(lián)系,以便在需要的時候可以轉(zhuǎn)身回去求得支持”(19)。而伴隨著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解體,社會個人日益被原子化,“只能在那些能夠提供他就業(yè)、醫(yī)療、社會福利和退休金的較大的非人格的公共或私人組織之間尋找出路”(20)。
問題在于貪婪資本驅(qū)動的放任自由競爭會形成弱肉強(qiáng)食的叢林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失控的勞資沖突,累積生成“末日危機(jī)”,資本家被迫接受基于私有制的適度社會保障(福利國家),以圖部分矯正初次分配不公,淡化勞工大眾革命與改革的意愿,維系資本統(tǒng)治秩序。在利潤和效率取向的市場機(jī)制下,與稀缺的資本和技術(shù)要素相比,勞工大眾的賦值偏低,且稟賦存在差異的勞動者會遭遇不均等的機(jī)會配置,從而帶來初次分配的不公。市場是迄今為止人類基礎(chǔ)性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模式,但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基于市場機(jī)制的初次分配必然導(dǎo)致收入不平等,累積生成貧富分化。“如果沒有作為社會共享機(jī)制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不可能化解社會成員可能遭遇的各種生活風(fēng)險,也不可能縮小初次分配或市場化分配下的收入與消費(fèi)差距,更遑論共同富裕”(21)。
后發(fā)國家將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視為現(xiàn)代化的主體,但需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社會福利間保持動態(tài)平衡。沒有經(jīng)濟(jì)發(fā)展保障的社會福利不可維系,而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的政治穩(wěn)定難以持續(xù),政治動蕩會讓經(jīng)濟(jì)改革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化為泡影。歷史事實(shí)表明,后發(fā)國家堅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優(yōu)先,政治民主和社會福利的相對滯后是合理的,但不能長期滯后,“逐步跟上”和“小步快走”是可取路徑。需要關(guān)注的是,歐洲奉行的“社會凱恩斯主義”雖然帶來了福利國家,但出現(xiàn)了“福利主義”的危機(jī),而美國奉行的“按揭凱恩斯主義”放任超前消費(fèi),則造就了豐饒與貧困孿生的美國式奇景(22)。后發(fā)國家如果基于私有制的社會保障予以政策回應(yīng),顯然難以消解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無法真正實(shí)現(xiàn)社會公平與正義。
三、中國式現(xiàn)代化何以能跳出現(xiàn)代化角落的窠臼
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現(xiàn)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xiàn)代化,其光芒能夠照耀每一個社會角落。中國式現(xiàn)代化之所以能跳出現(xiàn)代化角落的窠臼,就在于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執(zhí)政理念,主要通過以下兩種路徑實(shí)現(xiàn)了對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的消解。
(一)通過全面脫貧、鄉(xiāng)村振興和社會保障,國家資本取代私人資本實(shí)現(xiàn)對現(xiàn)代化角落生產(chǎn)和生活要素的持續(xù)輸血和合理賦值
中國體制的社會主義屬性要求用國家資本對現(xiàn)代化角落的生產(chǎn)和生活要素進(jìn)行合理賦值和持續(xù)輸血。目前分布在基礎(chǔ)性行業(yè)和支柱產(chǎn)業(yè)的國有資產(chǎn)關(guān)系到國民經(jīng)濟(jì)命脈、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可以成為全面脫貧、鄉(xiāng)村振興和社會保障的排頭兵和主力軍,其持續(xù)發(fā)展壯大可以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堅實(shí)的物質(zhì)基礎(chǔ)。
回顧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的扶貧戰(zhàn)略,可以看出其具有顯著的階段性特征。其一,體制扶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讓最會種田的農(nóng)民掌握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結(jié)合農(nóng)村水利建設(shè)和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推廣,讓農(nóng)民增產(chǎn)增收;同時,允許農(nóng)村興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村辦企業(yè),農(nóng)村集體資產(chǎn)和農(nóng)民非農(nóng)收入得以增加。二是允許城市個體工商業(yè)經(jīng)營,以緩解下鄉(xiāng)知青大量集中返城帶來的嚴(yán)重就業(yè)問題和生存問題。這一階段雖然沒有正式的扶貧戰(zhàn)略和扶貧目標(biāo),但是通過體制改革和經(jīng)濟(jì)增長實(shí)現(xiàn)了減貧的間接目標(biāo)(23),這是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初期實(shí)施的一種生存型反貧困政策(24)。其二,開發(fā)扶貧。國家通過專設(shè)扶貧資金和財政轉(zhuǎn)移支付,將財政資源集中投放到貧困人口聚集的偏遠(yuǎn)地區(qū),著力解決水、電、路等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滯后問題。農(nóng)村水利和電力建設(shè)改善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農(nóng)民生活條件,而農(nóng)村道路修筑既可以暢通物流,讓貧困地區(qū)的農(nóng)產(chǎn)品順利進(jìn)入市場,降低農(nóng)民交換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的交易成本,又可以促成農(nóng)村勞動力便利地進(jìn)入城市務(wù)工,實(shí)現(xiàn)非農(nóng)收入增加,促成農(nóng)民可行能力的提升。其三,精準(zhǔn)脫貧。經(jīng)過開發(fā)扶貧的持續(xù)投入,大量貧困人口相繼擺脫貧困,“撒胡椒面”式的扶貧資源配置成效邊際遞減,原先以貧困縣和貧困村為單元的籠統(tǒng)區(qū)域扶貧戰(zhàn)略難以覆蓋到真正的貧困戶。(25)新時代十年,我們堅持精準(zhǔn)扶貧、盡銳出戰(zhàn),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zhàn)。全面推進(jìn)鄉(xiāng)村振興,需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增強(qiáng)脫貧地區(qū)和脫貧群眾的內(nèi)生發(fā)展動力。(26)
全面脫貧是共同富裕的前期工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共同富裕的基礎(chǔ)工程。鄉(xiāng)村振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依托,它反映了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方式的系統(tǒng)轉(zhuǎn)變,體現(xiàn)了城市化向城鎮(zhèn)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shí)質(zhì)調(diào)整,旨在實(shí)現(xiàn)城鄉(xiāng)的均衡發(fā)展。這依然需要社會經(jīng)濟(jì)體制的相適調(diào)整,要進(jìn)一步深化農(nóng)村土地制度改革,發(fā)展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同時,要逐步廢除戶籍制度,順暢要素流動,促成要素競爭,均衡要素收益。
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能夠以基于公有制的社會保障實(shí)現(xiàn)基礎(chǔ)性社會公共產(chǎn)品的有效供給,創(chuàng)設(shè)生存資源的兜底配置,杜絕逐利資本無序擴(kuò)張對邊緣空間和原子化個體的剝奪和排斥。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生活的安全網(wǎng)和社會運(yùn)行的穩(wěn)定器,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治理需要公平性、覆蓋性和可續(xù)性兼具的社會保障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進(jìn)入新時代十年來,我們建成了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教育普及水平實(shí)現(xiàn)歷史性跨越,基本養(yǎng)老保險覆蓋10.4億人,基本醫(yī)療保險參保率穩(wěn)定在95%。(27)未來五年,我們要實(shí)現(xiàn)“居民收入增長和經(jīng)濟(jì)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健全”(28)。另外,對于特殊人群的權(quán)利貧困,黨的二十大也提出了明確要求,如“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guān)愛服務(wù)體系,促進(jìn)殘疾人事業(yè)全面發(fā)展”(29)。
國家資本對現(xiàn)代化角落生產(chǎn)和生活要素的持續(xù)輸血和合理賦值,需要通過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和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促進(jìn)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的構(gòu)建;同時,要堅持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優(yōu)先發(fā)展和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通過暢通城鄉(xiāng)要素流動和創(chuàng)設(shè)多種渠道來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xiāng)居民的財產(chǎn)性收入(30),實(shí)現(xiàn)由外在“輸血”到內(nèi)在“造血”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
(二)以最廣泛、最真實(shí)、最管用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shè)來盡可能創(chuàng)設(shè)機(jī)會平等和權(quán)利均衡
后發(fā)國家的現(xiàn)代化困境,原因當(dāng)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衰敗、無序黨爭和政府腐敗是根本原因。這表明,民主發(fā)展本身就是現(xiàn)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法被經(jīng)濟(jì)增長簡單替換。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治理離不開民主政治的頂層設(shè)計、強(qiáng)大政黨的有效領(lǐng)導(dǎo)和法治政府的廉潔有為。“政治自由和民主權(quán)利是發(fā)展的‘構(gòu)成部分,并不需要通過其對國民生產(chǎn)總值增長的貢獻(xiàn)這一渠道間接地建立它們與發(fā)展之間的聯(lián)系”(31)。同樣,現(xiàn)代化各項(xiàng)硬性指標(biāo)的“價值必須取決于它們對相關(guān)人的生活和自由產(chǎn)生什么影響,這是發(fā)展理念的核心”(32)。
當(dāng)然,腐敗問題既是弱勢群體權(quán)利貧困感知和生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又是導(dǎo)致社會保障制度難以合理創(chuàng)制和良性運(yùn)行的“頑疾”。“當(dāng)信息公開與條件明晰這兩項(xiàng)自由交易的必要條件被嚴(yán)重破壞時,很多人——交往的雙方以及其他人——的生活可能因?yàn)槿狈_性而受到損害”(33)。腐敗的盛行必然會消解政治信任,衍生合法性危機(jī),危害社會穩(wěn)定;同時,腐敗會扭曲經(jīng)濟(jì)激勵,導(dǎo)致發(fā)展乏力且亂象叢生。從某種意義上講,腐敗是對事后利潤的附加稅,尋租收益的遞增最終可能擠走生產(chǎn)性投資,抑制新產(chǎn)品和新技術(shù)的流動(34),遲滯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后發(fā)國家要消除腐敗就必須“有一個能夠減少政治俘獲和權(quán)力尋租活動機(jī)會的發(fā)展戰(zhàn)略……創(chuàng)造一個減少此類產(chǎn)生外部性活動的機(jī)會和相應(yīng)收益的政策環(huán)境”(35),這就需要用政治民主約定權(quán)力邊界,用全面法治糾正權(quán)力妄為。區(qū)別于后發(fā)國家對西方選舉民主的照抄和對腐敗盛行的容忍,中國式現(xiàn)代化依靠全過程人民民主來保障中國人民的政治權(quán)利和政治自由,并將反腐敗視為一場決不能輸?shù)闹卮笳味窢帯!案哒{(diào)且激進(jìn)的政治一般都是現(xiàn)代后發(fā)國家的政治主調(diào)”(36),“問題不僅在于從舊體制轉(zhuǎn)變到新體制之間的峽谷有多深多寬,還在于什么樣的政治勢力最有能力跨越它”(37)。中國式現(xiàn)代化當(dāng)然意味著新舊體制的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變,而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既是這種轉(zhuǎn)變的組織者和推動者,又是這種轉(zhuǎn)變?nèi)〉贸晒Φ年P(guān)鍵。
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基于原發(fā)民主元素,審慎借鑒外來民主理念和形式,注重提升人民的民主參與體驗(yàn)和實(shí)際的民主治理績效。它不是高調(diào)且激進(jìn)的,而是務(wù)實(shí)且漸進(jìn)的,既有頂層政治設(shè)計,又有中宏觀制度創(chuàng)設(shè),還有微觀運(yùn)行機(jī)制調(diào)適。與中國式現(xiàn)代化相伴而行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統(tǒng)合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建構(gòu)過程。另外,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shè)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當(dāng)然需要,它與全過程人民民主共同捍衛(wèi)中國人民的機(jī)會均等和權(quán)利均衡。這就需要在扎實(shí)推進(jìn)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同時,“全面推進(jìn)科學(xué)立法、嚴(yán)格執(zhí)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jìn)國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38)。同時,“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序”(39)。因此,需以完善的法治體系規(guī)范政府透明性建設(shè),以有效的政府制度安排打造社會保障安全網(wǎng),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提供政府信用支撐與防護(hù)性兜底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優(yōu)化政府職責(zé)體系和組織結(jié)構(gòu),推進(jìn)機(jī)構(gòu)、職能、權(quán)限、程序、責(zé)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40)。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要努力促成全能主義政府向有限法治政府的轉(zhuǎn)變,通過構(gòu)建公開透明、邊界清晰、分工合理和權(quán)責(zé)一致的政府職能體系實(shí)現(xiàn)政府的有為和高效。
四、結(jié)語
現(xiàn)代化是人類共同的事業(yè),但也是“一個創(chuàng)造與毀滅并舉的過程,它以人的錯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換來新的機(jī)會和新的前景”(41)。由資本邏輯驅(qū)動的西方式現(xiàn)代化無法以福利國家夢想的編織來真正化解貧富分化、社會對立和政治沖突,而后發(fā)國家對西方式現(xiàn)代化的附庸和西方政經(jīng)模式的照搬更會衍生現(xiàn)代化角落的權(quán)利貧困,帶來難以承受的現(xiàn)代化之痛。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以人本邏輯超越資本邏輯,通過國家資本實(shí)現(xiàn)對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空間和人群的權(quán)利賦予,并用全過程人民民主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建設(shè)盡可能創(chuàng)設(shè)全社會的機(jī)會均等和權(quán)利均衡,進(jìn)而真正消解了現(xiàn)代化角落權(quán)利貧困存續(xù)的內(nèi)外根由。中國式現(xiàn)代化實(shí)現(xiàn)了對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的全面超越,將為后發(fā)國家跳出現(xiàn)代化角落的窠臼貢獻(xiàn)中國智慧和中國樣本。
注釋:
(1)(2)(19)(20)(41) [美]C·E·布萊克:《現(xiàn)代化的動力》,段小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113—114、113、113、38頁。
(3)(6)(7) [印]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王宇、王文玉譯,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版,第55、4、205頁。
(4) [德]馬克斯·韋伯:《經(jīng)濟(jì)與社會》上卷,林榮遠(yuǎn)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657頁。
(5) [德]馬克斯·韋伯:《經(jīng)濟(jì)與社會》下卷,林榮遠(yuǎn)譯,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版,第729頁。
(8)(13)(14)(15)(16)(17)(33) [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fā)展》,任賾、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85、7、32—33、11、181、180、32頁。
(9)(10)(18)(31)(32) [印]阿馬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王磊、李航譯,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7、210—211、323、322頁。
(11) [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jì)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89—590頁。
(12) 宋朝龍:《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對后發(fā)國家現(xiàn)代化制度癥結(jié)的破解》,《科學(xué)社會主義》2020年第6期。
(21) 鄭功成:《共同富裕與社會保障的邏輯關(guān)系及福利中國建設(shè)實(shí)踐》,《社會保障評論》2022年第1期。
(22) 顧昕:《美國按揭型凱恩斯主義的前世今生》,《讀書》2018年第1期。
(23) 吳國寶:《改革開放40年中國農(nóng)村扶貧開發(fā)的成就及經(jīng)驗(yàn)》,《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
(24) 王春光:《社會治理視角下的農(nóng)村開發(fā)扶貧問題研究》,《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xué)報》2015年第3期。
(25) 袁明寶、余練:《精準(zhǔn)扶貧嵌入與全面脫貧的基層治理邏輯》,《開放時代》2021年第3期。
(26)(27)(28)(29)(30)(38)(40) 習(xí)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shè)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tuán)結(jié)奮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
(34) Romer Paul,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4, 43(1), pp.5-38.
(35) 林毅夫、[喀麥隆]塞勒斯汀·孟加:《戰(zhàn)勝命運(yùn)——跨越貧困陷阱,創(chuàng)造經(jīng)濟(jì)奇跡》,張彤曉、顧炎民、薛明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
(36) 任劍濤:《人權(quán)、共和與革命:潘恩思想與現(xiàn)代政治的調(diào)性》,《江蘇社會科學(xué)》2017年第6期。
(37) [美]亞當(dāng)·普沃斯基:《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jīng)濟(jì)改革》,包雅鈞、劉忠瑞、胡元梓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頁。
(39)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作者簡介:沈承誠,蘇州大學(xué)中國特色城鎮(zhèn)化研究中心研究員,蘇州大學(xué)新型城鎮(zhèn)化與社會治理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研究員,蘇州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江蘇蘇州,215123。
(責(zé)任編輯 劉龍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