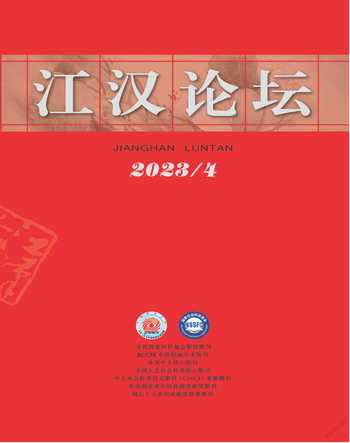論民事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之關聯
蔡虹 王璨璨
摘要:對于符合法定證據種類是否構成具備證據能力的必要條件,司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皆存在爭議。在解釋學進路下,無論是采文義解釋還是論理解釋,我國法定證據種類對證據能力都沒有直接限制作用。法定證據種類規則是對證據的不周延列舉,目的在于引領每一種證據的特定化證據能力規則。從學理觀之,法定化的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之間的關系具有間接性和附屬性,二者建立間接關聯的方式有:以證明程度(完全證明和疏明)為橋梁,以證明方法(嚴格證明和自由證明)為媒介,根據特定爭議類型或標的來限制證據種類的證明能力以及實體法中權利義務關系之形式要件延伸至訴訟領域的情形。
關鍵詞:民事法定證據;證據種類;證據能力;自由證明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請求權視角下民事訴訟與民法典問題對接研究”(19BFX082);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722023AK002)
中圖分類號:D92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3)04-0109-07
一、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了民事訴訟中法定的八種證據種類,有觀點認為只有能夠歸入這八種法定證據種類的證據才能具有證據能力。然而,由于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之間的直接關聯沒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規范依據,在司法實踐、理論研究和法律規范等三個層面產生了沖突: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對當事人舉出的無法歸入法定證據種類的證據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證據能力認定結果。例如,在2017年“鄭州大瑜園林工程有限公司、黃年合同糾紛”一案中,針對當事人之間存在爭議的刑事詢問筆錄之證據能力,人民法院認為“只要符合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特征,只要能證明案件的客觀事實,就應當作為證據使用。”(1) 而在2018年“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等與浙江物產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等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糾紛”中,最高人民法院以“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定的證據范疇”(2) 為由否定了當事人提供的材料之證據能力。在2021年“張耀權、廣東新會水務有限公司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中,對于當事人舉出的行政賠償裁定,人民法院亦以“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的民事訴訟證據類型”作為不認可其證據效力的原因之一。(3) 在理論研究層面,學者們對非法定種類是否構成證據能力直接排除事由的觀點亦有分歧。第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屬于法定種類的民事證據才能具有證據能力。原因在于“限制證據能力、排除不屬于法定證據種類的證據材料,一直被認為是我國證據分類制度的法律功能”(4) 。在研究證據能力學術著作里,有學者曾指出當時教科書中常見觀點是只有符合法定種類的證據才具有合法性,才能被采納。(5) 另一方面,亦有觀點對“不屬于法定證據種類是排除證據能力的原因”持否定態度,認為“證據種類應當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法律關于證據種類的規定,應該視為對主要證據的列舉。”(6) 在法律規范層面,實體法和程序法在法定證據種類和證據能力的關系上也產生了齟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中存在著被實體法明定為裁判依據,而程序法規定的證據種類卻無法涵蓋的事項。例如,《民法典》第1254條規定公安調查高空拋(墜)物案件,而在這類民事侵權責任糾紛中,公安機關往往出具的詢問筆錄和認定意見等不屬于我國法定證據種類的證據。
證據是當事人攻擊防御的武器,證據采納攸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差異對待不屬于法定種類之民事證據易于導致個案中的裁判突襲和不公,不利于統一法律適用和維護司法權威,也對訴訟中的程序保障和發現真實帶來隱患。因此,本文將從上述爭議出發,探討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之關聯。
二、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非直接關聯的文義解釋
從法條文義本身而言,《民事訴訟法》第66條不能成為直接排除無法歸入法定種類的民事證據的依據。原因在于:首先,該條文在引入法定證據種類時,采用的措辭是“證據包括”。這一遣詞方式說明法條中的證據之集合和民事訴訟中的證據總集是后者包含前者的關系,而不是同一關系。其次,該條文列舉的八種證據,在外延上不能通過包容性解釋來覆蓋民事訴訟中出現的所有證據。條文中列舉的八種證據,在內涵和外延上爭議較多的是書證和證人證言。實踐中在面臨無法歸入法定種類的證據時,可能會選擇采用“大書證”或寬泛人證的概念將其籠統納入其中,從而規避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關系問題。但是,我國民事訴訟規范中的書證和證人證言皆為狹義,且無法做包容性解釋。
其一,與域外泛化的書證概念不同,我國民事法定證據種類中的書證強調的是案件事實發生過程中所形成的以其內容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即與案件事實具有同步性的書證。相對于案件“元事實”而言具有“事后性”的書面證據材料不屬于書證。(7) 因此,在進入訴訟之后,案件調查審理過程中形成的書面形式的材料不能歸入書證。我國民事訴訟中的書證不能采包容性解釋。雖然有學者曾指出“我國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本身具有解釋上的包容性”,(8) 但是,如果認可這種擴大解釋,就會將我國法定證據種類體系推入邏輯謬誤中。書證的“包容性解釋”意指采取開放式的廣義解釋,其含義范圍類似于英美法系國家所采取的廣義。英美法中的書證(documentary evidence)釋義為“以書面文件為表現形式的證據”。(9) 英美法系對證據采用的寬泛概念,在其證據制度中是能夠自洽的。英美法中的書證“包括了中國歸屬于其他證據種類的視聽資料和勘驗、檢查筆錄,以及中國法律規定中所不能包括的其他具有證明作用的書面材料”。(10) 反觀我國,從《民事訴訟法》第66條自身的邏輯觀之,如果將書證概念解釋與英美法系中的書證一致,這一條文就無法在邏輯上成立。該條項下規定的勘驗筆錄也是書面形式的證據,這一證據何以同“書面形式的證據”成為并列關系?由此可見,我國民事訴訟規范中的書證除了形式要件之外,還在生成機制上有所限定,為狹義上與案件事實具有同步性的書證。
其二,我國法定證據種類中的證人證言亦是狹義上的證人證言,要求證人具有親歷性。因為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19〕19號,以下簡稱《民事證據規定》)第72條規定的“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作證時不得使用猜測、推斷或評論性語言”可推知,我國在證人資格上限定為對案件事實親身感知的主體。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法條釋義中指出“有專門知識的人”與英美法系中的專家證人在功能和訴訟地位上存在顯著差別,不承擔輔助法庭事實發現的功能,不能歸入證人范疇。(11) 與英美法上寬泛的證人概念不同,德國民事訴訟規范中區分證人和鑒定人兩種證據手段,鑒定不屬于人證的范疇,而是屬于與人證并列的依法規定的證據種類。(12) 在這一點上,我國法上的證人內涵上更接近于德國法。我國鑒定意見雖然要求具有書面形式,但在庭審中也要求鑒定人接受當事人的發問,作出口頭的闡明與解釋,復合了言詞形式。故而鑒定意見也難以和廣義的證人證言并列。如果對證人證言采取寬泛解釋,會導致我國民事證據規范中概念用語的一貫性缺失以及規則之間的沖突,因為證人證言的采納和采信規則是基于狹義證人證言展開的。
三、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非直接關聯的論理解釋
前文從條文文義論證了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非直接關聯。然而,法定證據種類規則并不是恒定的、孤立的,而是不斷發展,并內嵌于宏觀證據制度中,且與其他的一些證據規則相互牽連。下文將從現行條文回溯至立法沿革,從微觀規則流轉至宏觀體系,進一步觀察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關聯。
(一)法意解釋:從限定到列舉的功能沿革
立法沿革是法意解釋的主要依據。我國法定證據種類規則在立法變遷中已經呈現出從“限定證據種類”到“列舉證據種類”的功能轉型。結合法條的嬗變經歷,可以作以下分析:
第一,法條中引入證據種類列舉的導語由“證據有下列幾種”變為“證據包括”,代表立法者認可了下列八種證據并不能涵蓋所有的民事訴訟證據,態度轉向“包括但不限于”。故而將證據和法定種類之證據的關系由同一關系變為了包含關系。2012年《民事訴訟法》修改表明了法定證據種類之條文只是對典型證據的列舉,不能囊括或限定訴訟中能夠被采納的證據。
第二,電子數據這一法定證據種類的新增實際上說明了實定法證據種類列舉的前瞻性缺失,間接體現了直接排除非法定種類之證據是不合理的。在這一法條的前綴修改之前,有學者曾指出證據種類劃分的邏輯標準應該科學合理且具有明確性、恒定性,且“作為某一特定的訴訟證據分類序列在概括功能上必須窮盡所有的證據形式。”(13) 然而,要追求窮盡和恒定,僅憑明確的列舉十分困難。因為人的認識是有限的,總是受制于當下的物質條件。由于立法的滯后性,會存在某些有助于發現真實的新型證據已然穩定可靠但還處于未能上升為法定種類的遲滯期。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因為這類證據不屬于法定種類而武斷地將其排除,不僅不利于司法證明的效率和效果,也無益于保障事實認定之公正及當事人之程序參與。
第三,從“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演變為“證據必須查證屬實”,可以推測立法者意識到了“以上證據”不能等同于所有證據。并且認為即使是不屬于“以上證據”的證據,也可以且必須經歷查證屬實的證據能力判斷程序。
(二)目的解釋:順應訴訟真實觀之轉型
在民事證據和證明的環節中,發現真實是其最核心、最直接的目的。無論是證據能力規則還是法定證據種類規則,都服膺于這一目的。
發現真實的具體尺度無法脫離宏觀訴訟制度的真實觀,亦即宏觀證明標準。關于宏觀證明標準,存在客觀真實(又稱實質真實)、法律真實(又稱形式真實)等不同的觀點。法律真實指“在訴訟證明的過程中,運用證據對案件真實的認定應當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應當達到從法律角度認為是真實的程度”。(14) 在法律真實觀下,民事訴訟建立起證據失權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規則。從這一層面看,似乎法律真實為證據能力設置了更高的標準。但在法定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雙重視角下,法律真實觀對不屬于法定證據種類之證據的態度比客觀真實觀更為寬容。
一些非法定種類之證據,在客觀真實觀之下被認為不具有證據能力,但在法律真實的司法證明標準之下可以作為法官認定事實的依據。在刑事證據領域,在不要求事實認定達到客觀真實標準的國家中,某些對于待證事實具有推測性證明價值,能夠為待證事實提供可能性判斷的證據材料(例如偵查實驗)可以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但對于當時采客觀真實之證明標準的中國而言,這些證據因為與待證事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不具有合法的證據地位。(15) 這類證據不僅出現在刑事訴訟中,也有可能在民事訴訟中出現。
法律真實觀對非法定種類之證據的寬容態度源于調整了關聯性標準。在客觀真實觀下,證據事實和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一般表現為因果關系。證據事實的存在可以是待證事實可能存在或實際存在的唯一原因,也可以與其他事實結合,成為待證事實的一簇原因中的一部分。而在法律真實觀下,證據的關聯性要求不一定是因果關系(或者說生成意義上的關系)。雖然在證明力評價的階段,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會影響法官對證據價值的評價。但至少在證據采納階段,某些非法定種類之證據即使與待證事實沒有因果關系,但是與待證事實發生的可能性有所關聯,就可以作為證據給法官提供線索。
法定證據種類規則服務于發現真實的目標,那么這一條文的目的解釋應當隨著發現真實的尺度標準的變遷而有所調整。我國曾在蘇聯民事訴訟理論的影響下強調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任務是發現客觀真實。(16) 但是“隨著程序法治建設的推進,國家權力‘大一統的觀念已經不斷瓦解,審案裁判者的獨立性正日益得到重視;‘客觀真實這種證明標準一般適用性/實用性已經在學理上受到了極大的消解。”(17) 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國民事訴訟“事實認定的宏觀標準從客觀真實轉向法律真實,已經和當初沿襲蘇聯法的訴訟運營體制分道揚鑣。”(18) 在法律真實觀的指引下為非法定種類之民事證據保留制度空間,亦能拓寬裁判資料收集的路徑,推動發現真實。
在發現真實的目的之下,對證據規則的解釋還必須符合認識論規律。“從認識論的邏輯來說,某一當前事實是否具有證據的資格,并不由證據種類的區分決定,而是看其對證明對象是否具有認識論上的證明能力。”(19) 證據是我們認識事實的手段。靈活且具有彈性的證據種類能拓寬法官發現真實的渠道,比封閉僵化的規則更能接近發現真實之目的。
(三)體系解釋:與關聯條款的意旨之辨
因為證據種類與證據形式的密切關聯,故而涉及“證據形式符合法律規定”等表述的條款可視為與《民事訴訟法》第66條的關聯條款。另外,第66條中亦包含“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之表述,而我國現行民事訴訟和民事證據中不乏其他包含這一表述的條文。
1.與“形式符合法律規定”條款之辨析
通過對“形式符合法律規定”之條款的法意探索,可以觀察到我國現行規定中對證據形式的合法性要求,實際上是對具體證據種類提出的載體要求或格式要件,并不是歸納意義上的形式和種類要求。
在我國現行規范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22〕11號,以下簡稱“民訴法解釋”)第99條提及證據形式上的瑕疵補正;第104條亦提及證據的“形式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采用“證據的形式”之表述的法律條文還存在于“民事證據規定”中,這一司法解釋有四個條文運用了“形式”一詞,分別是第14條、第51條、第87條和第92條。這四個條文論及的證據形式,除了第87條中的“形式”意涵較為模糊之外,其他法條中的“形式”都是對具體證據的載體要求和格式要件。
從上述法條觀之,我國現行法中所指的證據形式更大程度上是針對具體證據提出的格式要求或是載體要件,與學理中歸納意義上的證據形式有所不同。歸納意義上的證據形式是從整體上對某一類證據共有的屬性進行整理,而證據的格式要求是針對已經被呈現出來的單一的、特定的證據。這一觀點的佐證還有:我國民事證據立法中的“證據的形式”存在瑕疵補正的規定,如果是歸納意義上的證據形式,就不存在瑕疵補正的問題。從反面推知,形式不合法的證據指的是未滿足法定載體或格式要求的證據,與不屬于法定種類之證據不在同一個判斷層面。我國立法往往是針對某一法定證據種類提出“證據的形式”的要求,判斷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證據種類歸屬之后的問題。
2.與“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條款之關聯
從我國民事訴訟和民事證據規范中涉及“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條款的條文觀之,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關聯在于“每一種證據都有相應的證據能力的要求”(20) ,而不是以法定種類直接拘束證據能力。在我國現行民事證據規范中,能夠與證據能力建立聯系的主要立法表述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具體表現為從法定消極排除角度作出的“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以及從積極要件角度作出的“應當/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還有提示法官裁量的“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根據現行民事訴訟規范中包含“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條款的條文,我國民事訴訟規范和證據規范中對證據能力的規定呈現出以下特征:
其一,證據能力排除規則主要是對某一具體種類之證據的具體形式要件作出要求,并沒有涉及對證據種類的直接要求。以消極排除的方式限制證據能力的規定,除了“民訴法解釋”第106條與第103條是對整體證據作出的共通性要求外,其他條文都是針對具體的某一種證據(例如針對證人證言)作出的要件規定。且第106條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103條屬于證據能力的程序性要件,皆屬于無關乎證據種類的規則。可見,證據種類的區分只是為證據能力規則的特定化、系統化提供邏輯支持,因為不同證據種類在證據運用和判斷上有不同的要求,需要針對不同的證據種類設置不同的證據能力規則,(21) 而不是直接根據證據種類來判斷證據能力。
其二,證據能力的積極要件規則亦不涉及對證據屬于法定種類的要求。具言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的“證據必須查證屬實”這一要件與證據的種類歸屬無關。關于“民訴法解釋”第104條,在“形式符合法律規定”之條款的辨析中已經厘清了它無礙于非法定證據種類的合法性。同樣從積極要件角度規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的《民事訴訟法》第72條亦是從具體的證據作出的,不涉及非法定種類之民事證據的證據能力有無。
其三,在提示或授權法官裁量證據能力的條款中,亦是針對某一特定證據種類的審查。并未提示法官關注證據是否符合法定種類,更沒有授權法官直接排除非法定種類之民事證據。另外,列舉法定證據種類對司法裁判的意義既不在于排除非法定種類之證據的證據能力,也不在于強化法定種類之證據的證據能力,而是一種識別與索引的作用。立法通過把實踐中常見證據的稱謂術語化、標準化,從而引導法官在定位證據的基礎上準確識別這類證據相應的預設證據規則。
四、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之間接關聯的學理審思
從學理上觀之,原則上是否屬于法定證據種類不構成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原因。但因為二者皆與訴訟證明中的一些其他因素有關。在某些情形下,這些因素作為介質導致二者表現出了因果關聯。證據種類與有無證據能力之間的關聯必須要在具體情形中經由特定的介質才能成立,不能將這種關聯直接化,常態化。
(一)以證明程度為介質:完全證明與疏明
在大陸法系證明理論中,按照法官的確信程度,證明可分為完全證明和疏明(我國臺灣地區采用“釋明”之表述)。完全證明指“法院對待證事實的真實性形成了確信。”(22) 而疏明指“通過證據等予以印證,雖未達到證明的程度,但可以使法官作出大致確定之推定的狀態”。(23) 疏明在是否接近客觀真實上有一定的或然性。在大陸法系的證明理論中,適用疏明的事項一般限于訴訟之先決問題及附隨程序性事項。(24) 例如在日本民事訴訟中的假扣押、假處分事項的權利存在和必要性;德國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申請法官回避之事由的證明等。
事項的證明程度會影響證據種類的允許和證據能力的判斷。例如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規定,“釋明事實上之主張者,得用可使法院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但依證據之性質不能即時調查者,不在此限。”這一規定在法理上稱為“疏明方法的即時性”(25) ,即用于疏明的證據雖然不以法定的證據方法為限,但僅限于法院能即時調查的證據。在大陸法系證據法學理論中,即時調查的證據方法與依特別手續調查之證據方法相對,指得與本案同時為之而無需依特別手續為之的證據方法。(26) 規定“疏明方法的即時性”的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在不屬于案件核心爭點的事項中耗費過多的時間,力求迅速決斷以避免程序遲滯。因此,在疏明制度下,一些證據種類會因為不符合證據方法的即時性而被直接排除證據能力。但不能認為喪失證據能力的直接原因在于證據種類,二者只是在特定的程序性事項中,經由證明程度的橋梁而建立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疏明方法的即時性”是從大陸法系理論和制度的視角展開的。從本土視角而言,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以證明程度為介質的間接關聯暫時不存在于我國民事證據領域。我國“民事證據規定”第86條規定了“與訴訟保全、回避等程序性事項有關的事實,人民法院結合當事人的說明及相關證據,認為有關事實存在的可能性較大的,可以認定該事實存在。”從這一條文可見,我國立法雖然存在降低證明程度要求的條款,但該條文僅設定了通常證明標準之例外,沒有為了訴訟程序的推進效率而進一步對證據作出限制。相較于域外理論和規則建構中的疏明,這一條文并沒有體現出對證據種類和證據能力的影響。
(二)以證明方法為介質: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
大陸法系證明理論將證明方法區分為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證明方法能夠成為證據種類和證據能力建立關聯的介質。德國訴訟法學理論“將依法律所定之證據方法踐行法定證據調查程序而為之證明稱之為嚴格證明。”(27) 自由證明與嚴格證明相對立,目的在于靈活地解明事案,緩和嚴格證明的非靈活性。(28) 自由證明在證據方法及證據調查程序上皆不受法律拘束,不必嚴格遵循相應的證據調查程序。(29) 自由證明不同于前文討論證明程度時論及的疏明。雖然二者都旨在提升證明程序的效率與靈活性,且關系密切(自由證明在德國訴訟法領域的創立伊始就是為了填補嚴格證明和疏明之間的空隙),但自由證明僅在證據方法與證據調查程序上與嚴格證明存在差異,在證明程度上仍屬于完全的證明,需要達到完全確信或高度蓋然性的證明程度。(30) 另外,疏明基于即時性要求限制使用某些證據,而自由證明沒有在這一意義上聯結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
證明方法與證據能力和證據種類皆有關聯,并影響著非法定種類之證據的證據能力。對于證據能力而言,嚴格證明與其緊密相關。在德國法上,只有用于證明嚴格證明事項的證據,才需要考察其證據能力,甚至可以將證據能力定義為“指具有可為嚴格證明系爭的實體法事實之資料的能力”(31) 。自由證明情形下可以運用的證明手段和證據方法更為廣泛,除了法定的證據種類外,“只要有助于待證事實之澄清,一切認知手段均可資法官利用”。(32) 在自由證明中,法官對于非法定之證據種類的適用享有自由裁量權并且可以依職權主動利用。在德國法上,官方答復是自由證明常見的證據手段之一。雖然官方答復在德國民事訴訟法學理論是屬于自由證明的證據手段還是嚴格證明的證據手段存在爭議,但從實定法的角度而言,官方答復確實不屬于德國法中的法定證據種類。(33)
從上文可見,證明程度和證明方法都可以作為法定證據種類和有無證明能力建立間接關聯的橋梁。這兩種間接關聯既有區別亦有一定的通性。通性之一在于自由證明與疏明都不以法定的證據種類為限。通性之二在于兩種間接關聯都是來自大陸法系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理論及立法,但在我國民事證據領域未有體現。我國當前民事訴訟規范中雖然存在與疏明制度類似的條款,但沒有在證據使用上作出限制。而對于自由證明而言,雖然我國有學者指出“非法定的證據方法僅在自由證明之場合方可采用,此即證據法定之意義所在。”(34) 但我國當前立法中沒有建立起嚴格證明、自由證明相關的理論、概念或條款。
(三)以案件類型為介質:爭議及標的額
非法定證據種類的采納在域外民事訴訟中還可能與爭議類型或訴訟標的額有關。證據能力和證據種類以爭議類型或標的額為介質建立關聯的模式有三種:其一為在某些特定爭議中僅能使用特定的證據種類;其二為在特定爭議中排除某些證據種類的證據能力;其三為在某些特定爭議中授權使用法定種類之外的證據。
在第一種模式中,因為立法限制了證據種類,那么除特定的證據之外,無論是其他法定種類的證據還是非法定種類的證據,都不能具有證據能力。例如,日本民事訴訟法中存在“票據及支票訴訟或者小額訴訟中的證據方法限制”。(35) 第二種模式在域外立法中一般體現為根據標的額限制人證的證據能力。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721條規定的“契約證人的舉證,其標的物的價值超過五千里拉時不予承認”(36) 。在第三種模式中,立法明確賦予某些非法定種類之證據在特定爭議中的證據能力。例如,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于第421條規定了個體勞動爭議中法官可以突破常規的證據調查手段:“法官可以在訴訟的任何時候要求采納除了決定性誓言外的任何一項證據,即使該證據超出了《民法典》的有關規定;并可向當事人指定的工會要求提供書面或口頭的信息和意見。”(37)該法條中還進一步規定了為了確認案件事實,法官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進入工作場所,“并在其認為有助于確認事實時,詢問工作場所中的證人”。(38)
在特定爭議類型中或者根據爭議標的額來規定證據種類的證明能力之立法方式在我國當前民事證據領域暫未存在。雖然我國亦專門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但僅在證據的程序簡化方面與普通程序有所區別,不涉及證據種類和證據能力的限制。
(四)以證明對象為介質:實體要式的程序延伸
在域外民事證據理論和經驗中,還存在根據證明對象的性質不同來限制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種類。例如,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41條將證明對象區分為法律行為和法律事實,當證明對象是單純的事實時,法律中準許的所有類型的證據方法都有證明能力,尤其是能夠以證人證明之,但如果是有關法律行為,則建立了“要求有書證”原則。(39) 但是,這一原則在司法中的適用要受到當事人意志的制約。法國民事訴訟規范認可證據規則的私法性質,當事人可以主張免除“要求有書證”原則的限制,也可以以默示的方式接受證人證言的證據資格,并且當事人之間“有關證據方式的協議”被認為具有合法性。(40) 這些表達當事人意志的方式都能夠突破“要求有書證”原則。在日本民事訴訟法中,亦存在以具體的證明對象為橋梁聯結證據種類與證據能力的特殊情形,例如代理權的書面說明。(41)
針對證明對象的性質通過證據種類限制證據能力的規定不僅存在于域外,中國古代法制亦有先例。成書于南宋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云:“大凡官廳財物勾加之訟,考察虛實,則憑文書(《清明集》卷九《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清明集》卷五《物業垂盡賣人故作交加》)”。明代規定民間的民事法律活動都須要保留憑證,尤其是書證。(42) 例如要求男女訂立婚約必須要有婚書,婚書上必須要寫明各種可能發生糾紛的因素,以便于糾紛發生時有據可查。(43) ?上述訴訟判詞、律例等都屬于針對具體證明對象以限制證據種類,將實體領域形成的形式、內容完備的各種契約文書,明定為訴訟領域的斷結依據。
在訴訟中針對特定的證明對象限制證據種類的規定,亦可以理解為實體法中權利義務關系形成之要式約束力在訴訟領域的延伸。故而這一方式往往體現于合同糾紛,尤其是要式合同糾紛中。上文列舉的法國與中國古代宋、清時期的規定體現了立法認為法定的合同形式才能作為證據來證明法律關系的存在——例如如果實體法中要求某種債權債務關系的成立必須采書面形式,那么在訴訟中僅能以書面契約這一書證作為證據證明債權的存在,他種證據則被認為沒有證據能力。
就我國民事規范而言,雖然我國民事實體法中大量存在要式法律行為的規定,例如《民法典》第33條規定的意定監護、第348條規定的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等,都要求當事人以書面形式確定意向或訂立合同。但我國民事程序法則對此未有銜接,沒有從證據法的角度規定證明要式合同的證據也必須符合要式,更沒有明文否定他種證據在證明要式合同時的證據能力。有學者認為,就我國有關法律規定而言,“任何合同的形式,無論口頭還是書面,其作為當事人合意得以外界化的媒質都具有程序法上的證據效力。”(44) 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尤其是在當事人對合同的成立、生效沒有異議,只是對具體約定內容有所爭議;抑或是被主張債權的一方當事人沒有否認債權存在,而只是展開抗辯的情形中,不能直接從實體法的要式規定推出證據法的資格規定。從域外經驗來看,雖然法國民事證據領域針對法律行為的證明確立了限用書證的原則,但同時規定了當事人意志優先于這一規定。可見,法國民事司法程序中既沿襲了實體法的要式規則,也旗幟鮮明地順應了私法領域的自治精神。故而實體法規定的要式延伸于證據法的方式在該國民事領域是邏輯自洽、一以貫之的。但我國民事程序法并沒有肯定當事人意志在司法證據領域的優位性。如果我國在要式合同的證明中限用書證,有程序法選擇地沿襲實體法之嫌。
注釋:
(1) 鄭州大瑜園林工程有限公司、黃年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豫07民終1462 號。
(2) 天津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等與浙江物產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等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27號民事判決書。
(3) 張耀權、廣東新會水務有限公司等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民事二審民事判決書,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粵07民終7587號民事判決書。
(4)(8)(21) 林勁松:《我國證據分類制度的功能反思——以刑事訴訟為中心的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5) 參見紀格非:《證據能力論——以民事訴訟為視角的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
(6)(20) 張衛平:《民事證據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7頁。
(7) 參見張衛平:《論訊問、詢問筆錄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效力》,《清華法學》2011年第1期。
(9)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頁。
(10)(15)(17)(19) 周洪波:《訴訟證據種類的區分邏輯》,《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編:《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728—729頁。
(12) 雖然德國《民事訴訟法典》“鑒定”一節的規定(總第402條)規定“對于通過鑒定人進行證明,準用有關通過證人進行證明的規定,但以下各條另有規定的除外。”但這一規定僅為證明規則上的參照使用,不構成將鑒定人等同于或擬制于證人。參見趙秀舉譯:《德國民事訴訟法典》,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頁。
(13) 張嘉軍,張紅戰:《我國證據種類的反思與重構》,《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14) 紀格非:《民事訴訟中的真實——路徑與限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頁。
(16) 參見李浩:《蘇聯民事訴訟理論與立法對中國的影響》,《東南法學》2019年第2期。
(18) 段文波:《預決力批判與事實性證明效展開:已決事實效力論》,《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22)(33) [德]羅森貝克、施瓦布、戈特瓦爾德:《德國民事訴訟法》,李大雪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版,第814、923—924頁。
(23)(35)(41)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林劍鋒譯,第386、373、387頁。
(24)(25) 占善剛:《降低程序事實證明標準的制度邏輯與中國路徑》,《比較法研究》2021年第6期。
(26) 參見[日]松岡義正:《民事證據論》,張知本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27)(29)(30)(32) 占善剛:《論民事訴訟中之自由證明》,《法學評論》2007年第4期。
(28) 自由證明的適用對象一般限于訴訟要件事實、外國法、特殊經驗法則等非本案判決事項上。與疏明的適用對象相比,“自由證明之事項雖非訴訟的直接審理對象卻也為本案判決形成不可或缺之基礎事項”。
(31) 肖建國:《證據能力比較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6期。
(34) 占善剛:《證據法定與法定證據——兼對我國〈民訴法〉第63條之檢討》,《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36) 《意大利民法典》,陳國柱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82頁。
(37) 指意大利《民法典》第2721—2726、2729、2735條。意大利《民法典》第2721—2726條是關于人證的規定,第2729是關于事實推定、第2735條規定的是裁判外的自白。
(38) 《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白綸、李一嫻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頁。
(39)(40) 《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附判例解釋)》上冊,羅結珍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295、292—293頁。
(42)(43) 參見張晉藩:《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巴蜀書社1999年版,第154、154頁。
(44) 溫向麗、尹偉民:《合同要式性對證據方法的影響》,《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作者簡介:蔡虹,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3;王璨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3。
(責任編輯 李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