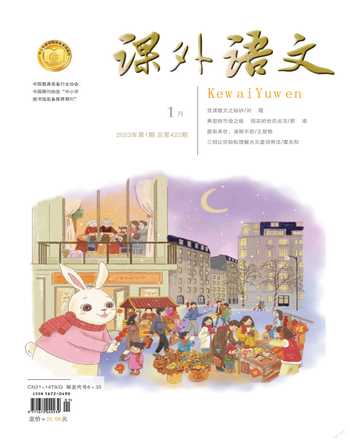真情實意,心音共鳴
徐嬋美


作文經常強調【言為心聲】【披文入情】,意在說明在寫作時要表達真情實感,不說假話、空話、套話,避免為文造情。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同學寫作時無病呻吟、矯揉造作、重復啰嗦,而且比比皆是。立足新時代,我們先來看看作文的要求,再來談談寫真情實意作文的重要性。
【寫作要有真情實感,力求表達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感受、體驗和思考;要多角度觀察生活,發現生活的豐富多彩,能抓住事物的特征,有自己的感受和認識,表達力求有創意。】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寫作不單單要立意明確,中心突出,選材得當,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真切感受。這種真切的感受是發自內心的,不矯揉造作的,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的文章感動人、吸引人,達到寫作人與讀者心音共鳴的目的。既如此,就要求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
一、要寫真——真人、真事、真感受
我們每天的生活都是真實存在的,何必虛構說空話呢?
第一,寫自己身邊的真人。每當談到寫身邊的人,總有同學“汗顏”,因為在很多同學的頭腦里,認為身邊的人沒有值得寫的地方。其實,這是觀察的失當與失誤使得寫作者沒有能夠抓住人物的品質這個關鍵點造成的。比如,一個同學在作文《我的媽媽》中這樣寫他的媽媽:“媽媽對我很嚴格,每當我寫作業時忘記了放好筆,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跟我講一定要有條理地做好自己的事情。當我做完作業,她還會監督我收拾好桌子上的文具,哪怕一塊橡皮都要放到本該屬于它的地方。她不但對我這樣,她也這樣要求自己,廚房的工具一一擺放整齊;醬醋油鹽的瓶子總有屬于它們的地兒。”簡短的一段文字就把媽媽那種有條理、一絲不茍的生活態度寫了出來,活靈活現的。那么,同學們,大家看看,這樣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是隨處可見?
第二,寫自己身邊的真事。很多同學總是認為沒有素材可寫,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兩篇文章。比如一個父親送自己的兒子出門,可以寫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為兒子搬行李、為兒子買票、為兒子叫車……而我們看看部編版《語文》八年級上冊朱自清的《背影》,在這篇文章里,朱自清專門挑選了父親為自己買橘子這件事情來寫。這是不是很平常的事情?沒有矯揉造作,沒有添油加醋。又比如,在部編版《語文》七年級上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寫的關于孩子們不上課溜出去玩又被老師喊回來的場景,難道跟我們的生活不像嗎?有人認為,魯迅和朱自清都是大師,我們不能與他們相比。他們是大師,固然沒錯。但是,他們所寫的買橘子、孩子貪玩都是身邊的真事,而且寫得情真意切。
第三,寫自己的真感受。要說真感受,這個可模糊不得。有句話說得好:“我們能夠欺騙別人,但是不能欺騙自己。”說的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對于世間萬物都有自己的真實感受。當然,大師也不例外,同樣是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墻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這一段描寫兼具了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的感官描寫。這難道不是我們真實的感受嗎?真實的感受,就是文章的靈魂。
二、要寫細——從小處著眼,從小處寄情
偉大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說:“藝術起于至微。”所謂“至微”,就是在我們的文章中要有顯示人情美、人性美的細節。要讓自己的作文感人,秘訣就是“從小處著眼,從小處寄情”,用細節展現生活的美,用細節書寫生活的真。前文我們提及朱自清的《背影》,里面談到一件真人真事—父親為兒子買橘子。這個寫作的素材已經被研究得很透徹了,這里我們不妨“舊事重提”:從父親的衣著看—“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寫出了父親的樸素;從父親的動作看—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寫出了父親行動的艱難,但為兒子付出又覺得無怨無悔;從父親買橘子回來的動作看—“撲撲衣上的泥土”,輕描淡寫,卻體現了父親完成一件重要工作似的輕松。作者就是從父親買橘子這個“小處”著眼,精心描畫了一個讓我們感動不已的、可愛可親的、疼愛兒子的父親形象,正是這些細節讓情感真情流露。另外,我們不但要善于“從小處著眼”,還要善于“從小處寄情”,在作文的某個時刻該抒發自己的感情就一定要將自己的感情宣泄出來,這樣的文章才能飽含深情。如一位同學在《美麗鄉村》中這樣來抒發自己的感情:“屋子背后的那塊草地遍地都是青綠的葉,柵欄上都是彎曲的藤,給整個園地鑲上了沒有雕琢過的天然花邊。這樣的裝飾比大城市高樓門前的石獅子來得親切和質樸。家的對面,是一條悠長的小河,陽光下,一陣微風掠過,水面上泛起層層漣漪,波光粼粼,讓人陶醉。鄉村、田園、農家風光,這一切都是一道獨特的、迷人的風景。”這一段真情表白寫出了小作者對美麗故鄉的無限熱愛,讓我們也感同身受,仿佛一幅自然的、和諧的田園風景圖躍然于眼前。通過這兩個示例,誰還說“言情”表白自己是一件難事?只要肯用心寫。
三、要寫實——語言要平實,描寫要務實
我們的作文是用語言文字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沒有必要追求華麗的辭藻,那么就要求我們的作文要“接地氣”。何為“接地氣”呢?就是樸實無華,在一種淳樸自然的描述中流露出真摯的感情。首先,在語言方面,要做到平實。就拿平時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來說,生活中的對話無非就是那么幾句,還需要什么華麗的辭藻嗎?我們一起來看看一位同學寫的《缺少一點勇氣》,作文這樣寫母女之間的對話:
“妹子,為什么這么晚了還沒有睡覺?在想什么問題啊?”媽媽說。
“不想什么?就是擔心明天的校運會,我怕掉鏈子,怕辜負了老師和同學的期望。”我說。
“怕也要睡覺啊。但是,你不妨這樣想,只要我順利沖過了終點,其間沒有跌倒、其間我盡力就行了。難道你害怕跑不完?”媽媽笑著說。
“怎么會跑不完呢?不管怎樣,我也要跑下去。”我反而被媽媽說服了。
就這一段對話,有的同學可能說,平淡無奇,算不得“美文、美段”。但筆者想說,這就是我們生活本來的樣子,難道普通的對話也要用大道理、用華麗的修辭嗎?其實沒必要,最樸實的就是最真實的,這才是生活的本質。
其次,描寫要務實。這里,我們不妨重讀一下部編版《語文》七年級上冊莫懷戚的《散步》中的一段描寫:“這南方的初春的田野!大塊兒小塊兒的新綠隨意地鋪著,有的濃,有的淡;樹枝上的嫩芽兒也密了;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著水泡兒……這一切都使人想著一樣東西—生命。”這一段描寫,不也是樸實自然嗎?恰如其分地寫出了春天的秀麗和自然,還有那種與生俱來的春的氣息、春的情景,結合一家三代人的出行場景,更顯得溫馨和幸福,描寫得云淡風輕,細讀起來卻耐人尋味。
當然,寫作畢竟有藝術的成分。但這個藝術加工是建立在生活真實面貌的基礎上,離開真實生活這個土壤,任何的描述都是站不住腳的,也不會引起讀者的共鳴。
古往今來,先賢們對于寫作說假話、說套話也是深惡痛絕的。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中,提出“疾虛妄”,倡導真實,要求一切著作和文章的內容必須是真實的,他極力反對那些無聊的、虛假荒誕的“虛妄之文”,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講也是非常必要的;魏晉時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強調的是文章要表達出心志,更要做到感情真摯和文辭美好,這就是所謂“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的真諦,具體而形象地說明了情感在文章中的重要地位。當下,我們也應該寫自己的真情,這是我們做人求真、求學務實的體現。讓我們拿起手中的筆去記錄真實的生活,回歸真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