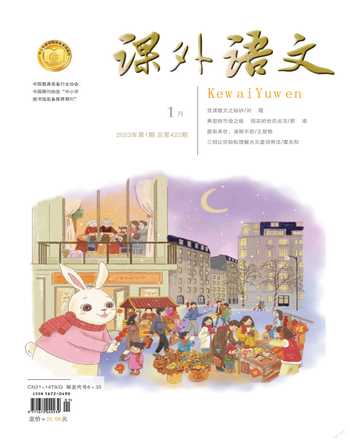盛世繁華,孤城淚光
方友法


唐詩被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瑰麗寶藏,在持續一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文學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唐時期衍生了長短句的文學形式,這種文學形式有著民歌的藝術特點,詞風樸素自然,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到了南唐的李煜,開拓了新的深沉的藝術境界,這種新的文學形式就叫作“詞”。進入宋朝,詞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成為一種完全獨立并與唐詩相抗衡的文學形式。宋詞所蘊含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遠比唐詩更為濃厚,更為獨特的是,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的詩風有所區別,北宋由于國力尚且強悍,經濟實力也強盛,所以大多透露著濃厚的享樂主義思想;而南宋國力遠不及北宋時期,且又不斷遭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所以全國從上到下都彌漫著一股濃厚的憂國憂民情緒,在詞里面關于國家、民族的憂慮也更是與日俱增。今天,我們就以北宋詞人柳永的《望海潮》和南宋詞人姜夔的《揚州慢》作一個對比閱讀。
一、品讀《望海潮·東南形勝》——領會盛世繁華
柳永是北宋詞人,婉約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精通音律,能夠自由地駕馭各種詞調,靈活地變動曲度和詞句,屬于宋朝“流行音樂”的頂級作詞人。在本詞中,他極力描繪杭州的美麗風光和都市的繁華景象。
上闋主要寫杭州的景色之美。“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開頭三句直接點明了所詠的主題,也不著痕跡地按由大及小的順序介紹了杭州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歷史、繁華的國度,讓讀者產生很強的歷史與現實的代入感。接下來的三句“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都是對頭三句的進一步解釋,“煙柳畫橋”寫出杭州水墨山水的媚態,“風簾翠幕”寫百姓住宅都是非常雅致的,“參差十萬人家”說明杭州這個地方人口多,自然物產豐富,生活富足。“云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這三句作者把目光投到城市郊外,這里呈現的自然景觀更是開闊壯觀——高高聳立的大樹環繞著錢塘江大堤,江濤洶涌澎湃,浩浩蕩蕩,江面一望無涯。作者用“云樹”夸張地形容樹木的高聳,用“霜雪”來形容浪花滾滾的情態,柳永的煉字的確別具一格,讓人嘆為觀止。后三句,作者又將目光投回北宋的市場商鋪,“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說的是市場上陳列著琳瑯滿目的珍寶珠玉,家家戶戶都存滿了綾羅綢緞,爭相比較,極盡奢華。我們通過這段描寫可以看到北宋時期的杭州真是繁華富庶,市民生活十分殷實。
詞的下闋著意描寫西湖之景。“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這三句詞主要寫的是西湖的山山水水。“重湖”是指西湖的河堤將湖面分割成內湖和外湖,所以說兩重湖。“疊”就是指重重疊疊的山,西湖有靈隱山、南屏山、惠日峰等山峰,這些山峰構成了西湖的美景。山上有桂子,湖中有美艷的荷花,景色真是醉人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湖的景色秀麗,讓人沉迷其中,流連忘返。“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說的是歌舞升平的場面:西湖上下,各種樂器的聲音不分晝夜地響個不停,這里的人采菱唱歌,釣魚的老翁怡然自樂,采蓮的姑娘都喜笑顏開,一派和諧自由、喧鬧快樂的場面。“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說的是士兵們簇擁著巡邏歸來的高官,他們也乘著酒意傾聽美妙的音樂,欣賞著美麗的山水風光。詞的最后,詞人寫道“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夸”,說的是這個美景值得每一個升官的人回到朝廷爭相炫耀,表達了詞人對杭州西湖美景的深深熱愛。
讀完這首詞,相信很多同學都會聯想到《清明上河圖》,這幅畫描繪的是北宋開封的繁華富庶,而柳永的《望海潮》則點出了杭州的繁華富庶。畫與詞都點明了北宋時期的極盡奢華,這不屬于巧合,恰恰是這個時代的真實反映。就盤活經濟這一點來講,北宋確實厲害,即使盛唐也沒法比擬。能夠活在這個時代,見證這個時代的繁榮和百姓生活的富足與自由,與下文的姜夔相比,柳永當屬幸運了。
二、品讀《揚州慢·淮左名都》——感悟古城淚光
《揚州慢·淮左名都》是姜夔的一首感嘆時局的名篇,姜夔特地介紹了本詞寫作的確切年代。這里有一段序言:“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為有黍離之悲也。”這一段序言,類似于我們現在記敘文中常用的序或者前言,交代了詞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這里詞人特地將各個元素組合在一起,為的就是讓讀者能夠真正理解其所寫詞作的心理情懷。這段小序說的是淳熙三年的冬天,姜夔路過揚州,因為連年戰亂,昔日繁華的揚州如今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都是蕭條景象,連揚州的水都變得冰冷無比,讓這個地方的夜晚更顯無限悲涼。詞人有感而發,于是創作了這首名垂千古的曲子,還在內心深處不禁產生黍離之悲。那么什么是“黍離”呢?“黍離”一詞來自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一首詩——《王風·黍離》。這是一首有感于家國興亡的詩歌,詞人用此就有一股亡國的悲涼之感。
本詞分為上下兩闋,上闋主要寫景。首句“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他說,戰爭前的揚州是一個勝地,是座名都,風景綺麗,過往的行人都解下馬鞍稍作停留,這似乎是為欣賞揚州美景作鋪墊。然而,詞人話鋒一轉,居然“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發現昔日繁華的揚州城居然到處是青青的薺菜和野麥,荒涼之意涌上心頭。是什么原因導致這樣的呢?“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這里的“胡馬”指的是金兵,原來是因為金兵南下燒殺搶掠,給這座城市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其中“猶言厭兵”四個字包含無限的悲哀之意。這里詞人借荒廢的池苑和喬木來描述這場災難性的戰爭。“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夜幕降臨,凄厲的號角又響起來了,在揚州上空回蕩,讓這座城市顯得更加孤寂與悲涼,當然包括當地人內心的恐懼和無奈。上闋將戰爭后的衰敗展現了出來,表現詞人反戰的情緒和對老百姓的無限同情。
下闋重在抒情。“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詞人特別提到晚唐時候的杜牧,他在揚州這個地方住了很久,也留下很多不朽的詩作,對揚州城可謂極力地稱贊。這里,詞人做了一個假設,假如杜牧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這里,應該會震驚萬分,縱然這位風流才子有千般風情,有神乎其技的深厚文學功底,面對眼前凋殘破敗、百姓流離失所的景象,他也一定不能寫出昔日的款款深情來,也只有暗自神傷的份了。“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揚州的名勝二十四橋仍然存在,但以往時候夜游觀賞夜景的場面已經不復存在,在冷峻的月光下,水波依然蕩漾,但四周寂然無聲,極盡荒寂、極盡悲涼。“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詞人特地提及橋邊的紅芍藥花年年如期盛放,但它們知不知道如今已經很難有人有情思去欣賞它們的艷麗。詞人用帶懸念的疑問作為詞篇的結尾,很自然地移情入景,今昔對比,催人淚下,發人深省。
縱觀全詞,全篇的感情基調一直籠罩在一片悲涼的氛圍當中。詞中“薺麥”“廢池”“喬木”“號角”“空城”都暗含著悲劇的色彩。詞人也想借這首詞,激發當朝統治者收復河山的熱情,怎奈南宋朝廷軟弱無能,已不再有收復失土的激情,姜夔的這一篇無奈之詞,徒具傷感罷了。與柳永的《望海潮》相比,姜夔的悲傷色彩更為濃烈,這是時代的不幸,也是詞人的不幸,實在可惜。
時光荏苒,宋詞已去千年。驀然回首歷史,不禁感慨萬千。柳永和姜夔是兩位深諳音律的詞人,而且《望海潮》和《揚州慢》的詞牌又是二人的首創,內容也是以城市為主要表現對象,不覺讓人感嘆這是時代的緣分,雖是緣分,但內容、情感卻天差地別。一寫盛世繁華,柳永之《望海潮》采取鋪敘的手法,描寫了杭州的繁華與人民生活的平和安樂;一寫孤城淚光,姜夔之《揚州慢》聚焦揚州的今昔盛衰的對比,表現舊地重游的悲哀。兩種情緒的交織,譜寫了兩個時代不同人的心態,今天我們重讀這份關于歷史的記載,心緒似乎別有一番情意。當今的杭州與揚州已與過去截然不同,都已涅槃重生,這當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幸。但是,宋詞中的杭州、揚州依然有永恒的象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