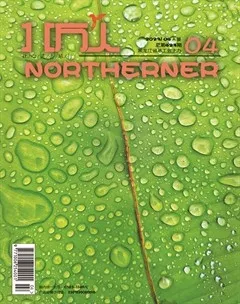我不想成為你的垃圾桶
葉傾城
與我曾經最要好的中學同學漸漸分散,我一直覺得很遺憾,但也確確實實不想與她來往了。
上學時,我們倆有說不完的話,在學校說不夠,寒暑假,我不遠千里去她家找她。那時,我們兩家還沒有住到一個院里。一個假期后,她父親調入我父母所在的系統,她家搬到我家隔壁了——天從人愿呀。
后來,我們沒有上同一所大學,但這不妨礙我一有機會就找她,我們兩個滔滔不絕地聊天。兩家都裝了電話后,我們的交流越來越容易。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漸漸不再打電話給她,每次接她電話都想辦法早早掛斷。
那時我真的很痛苦,一聽她說話就煩,又自責于自己的殘忍。她已經很慘了,父母重男輕女、男朋友三心二意、上班后領導欺負人、婚后婆婆對她不好……為什么我連聽都不想聽?
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呀。我正在摩拳擦掌開始文學創作,對這些單位上的蠅頭小利、家里的雞毛蒜皮毫無興趣。我愿意和她談文學,但她打斷我:“誰像你這么閑,還有時間看小說。我們單位領導……”
我心里想:我不是看小說,我是寫小說。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她并不關心我。
我一直在聆聽她、安慰她、給她出謀劃策。我們并不是在對話,是她在宣泄情緒,而我在承接。
我已經盡力了,我試著附和她,比如一道罵她婆婆,毫無效果,她說:“你又沒有婆婆,你不會懂。”
我鼓勵她辭職,主張帶她去旅游,她笑我幼稚,告訴我為什么不現實,為什么她做不到。
每次,都有很深的挫折感籠罩我: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卻幫不上忙。我也很委屈: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嗎?她何曾聆聽我,給過我任何幫助?她知道我在干什么嗎?她關心我嗎?
時代漸變,我開始用BP機、手機,我遲疑了一下,沒有告訴她我的手機號碼。
我們自此失聯,直到十多年后,在同學群里重新遇到。我表示要請她吃飯,她說:“誰像你這么好命?”我立刻就知道:又開始了。
我什么也沒說,因為我已經知道:我不是她的朋友,只是在某個階段是她的垃圾桶。
她為什么有這么多負面情緒?顯然是她的生活方式有問題。要一舉解決她的情緒,首先要解決的是她的生活方式,而這是艱難的。
待在毫無前途的工作單位抱怨,是容易的,勇敢辭職,靠自己去闖一片天,需要力量與自律。因此,她選擇了抱怨,抱怨隱含的內容是:我是無辜的,你要為我的不幸負責。而接受抱怨的人,往往也要下意識地接受這個“責任”,你會情不自禁想要幫助,動腦費心。
我曾經為離開她而心懷內疚,但十幾年過去,她絲毫沒有進步。這些年,她應該也找到了其他的傾訴對象吧?
我愿意聆聽朋友的悲傷,給出安慰或者建議——一次為限。如果要包月安慰服務,請付費;而那不聽我建議的人,也沒必要再浪費腦子給他們下一步建議了。
我當然也有低谷時間,我感謝每一位聆聽者的好意,樂于用各種方式給予回報。我更知道,他們最想看到的,是我走出低谷,又重新高飛。
人際交往中,我可以是燈火,照亮你的道路;可以是爐火,溫暖你的余生;可以是食物,提供給你成長;可以是藥物,治愈你的痛苦——但我不是你的垃圾桶,無休止地聆聽、陪伴,無休止地承受你的壞情緒、壞脾氣。
(摘自2022年第12期《風流一代·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