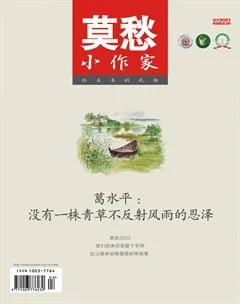萬物迎春送殘臘
1
最近,讀到宋代戴復古的《除夜 》,“掃除茅舍滌塵囂,一炷清香拜九霄。萬物迎春送殘臘,一年結局在今宵。生盆火烈轟鳴竹,守歲筳開聽頌椒。野客預知農事好,三冬瑞雪未全消。”忽然想到同學群里昨夜說吃臘八粥,心里一動,這是快過年了呀。
有了過年的念頭,腦海里馬上浮出童年時老家的那些過年場景。臘月里的鄉村,是處處都飄著 “年味”的。祭灶王爺、除夕夜接神,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祖先墓祭后,在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前,點燭燃香,跪拜祭奠,沐浴家族血脈延續的神圣,探尋個人生命的源頭;親戚走動、團賀喜慶,感受小家匯成族,眾族聚成國,家國情懷凝成生生不息的莊嚴力量。
從鄉村的“年味”中,感受到的不僅是歡樂,還有蘊含其中的文化內涵,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對生命價值的沉思。可惜,在疫情肆虐的當下,在外打拼的游子內心太掙扎了。渴望回老家過年,期冀心靈得到撫慰;又不敢啟程回老家,怕攜帶了病毒感染老爹老娘。于是只能“就地過年”,視頻里看看老家,在夢里擁抱爹媽、鄉鄰、親戚,“過年”竟淡化成了一通視頻通話,連一頓團聚的年夜飯都成了奢望。
2
我的老家在江蘇溧陽市湯橋的劉家邊,若論風水,算個寶地。村子北、西兩面是緩山坡,南面則很開闊。兩支澗水環繞小村的南北,注入村東的小河。河邊是肥沃的良田,緩坡地也能長土豆山芋黃豆芝麻。村里的人大多很勤快。但不知道為什么,日子都過得并不寬裕。麥子收上來之前,靠“預借糧”度日;秋收之前,差不多有一個月,頓頓都是吃山芋。只有到過年的時候,生產隊殺年豬、網河魚,家里殺雞宰鵝,風里才會飄過肉的香味。
清貧的日子并不妨礙村民們樂觀的生活態度。每天,清脆的鳥鳴伴著公雞高亢的司晨鳴唱,將村莊喚醒。裊裊炊煙開始在村子的上空飄蕩。村口池塘,先是勤快的男人們一個個挑著水桶來擔水,灌滿家中水缸。一陣啪嗒啪嗒的腳步聲伴著吱吱呀呀的扁擔聲過后,是主婦們噼噼啪啪漿洗衣裳和嘻嘻哈哈的說笑聲。
夜幕降臨,勞作一天后的村民回到家,一家人圍坐著吃晚飯。洗碗涮鍋之后,漢子們去隊屋里,說是算工分,其實就是聚在一起抽煙吹牛皮。我家下放回村后,建了五間房,伯父一家借住了西側的兩間。暗黃的煤油燈下,伯母輕輕地轉動著紡車。吱吱呀呀的聲音,伴著一根長長的線,仿佛在轉動悠長的歲月,永無盡頭。小村上的高文志坐在紡車對面,用一本《雷鋒日記》的毛筆字帖,教伯母和堂姐認字。“一點一橫長,一撇到丹陽,兩個小木匠,坐在石頭上。”這是個“磨”字。昏暗的油燈光,將兩家之間的木柵欄門拉長成半透明的帷幕,將屋檐下的家與院落的公共空間似分不分地“拼接”在一起。
母親似乎永遠都在褙布角、扎鞋底,為孩子們做過年穿的新鞋。做一雙新鞋,先要收集破布片,洗凈曬干,刷上漿糊,一層疊一層地褙成布角。布角陰干成硬邦邦的,用白粉畫出鞋底樣,就可以剪鞋底樣了。剪好的鞋底樣,四五層疊加,用結實且較新的布蒙起來,形成千層底雛形。再用錐子扎眼,大針粗線順著眼兒縫。每縫一針,都要用中指套著的頂針箍使勁推針鼻。線穿過鞋底,雙手拉緊。這么一針一線地納一雙鞋底,是很費時費力的。孩子們沒有耐心陪著媽媽,就各找各的樂趣。哥哥的樂趣是在雜物間里搗鼓,制作礦石收音機。
夏天的傍晚,隔著百來米,即使有知了與蟋蟀爭鳴的背景音樂,我在家也能聽得見村口海松家場院上聊家常的聲音。我是愛扎堆玩耍的。吃過晚飯,經常趁母親不注意,帶著弟弟溜進老村,加入玩耍的頑童群。或跳躍奔竄于田埂之上抓青蛙,或潛在池塘邊小河沿摸魚蝦,或藏在草垛下斷墻角躲貓貓……更多的時候,我是把弟弟塞給玩耍的伙伴,自己則去找書桂爺爺。書桂爺爺是我祖父讀書時的同桌,他給我講“獨立芝峰秀,江寧入洞天”這類的詩句,出“雞兔同籠”之類的算術考題,也講鬼故事,讓人毛骨悚然。每回聽得我回家的一兩百步都走得腿打戰,但下次還愿意聽,非纏著他講完不可。
到了臘月,村子里就開始熱鬧起來。老家那一帶的村子,過年時除了舞獅子、跑馬燈、劃龍船,各村還有獨特的節目和自己的表演隊伍,比如蔣塘竹馬燈、嵩里跳幡神、乘馬圩凍煞窠、大田村跳五猖、劉家邊跳祠山、新塘跳觀音、宋村跳關公等等,這些都是傳承了幾百年的風俗。到了臘月冬閑,表演隊就開始排練。然后從大年三十一直到正月十五,這些表演隊伍在鄉村巡演,給村莊送來熱鬧,也延續著薪火相傳的鄉村文明。小時候我并不了解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表演的歷史文化價值,只是覺得熱鬧、好玩。而且我知道,只有各方面表現好的年輕人,才能得到技藝傳授和上場表演的機會,于是擔心以后自己能不能得到上場機會。
3
村外的田里,麥苗青了,菜花黃了,稻子熟了,一茬一茬的。光景就在一年年莊稼的種植和收割中逝去。
我長大了,外出求學,進城工作、成家立業。村里的同齡人大多陸續離開了村子,外出打拼,定居城里。高門大嗓、走路有聲、落地砸坑的老一輩,曾經爽朗的笑聲,被鄉野的風刮散了。
走出村子,不算是“背井離鄉”吧?但無論走得多遠,兒時溫暖的回憶、快樂的時光,總和老村一起,在我的夢里縈繞。一縷淡淡的鄉愁,一抹濃濃的眷戀,永遠在心靈的最深處。
離開老村四十年,我終于像激流中的浮萍被帶到了靜水灣,又有了閑,可以經常回到老村,那個幾十年魂牽夢繞的地方,那個可以安放靈魂的原鄉。
今年國慶節的時候,我去村里,發現跟夏天來時又有了一些變化。老村連接集鎮的泥濘土路,改建成寬闊的柏油馬路,畫了三彩線,成為溧陽“一號公路”的組成部分。從村子到高速公路的湯橋道口,不到三公里。村里新修了水泥路面的環村道,汽車可以開到村里每家的大門口。
到了村口,見木榮嫂子家開著門,就在她家場院上停了車。木榮嫂子平日陪著海松哥在城里,只有節日才回村。海松的妹妹妹夫在城里工業園區辦了冷卻塔廠,產品很暢銷,海松哥這些年一直在廠里當門衛。去年春節前,市文旅局和農業農村局合作制作年貨節目,其中做炒米糕的視頻,主角就是我推薦的海松哥。在熱播節目中露臉,年近八十、已經四世同堂的海松哥很開心。這事過去大半年了,海松哥見了我,還在說客氣話。
往村里繼續走。迎面遇上友松堂兄。看來是中午咪了兩杯酒,七十掛零須發皆白的友松面色紅潤。他是我童年在村里唯一可以“換書看”的閱讀伙伴,雖然小學沒畢業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但他依舊迷戀讀書。他的生活中始終飄著書香和酒香。獨自小酌,享受勞作后身心放松的快樂;手不釋卷,在閱讀中感受生活的豐富與內心的寧靜。鶴發童顏的友松堂兄,詮釋著耕讀人生的從容之美。
那天下午,我在村里遇到了好多人。堂弟周松承包了村東稻田連帶一片池塘,搞“鴨稻共生”。堂侄文斌承包的自來水廠被政府收購了,遇到我就咨詢湯橋的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區開發,想引進項目落實到老村來,現在時機是不是合適。我說嫁到高淳的侄女湯蓓前幾天也打我電話呢,她父母想借力曹山的旅游開發,把村里的老房子修一修搞民宿,我說緊挨著一號公路,有文化的年輕人回來搞,可以考慮呢。
在村里走了一圈,回到村口塘邊,看炊煙裊裊升起,老村生機勃勃,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時代。抬眼北望,不遠處的曹山近幾年已成為溧陽鄉村旅游的新符號。再看村外,秋日的田野天高云淡,像一幅清雅的油畫,恬靜優美。隔著水庫看湯橋集鎮,正經歷著發展中的嬗變,將成為引領溧陽現代農業產業發展的火車頭。被一號公路串聯其中的劉家邊村,未來充滿了希望。
4
被疫情限制了腳步,我已經好久沒有回老村了。經歷了新冠疫情的折磨,我想,每個人都希望得到釋放。此刻,我在心里默念著,“回到老村,回到老村。”
回到老村,在鄉野的清香四溢中感受天地和諧,在老農的世俗拙樸里感受喜樂安寧,在煙火味中感受歲月靜好的縷縷詩意。春天已經來了,我們沒有理由停下奔波的腳步。路,越走越寬,人也是這樣,越活越敞亮。
湯全明: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多部散文集。
編輯 木木 6913729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