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棟鬧鬼的房子
李靜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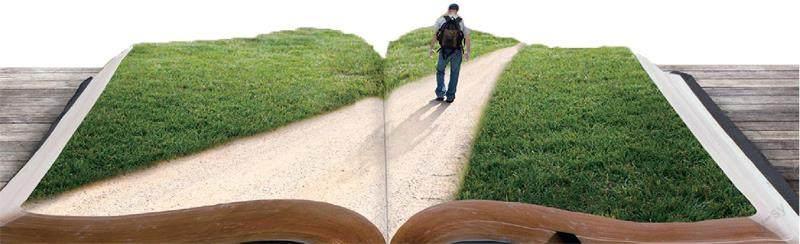
2013 年,《紐約客》刊登了約翰·威廉斯的小說《斯通納》的書評,名為“你未曾聽說過的最偉大的美國小說”。開篇即說“藝術也有遲來的正義”,氣勢洶洶,像是要寫一個開膛破肚慘死的文學冤案。
《斯通納》出版于 1965 年,當時大概賣了 2000 本。約翰·威廉斯于 1994 年去世,《斯通納》在那時早已絕版,且從未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以我的閱讀范圍看,也從未被任何當代美國文學史提及。到了 2013 年,這本書連荷蘭語版都賣出超過 12 萬本,在暢銷書榜前幾名盤桓數周,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版也差不多,聽起來像是文壇又出現了一個卡夫卡或者舒爾茨。文學評論家、作家、讀者,人人都想在這出熱血沸騰的勵志劇里打個醬油,以證明自己和50年前的同類有所不同——更聰明,更深刻,更有品位。
但約翰·威廉斯并不是另一個以被埋沒和生前失敗著稱的作家,除了曾經在緬甸和印度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一生順遂(參戰而沒死這件事可能也算得上順遂)。在密蘇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后,他成為丹佛大學創意寫作項目的負責人,還是《丹佛季刊》的創辦者,在丹佛大學平平安安教了三十幾年書,一直到 1986 年退休。結過 3 次婚,有3個孩子,活到72歲(作為一個酗酒的人,不能說短命)。他的文學之路更是讓人艷羨:一輩子出版了 4 部小說和兩部詩集,第一本小說出版時他只有 25 歲,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1973 年出版的歷史小說《奧古斯都》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這個獎的得獎名單里有福克納、厄普代克、索爾·貝婁和菲利普·羅斯,在緊接著的 1974 年,得獎作品是托馬斯·品欽的《萬有引力之虹》。哪怕是這本現在被《紐約客》稱為“你未曾聽說過的”《斯通納》,剛出版時《紐約客》也曾給出簡短而正面的評價:“一部高妙的作品。威廉斯展現出非凡的駕馭能力,講述了一個極其困難的故事。”總而言之,作為一本書和一個人,《斯通納》和作者約翰·威廉斯的命運都遠遠稱不上悲慘。沒錯,中間有幾十年他們被歷史遺忘了,然而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書和大部分人,連被遺忘都談不上,他們就像根本不曾存在過一樣。《斯通納》和約翰·威廉斯雖然是熄掉的燈,但你看那燈芯烏黑,有曾經燃燒的痕跡。
書里書外的故事有一種奇妙的映照。威廉·斯通納,一個出身農家的瘦高男孩,父親為了他以后能更好地照顧農場,讓他去讀了本地大學的農學院,他卻像中蠱一般被文學吸引,換了專業,本科畢業后繼續讀文學碩士。賞識他的老師阿切爾·斯隆給他提供了一邊教書一邊讀博士的機會,他在學校里留了下來,評教授,拿到終身教職,出版了一本寫得不怎么好但肯定也不壞的學術著作。他第一次戀愛就結婚,妻子出身良好,美麗優雅,他們先是住狹小的公寓,后來貸款買了一棟房子,生了一個女兒,長得和她母親一樣美。人到中年,斯通納愛上了一個女研究生,愛情是一場大火,他們避開家人朋友,偷偷去一個山地度假村待了一周,白天踩著積雪去森林中散步,夜晚坐在壁爐前疊好的地毯上聊天,“然后默默地看著原木上火苗千變萬化地飛舞,看著火光在對方的臉上飛舞”。他們后來分手了,因為一些庸俗得讓人震驚卻又完全能接受的原因。多年以后,他買到一本對方寫的書,扉頁上寫著“,獻給威·斯”。再后來他死了,死于癌癥。
就是這樣的一生,平庸得讓人喪氣,然而從這些浮動于表面的詞句中,你看不見失敗的陰影,就像一棟外墻裝修也算體面的房子,只有居住其中的人才知道,黑夜降臨,窗簾后的每個房間都是一片鬧鬼的廢墟,家庭、事業、內心,莫不如此。誰能想到呢?威廉·斯通納的婚姻在蜜月時就已經失敗,到后來,妻子執意要買一棟他們負擔不起的房子,原因是不想隨時隨地聽到他的聲音,而只有房間可以讓他們隔離彼此。再后來,妻子冷靜而歇斯底里地碾碎他與女兒之間的親密,只有在女兒敢和他說說話的時候,斯通納才“發現生活下去不僅是可能的,甚至偶爾有些歡樂也是可能的”。后來女兒長大了,為了逃離這個讓人窒息的家庭,她不惜和一個連喜歡都談不上的男人結婚,她也生了孩子,開始酗酒。最讓人絕望的是,他們完全不知道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為何發生,兩個自由戀愛的成年人,婚后甚至沒有過一次激烈爭吵,兩個人的日常生活像暗處的鬼魂,它一天天積蓄力量,最終吞噬掉生活本身。
整本書最激烈的情節,是斯通納竭盡所能,阻止一個他認為不合格的研究生進入英國文學專業,他為此得罪了系主任,在之后20年中飽受欺凌(當然大學內的欺凌也就是上不了自己想上的課、課程表被安排得亂七八糟等看起來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在和朋友談到自己為什么要如此堅持時,斯通納說:“我們不能讓他進來。因為如果我們那么做了,我們就變得像這個世界了,就像不真實的,就像……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
一生中有這么多關鍵性瞬間,約翰·威廉斯卻選擇一場乏味的論文答辯作為斯通納的人生高潮。作者讓我們知道它們很重要,起碼對斯通納而言,這些是他和這個該死的世界、自己該死的人生對抗的唯一武器。為了捍衛另一個世界的神圣尊嚴,斯通納,一個微不足道的英國文學教師,揮出了手中從未開刃的劍。但他還是失敗了,那個學生被順利錄取,斯通納又退回自己糟得不能再糟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他自己知道,他曾經拔出過那把劍,這讓他的人生有所不同。
在這個故事的最后,斯通納快死了,死之前他拿著自己出版的唯一一本學術著作,他看著那褪色磨損的紅色封面微笑。這本書被徹底遺忘,沒有派上任何用場,但他覺得這也沒什么關系,“他沒有過那樣的幻覺,以為會從中找到自我,在那已然褪色的印刷文字中。而且,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無法否認在其中,而且將永遠在其中”。斯通納的一小部分在這本名字都未曾提及的書中,而約翰·威廉斯的一小部分在《斯通納》中。人生是一棟鬧鬼的房子,但在鬼魂游走的地方,藏著一本自己寫的書,對每個寫作的人而言,這就是全部的不同。
(摘自上海三聯書店《死于昨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