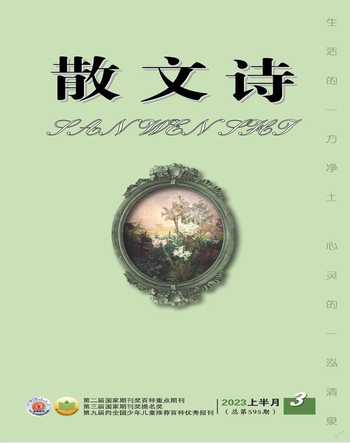敘事與沉思



王金明:生于廣東湛江,祖籍山東煙臺。影視編導,國家二級導演,現居北京。1980年代開始業余寫作,后停筆多年,2018年至今,先后在《詩刊》《散文詩》《星星》《上海詩人》《草堂》《北京文學》《星火》等雜志發表文學作品,并入選多種年度選本。組章《絲路筆記》獲2019年度中國散文詩十佳作品。電影作品《傾城》(合作)、《何二狗的名單》《等兒的濕地》等曾獲第13屆電影金雞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夏衍電影文學獎、第5屆中國人口文化獎、2021齋普爾國際電影節大獎等。獲第3屆中國電視文藝百佳工作者稱號。中國電視藝術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坐在高原的鐘聲下
搗酥油溢出陣陣芳香,仿若季節分泌的醒世經文,有人高聲誦讀,有人終生銘記。
骨笛沿著山勢說出鷹隼的軌跡,野兔藏起懵懂的幼崽。
秋色恍惚,巖畫上的馬匹越過爍金的拉薩河,奔向記憶縱深。
一位老者手中經輪走過的分分秒秒,與十年前甚或上百年前幾乎完全相同。這些年,他瞇著眼數陽光中的顆粒,數泥濘中的蹄花,偶爾也數燈苗下滾落的燭淚。
像草地陷在寂靜中,無喜無悲,寬闊無垠。也像佇立的雪峰,對塵世熟視無睹,又陡然痛惜。
一朵花邂逅另一朵花,用芬芳握手。一只羊碰見另一只羊,沒有寒暄也不會神聊,它們只是嗅嗅對方的鼻息,然后各行其道。
一個人和一縷桑煙久久相擁,看不出是道別,還是重逢。
路總是很長,通向任何地方,草從四面圍攏,又向八方散去。
此間渺遠,卻到處都有足音和心跳,仿佛古籍中傳來新鮮的人聲,你能聽見嗎?
我坐在高原的鐘聲下,靈魂被時光敲響,一生的銹跡,層層剝落。
在巖畫中賡續的時光
在納木錯北岸,巖畫是另一面鏡子,倒映著從前的羌塘草原。
牦牛,鷹隼,青羊,鹿,馬匹,獵人,唐蕃古道,鏡里鏡外,人世從來煙火稠密。
有一位發髻高聳的女子大概是你,長袍染著高原紅,正癡癡眺望著大湖對面的念青唐古拉。
一千年,還是兩千年?
望了那么久,早已超過一次愛情的長度。
窖藏的歲月,像老酒,恍惚中,我牽著你的手走出了封印的石壁,鷹在前方引路,我們跟著巖畫中的駝隊,去往今天的藏南。
一切,你都熟悉,從前的故事還在,包括喜悅和悲傷。
但這個國家,每一個春天都在更新,你看吧,夢想是新的,笑容是新的,仿佛天地也是新的,春意,不僅從草尖上萌發,也在人心里奔涌。
我用手機為你拍一張與念青唐古拉的合影,發送到祖先的朋友圈,你看,他們在巖畫中紛紛點贊,豎起干凈的大拇指。
邂逅古格遺址
與浮云對應的,是一個若隱若現的人影。
大風把邂逅吹彎,吹成殘月垂釣,沒有誰能從倉皇中取出明媚的詞語?
天堂高懸,命在低處,塵土濺起來,裹著那么多不同物種的腳步。
一個王朝漫卷的旌旗,銹成了敘事的死結,古格的骨骼,石化的懸疑,搭建謎團的腳手架,尚未來得及拆除。
巫師披著暗黑大氅,調配星宿和獅吼,一整夜演練土林,我是臨陣退縮的兵卒,夢境余悸未消。
逃進黎明的日頭,臉色如此羞慚,它曾躲開過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但塵埃始終沒有落定,傳唱史詩的人停在歷史的間歇中,失語的六百年,一晃而過。
離開得太早,又到來得太遲,我之所見不會比想象的更多,除了那些逃散的草,沿著象泉河的血緣,一簇簇返回故鄉。
插箭節筆記
一朵喇叭花無限生長,長出沉沉低語,法號對著蒼穹,開始訴說自己的往事。
吹奏的僧人運力鼓起腮幫,像犁地的耕牛,腹中的雷鳴,被一枝牽牛花帶走。
凋零之后的枝干,裸露在凜冬的矚望中,一副牛的顱骨和犄角,仍讓世界充滿激情。
勞動是對萬物的禮儀,莊嚴的起始,蒼茫的結局,謝世的人不住在這個季節,他們正在時間之外轉場,放牧人間的牲畜。
插箭節是一場大雪,靈魂的紙幡漫天歸來,像銀色的火焰。人們熔鑄記憶,用墳頭的土燒制一件永世存活的陶器。
我在雪中矮下身來,疾風掠過,山岡捧著寺廟,像有人獨自吹塤。
雪峰都有永恒的含義
野菊有時會獨自散步,仿佛被秋意困擾的少女。
曠野陷在一個青云密布的午后,陽光遠道而來,先把云杉的頭發曬干。
彩虹的責任格外婉轉,牽著牧歌從蒼穹中顯影,安詳的道路和山岡,恬淡得讓人謙遜的村落,騎手和馬群,以及心無旁騖的河流,都在自我進化。
那一刻,我堆滿塵垢的皮囊仿佛突然開始洗心革面,呼應著一對黑頸鶴的超度之旅,一生悠悠墜入愛河。
或許,愿望和結果幾乎從不會完全吻合,幸福和苦難也始終轉圜不息,但你所見所感所經歷的一切,便是答案。
細小的風捧住仰望的野菊,瞧吧,那些苦寒的雪峰都有永恒的含義。
雪蝴蝶先于我們抵達
迷途里追蹤一只白蝴蝶,另外一群白蝴蝶也在追攆我。
暴風雪不斷更改幻覺,像一篇失去了敘事方向的童話。
寒意挪動春天遺址,暖雪復原天籟之音,盡情猜想是掙脫困境的引信。
白蝴蝶是雪蝴蝶,白鬃馬是雪花馬,一個懵懂之人是風雪夜歸人。
那么多白蝴蝶,我已分不清哪一只是最初的誘惑,每抓住一只,瞬間就會碎成粉末。
找到的越多,失去的就越多。失去的越多,飛來的就越多。
而雪花馬只有一匹,睫毛掛霜,脖頸汗濕,鼻息粗重,像陷在棉花堆里的舊夢。
我松開韁繩,試圖還一匹馬以自由。
自由猶如神諭,白馬成為領舞者,帶著漫天的白蝴蝶飛旋,一場風暴跟著我們轉山,翻過黃昏的脊背,漸漸看見親愛的燈火。
馬兒把我和白蝴蝶領回家,落在窗欞上的那一只,先于結局抵達。
牦牛總是禱告
老牦牛的遲暮,像銹住的黃昏。
鏗鏘之路躍上高崗,再回頭,已是枯草漫卷。
吞咽了多少苦澀,時間仍被漏風的咀嚼所忽略,蠕動的唇語說了一輩子,也仍是茫然,仿若一種早已失傳的象形文字。
旦增老爹吆喝起來,聲音,像扔出的石頭,但牛能聽懂,他歸攏牛群,把暮色趕進月色。
是夜,月亮掛在柵欄上,像馬燈。皎潔中,牛群肅立,我也低頭想了想人生,一無所求的牛啊,是什么決定了它們的善惡選擇?
我貼近牛群,希望能聽懂它們的唇語,當它們談論愛情和人生時,會談論什么?
反芻就是對食物的感恩,旦增老爹雙手合十說,牦牛總是禱告,一直到死。
這輩子辛苦,下輩子有福……老爹嘟囔著扔過去幾捆草料。
一陣風過,柵欄上的月亮搖晃起來,淚眼婆娑。
回憶霧氣很重
一陣風掠過岡仁波齊,雪霧迷眼;一個人去了時光深處,塵緣未了。我最想念的那匹白馬,拴在傷心的月亮上。
一掌秋霜,滿腹凜冽,小杯斟滿衷腸,寄語何方?
與馬群廝混久了,很容易進化成一匹馬,脊背上,橫亙著彎曲的河流。
當你練習咀嚼青草,學會小步舞蹈,與遠方如影隨形,你已脫離想象,成為一匹現實的馬,這會給生活帶來驚喜和失措,你忍不住原地打轉,一仰頭,就能發出錚亮的嘶鳴。
我和一匹黑駿馬交換夜色,和一匹棗紅馬交換血帖,和一位老馬交換看透世事的目光。
多少鍛打在馬的體內叮當作響,跺腳的星星也擠進圍欄,老故事鼻息溫熱,添草料的人像給爐火添上炊煙,回憶霧氣很重。
蹄音如破繭之蝶,我們像雙翼神馬巡看人間。
只有那匹白馬恍若一場隔世的大雪。
落日停在他的指尖
就要動身了,這僵臥已久的季節,這火焰的廢墟,露出閃電的腳踝。
總有一莖深入的孤絕,總有千里單騎的愴然,在神諭的海拔研習取舍,靈芝的靈感來自漫長的獨處,讓我在登臨中深深內省。
凍土變軟,而羊身上的雪層層凝固,懷揣風霜的人,就要完成對苦寒的寬恕。
久治不愈的心事,發芽最后一次長旅,我夢見的回家之路,早已清除了前半生的擁堵。
你若有鷹隼的視力,就去讀植物的心靈簡史,讀陶罐里煮沸的河流傳記,讀一場雨為什么是喜極而泣。
跟著換季的人們,在歲月的繩索上,扎五種顏色的經幡,它們代表的吉祥,可以點撥所有后來者的彷徨,也包括此間即將轟然蒞臨又會陡然彌散的萬物枯榮,它們是五種顏色的暖風、五種顏色的眺望、五種頌詩的導語。
與我談論天氣的老僧,滿手皺褶,正俯身為一棵瘦弱的蒿草開光。
夕陽停在他的指尖,顫巍巍地欲言又止,久久沒有滴落。
楊樹在山坡上久久張望
高原樹少,遇見一片林子會覺得親熱,盡管只是一小片。
秋天的林子,更是讓人相惜,葉子將落未落,你也欲言又止。
草地開始清貧,這幾棵金黃的楊樹,已經在悄然彌散財富。
枝杈上黑漆漆的雀巢,像最終會剩下的一塊礦藏。
許多年前,我離開故鄉,曾有一棵帶巢的楊樹在山坡上久久張望,那個瞬間隱喻了我的一生——在歸巢和遠行之間彷徨。
路比夢遠,心比秋高,炊煙生成的疑惑,裊裊不斷。
孤獨者都擁有自己的靜默,走了那么遠,又仿佛從未離開。
一個夢境
倘若我們都鐫刻在石頭上,而神,陷在泥濘的生活中,我們是否還會向他祈禱?
我們在石壁上佇立,而神,腳步踉蹌,正背著柴薪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們在時間之外出神,而神,正勞碌在歲月的磨損中。
那個在希臘推巨石的,大汗淋漓;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又獻出一根肋骨……
我們目光悲憫地望著眾神:神也勞累,苦海無邊,一切終將歸于塵土……
我們為神祈福念經,但不知道求誰保佑它們,我們有些茫然失措……
幸好,此時一只停落在臉上的蝴蝶,把我叫醒,納木錯九月的陽光從夢的外面照進來。遠處,勞作的身影像人也像神,恍惚間我似有所悟,其實,神是天上的我們,我們是塵埃中勞碌的神。
我身旁的草叢里,有幾塊新發現的巖畫,考古隊員們正在研究,為什么一些從前的我們,現在還停在石頭中不愿出來,猶如神像?
沉思與獨白
那么多草木,是否有自己的信仰?
那么多動物,是否有自己的哲學?
我在高原上,經常問自己,也問天地。
鳥盡云孤獨,草綠羊歡喜,地平線之外,仍然是地平線,所有的答案,都是人的心意。
書卷浩瀚,萬物有靈,也都是人寫的頓悟。
紙頁上,喜怒哀樂對應著風霜雨雪。人世間,四時輪轉浸透了悲歡離合。
但大自然也許并不這么認為,它不喜不悲,無生無死。因為,只要說出來,就是人類的想法,就可能是偏見。
偏見和洞見,可能只錯開了一公分,卻失之千里,就算洞見,或許也是譫妄。
你們尋找的,我已放棄,我不會提煉真理,偶爾的沉思和沉吟,僅僅是人性的慣性。
我只是愿意和高原在一起,呼吸它的空氣,聆聽它的靜謐。
我找到了丟失的自己,就在高原一條纏人的小河邊,據說諾亞方舟曾在那里靠岸。
請換上簇新的馬蹄鐵
燕麥捧住了誰的臉?燈草纏住了誰的思念?
覆蓋五月的光焰,是一次燃燒,還是一次加冕?
雙手合十,水中天上都在祭拜。群馬出岫,草尖心尖都在澎湃。
掀起門簾就是整個高原,合上眼瞼也能看見彩虹彎弓搭箭。
哦,親愛的騎手,請換上簇新的馬蹄鐵,請從呼嘯的黎明奔來,請你甩出一條自由的長河,云游多汁的春天。
哦,那么多格桑花,都是永世的情人,風中,她們只為大地之子搖擺。
哦,盛大之愛,也可以簡化為細細的折磨,一顆恒星,始終敲打我的無眠。
曠野中,鳴蟲也在無休無止地描述愛情,它們的故事灌滿了我的淚腺。
請聽我說,人世蹉跎,也許被遺忘和被銘記的,都抵不過一次等待。
我在撩人的春色中徘徊,一會浮想聯翩,一會又喜極而泣,像一盞苦苦面壁的酥油燈。
天上的鏡子納木錯
誰需要這么大的鏡子,照一張終將泯然于眾的臉?
誰需要這么深的鏡子,照前生來世辨不清的淵藪?
誰需要這么美的鏡子,不照人間凄苦只照天堂盛景?
也許天使需要,她把云朵和藍,把霞光,把愛,投放到大地的眼睛里。
也許放羊的女孩需要,她把羊群和自己趕進鏡中,從此,她的目光永遠都那么明亮清澈。
也許月亮和星星需要,它們在一顆悲歡交集的星球上,看見了自己的倒影。
而我自慚形穢,今生不照也罷,我只需要一捧水,洗一洗臉上的塵垢,洗一洗心中的追悔。
河流是跋涉的神
有些行走太過久遠,無始無終,以至忽略了為什么出發,要抵達哪里。仿佛一直在掙脫厄運,又好似順從了天意,雅魯藏布,就在我眼前跌出峽谷。
它體中蓄滿了一千次風暴,也蓄滿了一萬種柔情,怒吼、嘯鳴和低吟,都是水的母語,一條河的陳述比塵世更蒼茫。
這最執著的前行,晝夜兼程,不知疲倦。
這最無可挽回的離開,在抵命的回溯中一次次驚濤拍岸。
從高原到大海,無盡的莽莽穿越,也只是一條河秀了一回步伐。
從遠古到此刻,浩瀚時光澎湃,也只是一條河挺了挺腰身。
無需提取任何意義,也無需猜測,河流是跋涉的神。
人類跟隨著大河走過懵懂時光,我卻站在河邊重新開始學步。
高原的風推送流年,歲月濺起浪花,把我剛留下的腳印覆蓋。
無論如何,我不可能比一條河走得更遠,除非,我成為它的一部分。
高原之秋
秋水低洄,鷹翅高亢,萬物足跡熙攘。
久遠的神山,頭頂積雪始終如初。斜披的藏袍,只需捂住半生暖意。清澈和清苦只隔著一片菩提葉,人間和天堂只隔著一道雪線。
清風送來審美和憂傷,一個人肩頭橫亙著蒼茫,種子和夢想都在尋找落腳點。
最古老的守望和出發,是高山與河流的執念,也是生命的寓言。
浮云疏離,秋色渙散,鸛鳥驚起蘆絮,雪豹越過巉巖。遠行者身影漂浮,像篳路藍縷的燈盞。
有些睡眠枯萎了,但夢還在。有些人離世了,但心愿還在。靈芝高傲,保持著锃亮的王冠,云杉樹干上層層鱗片升起鐵意,像勇士披上了出征的鎧甲。
滄海遼遠,桑田切近。
高原緩慢蛻皮,塵世喧囂的欲望漸次退隱,仿佛靈魂正在歸于塵土,那些曠遠浩大的事物,越是凋零,越是鎮定。
不斷回首的美,驚鴻一瞥的相遇,都是這個季節的禮物。
此刻,十月遼闊的遷徙正穿越我的蕭瑟心緒,向整個藏北涌來,橫斷山脈卸下轡頭,停在懸崖對岸,一只待產的盤羊對著枯草愣神,它不知道孩子來得是不是時候,也不知道,時光隧道里,一場雪正匆匆赴約。
大地隱隱胎動,充血的黎明,正穩穩托舉起又一輪剛出生的紅日。
那些樹從人間回來
一粒螢火蟲夜宿山谷,在自己小小的青燈下研讀經卷。
風搖晃著隔壁杜鵑,傳來花蕾里的人影和紅塵。
那些樹從人間回來,解開悲歡,徹底松綁,現在,它們只需要一個佇立沉思的地方。
月光撫慰篝火余燼,巖石始終沒有說話。我們的睡袋,像掛在林子邊的蠶蛹。
在樹影斑駁的懷抱里,睡著了回溯前世,醒過來看見來生,原來,人是會告別的草木。
黎明解除了夜的麻醉,新鮮的陽光像炭火化蝶,撲棱棱飛舞翩躚。
薄霧依稀,遠遠看見一座寺廟停在大山的額頭,似乎昨夜才剛剛搭建起來。
一個黃昏
旦增大叔從寺院回來,又把一袋蕎麥一罐酥油送到鄰村小學,那里,有一位內地來的支教老師,而過去,旦增只向佛進獻心意。
接著,他去了鎮上超市,買回新到的綢緞,準備更換門前的風馬旗。
他還買了一臺太陽能熱水器,但要等到兒子回來,才會安裝。
他在一塊石頭上,蹭了蹭靴底的泥。
做完這些,他給城里收羊的朋友發微信,手抖,總是打錯字,仿佛將要送走的是親人。
羊群開始陸續回村。羊也貪玩,但比放學的孩子要老實。
我想仔細觀察這個普通的黃昏,但幾個從田野歸來的人,擋住了一小部分落日。
桑吉大媽收下晾干的藏袍,抖了抖并不存在的塵土,像一棵小樹被風搖晃了幾下身軀。
扎西的身影還在草場上游蕩,馬語攪碎了小河里的夕光,卓瑪在光暈里,像朦朧的女神。
旦增大叔嘟囔著什么,進了方形藏居,他家的黃昏,從煙囪里裊裊而出。
我知道,再過一會,大媽就會出來喊我吃飯。
夕陽趴在窗口,看電視里的大風車節目,它也想進屋喝一杯。
一只小藏羚
是風暴來得太急,還是遇到了天敵或盜獵者?
一只落單的小藏羚,在可可西里浩大的曠野中,像一粒快要融化的雪花。
它踉蹌著,掙扎著尋找母親,它還不會吃草,無助而脆弱,仿佛世界上最后一只動物。
奄奄一息的小藏羚,遇到了一支科考小分隊,它成了四名年輕隊員的孩子。
用礦泉水瓶子制作了奶瓶,省下科考隊所有的配額奶粉,隊員們開始輪流做母親。
小藏羚漸漸恢復了生機,像個頑皮的孩子,每天纏著隊員拱來拱去,就連睡覺都要擠進睡袋里。
黎明被小羊舔醒,曦光甜酥酥地彌漫開來,快樂如露珠,滋潤著隊員們的苦和累。
科考日志里不僅有各種數據,還記錄了小藏羚的喜怒哀樂。隊員們為它取名:夢想。
夢想一天天長大,而風塵仆仆的科考生活,其實,也就是一次次在曠野里,懷揣夢想,眺望未來。
終于,遠遠看見藏羚羊群。是時候該告別了。但小藏羚不知道自己是一只羊,送過去,它又跟著隊員返回來,它清澈的目光里充滿了悲傷和祈求,就像怎么也不肯離家的孩子。
科考隊這些粗獷的漢子,眼里突然就涌出了淚水。
很多年后,大夢想帶著一群小夢想經過青藏線動物遷徙通道,它們總愛在遇見人的時候,多停留一會,目光溫潤而執著,仿佛在尋找失散的親人。
它們一直都在
羊群移動雪水,白云在草地上席地而坐,牧者是遠眺的冷杉。
為了兌現春天的承諾,烈香杜鵑在峽谷里升起誘惑的火焰。
獵豹斑紋,這閃電的魔咒,隱入蝶翅,漸漸變為人間花語。
一條拒絕進化的裂腹魚,“噗嗤”一聲,從白堊紀躍出水面,領航今春的尼洋河。
急匆匆的陽光,只用了8分20秒,就從遙遠的恒星趕到了南迦巴瓦峰腳下。從善如流的能量源源不斷,你也來吧!它們都在這里,一直都在。
無需攜帶任何塵世的行李,你可以擁有這里的一切,也將被一切擁有。
世界萌動,又仿佛靜止;萬物合一,又各懷其美。
存在與衛護,是歲月的天職,走在憂傷中的人,四周也開滿了花朵。
我身后,曾經的苦與樂,恨和愛,像陽光涂上又抹掉的影子,沒有留下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