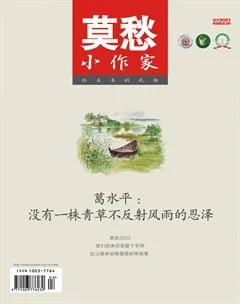一念思溪
1
小橋、流水、老宅,是婺源古村落最具特色又耐人尋味的風景。
甫入思溪村口,便見一個高高的觀景臺,站在上面可將整座村莊盡收眼底。一條清澈的小溪環抱著村莊,也滋養著村莊里的人丁六畜,還有四季不絕的莊稼蔬果。這條小河便是思溪。相傳,小河原名泗水,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死水,而村莊始建者姓俞,同魚諧音,魚在死水中自是不能成活。為吉利起見,人們將小河改名思溪,意為魚(俞)思念著汩汩清溪。
一念之間,美好的寓意代代相傳,也成就了今天的思溪古村。
深入思溪村,先要經過一座古老的木拱廊橋。橋名通濟,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間。青的地磚,木的檐廊,散發著久遠的氣息。有風從橋洞中穿過,消弭了午后的炎熱。三五個老人并排坐在長木凳上,一邊納涼,一邊閑話家常。
2
八百多年的古老村莊,繁衍著一代一代的人,也發生著這樣那樣的故事。悠長的光陰里,承載著人間或平淡或跌宕故事的,自然是那些老宅了。
走在窄窄的小巷里,踩著青石板,撫摸著斑駁的老墻,仿若穿越一條時光隧道。沿著這條幽深的隧道回溯到清嘉慶十七年,那時候,一個姓俞的木材生意人發財致富,回到生養他的村莊里,建造了一座名叫振源堂的大宅。《歙縣志》中說到徽商:“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園第,重樓宏麗。”俗話亦云:“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不管走得多遠,徽商們“根”的概念根深蒂固,對于家鄉宅子的修建,總是盡著十二分心力。
徽州三雕是徽派建筑的精髓所在。振源堂的磚雕、石雕、木雕之講究,可見一斑。門罩兩脊雕的是用以禳解火災的鰲魚,飛檐下坐斗雕的是蝴蝶和蝙蝠,下面還有麒麟、鯉魚等。它們鑲嵌在水磨青磚的花邊圖案框內,裝飾著房屋的大門,使之平添一種莊嚴繁復之美。這些精雕細琢之物,無不借用諧音,含蓄地表達了主人美好的愿望:蝴蝶寓意長壽,蝙蝠寓意福祿,麒麟隱喻送子,鯉魚象征富貴有余……
從屋外行至屋內,石雕和木雕同樣極盡精巧。在這樣重藝術重才學的家風熏陶之下,俞家英才輩出,清咸豐年間走出了一位名叫俞士英的通奉大夫,民國初又走出了兩名留洋學生,其中一個叫俞希稷的,還出任過當時的中央銀行行長。
3
從振源堂出來,看見居所墻角的護墻石,自兩米高以下九十度的直角被悉數磨去。這是思溪歷代村民為鄰里和睦,互相謙讓的見證。
在思溪村,這樣的老宅還有很多,每一座宅子都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思本堂、繼志堂、承德堂……傳達了著房屋主人對良好家風的期望。婺源曾為安徽省轄區,徽商輩出,古村落內皆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仰頭可見馬頭山墻、青瓦坡頂;大門是石門枋,門罩翹角飛檐;屋內多為一至三層穿斗式木構架,廳堂有天井院落,整體結構方方正正。每一座宅子又都各不相同,從堂號到裝飾花樣的選擇,每一處設計皆彰顯著主人的用心。
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一座建于清代嘉慶年間的百壽花廳。相傳,這是一位孝子為慶祝母親百歲大壽所建。導游帶著我們一個一個數壽字。站在百壽花廳的大門前,可見十扇隔門的鎖腰板上雕刻有百壽圖,每扇門上都刻著兩排壽字。奇的是,沒有一個壽字是一模一樣的,楷書、行書、隸書、篆書……每個字皆集書法之美與篆刻之美于一身。在正門中央,我們一共數出九十六個壽字。還有三個壽字藏得很深,導游帶著我們才找到。最有意思的是老母親住過的房間窗戶上,有兩個拉得很長的壽字,寓意“長壽”,真是匠心獨運。九十九個形態各異的壽字,立體集中地呈現于一幢房子里,將徽派木雕工藝之精湛發揮到了極致。
只是,最后的一個壽字,后人尚未找到,也成了未解之謎。當地人曾猜測,這最后一個壽字是嵌在房屋宅基線中,從空中俯瞰整幢大宅,便是一個壽字的形狀。然而,同行的攝影師用無人機從空中拍下照片,卻未見“壽”形結構。難道是幾百年過去了,大宅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又有人提出,或許這第一百個壽字原本就不存在,當孝子的母親住進這座房屋的時候,這位壽星就成了那第一百個壽字。孝子以此寓意,祝福母親壽比南山。若果真如此,這份心意可堪絕妙。古人的智慧,留給我們太多的想象空間。
4
思溪村有一座名叫敬序堂的老宅,其花廳曾作為電視連續劇《聊齋》的拍攝取景地。據《俞氏宗譜》記載,思溪村有位清代舉人俞文杰,曾為淄川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寫過兩篇跋文。冥冥中的巧合,將跨越幾百年幾千里的時空如此奇妙地連接在了一起。
徜徉其間,觀賞花廳中的精美雕刻,有戲劇人物,有山水鳥獸,無不形態逼真,不禁感慨古人的考究,還有對精致生活的極高追求。可以想象,主人在此呼朋喚友,或品茶對羿,或吟詩作畫,豈不快哉。在小花園墻壁上,有一個葫蘆形的“敬惜字紙”龕,是專門用于焚燒書畫練習留下的紙張,大約相當于今天的碎紙機罷。如今,偌大的房子已然空置,只覺氤氳著一股說不出的神秘之氣。我在心中暗想,如果一個人在此居住下來,會不會如蒲松齡一般,幻想出許多精靈古怪,再寫一部新《聊齋》呢。
順著青石小巷,穿行在這些古老的建筑物之間,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滄桑感縈繞心頭。大部分老宅顯然沒有主人經常打理,馬頭墻上爬滿了厚厚的青藤,有些藤蔓垂掛下來,竟有遮天蔽日之感。大門緊閉著,無以探究內里的情形,偶爾從窗戶或斷墻面窺探,只見院落中雜草叢生,忍不住又是一番唏噓感慨。從南宋慶元五年俞氏在此建村,八百多年的興衰沉浮,一些家族人丁越來越單薄,后人舉家遷徙他處。只有古村還坐落在這里,訴說著光陰的故事。
5
陽光逐漸西斜,從古村出來,我的腦海里裝滿了遠古的人和事,紛繁的思緒與想象。那些出資建造屋宇的主人,那些在磚石和木頭上雕刻紋飾的工匠,還有那個被孝子萬般敬重的百歲壽母……他們長著怎樣的一副面容?他們的身上發生著怎樣的故事?會在這里留下怎樣的聲氣和步履?也許只有思溪還記得吧,那村后的青山還記得吧。
經一座顫悠悠的小木橋穿過思溪,阡陌良田將我的思緒拉回了現實。站在高處回頭再看整座古村,一念之間,我仿佛剛從遠古的時代抽身而出,站在了思溪的門外。
朝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西省作協散文專委會副主任,作品散見《人民文學》等刊。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陪審員手記》《贛地風流》。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