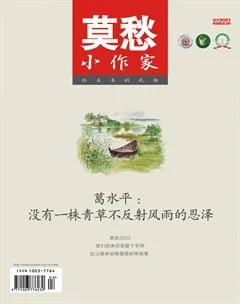縫縫補補的日子
下班回來,見小區(qū)門口的圓形水泥臺上,羅師傅又伏在縫紉機上忙碌著。舊式的縫紉機唧唧復唧唧,針腳細密行走的沙沙聲以及踏板帶動輪子的吱吱聲,聽起來極有節(jié)奏,舒緩又沉靜。
連日的雨天終于放晴,秋陽溫暖而明亮。羅師傅的老伴熱情爽朗,讓出長凳,笑呵呵地招呼一眾老姐妹坐下。她動作麻利,翻卷折壓,三五兩下,那些補好的衣物,便折疊得妥妥帖帖,裝入塑料袋,系好,待主人下班路過,拎了就走。有時,見她拿著衣物拆卸線縫,伴隨著噗噗的撕扯聲,微塵騰起又消失;或者剪掉縫補的線頭,將折縫用指甲刮刮平。往往羅師傅一個眼神,她就遞上碎布頭或者拉絲,稀松平常之中,流淌著默契與溫馨。
有一次,侄子的衣服裂了袖縫,我便拎著下樓找羅師傅縫補。咦,小區(qū)門口空蕩蕩,不見縫紉機,也沒有了聚集的人。猛然想起近段時間進出小區(qū),好像都沒有看見羅師傅了。一打聽,才知道他去了外地,給兒女帶孩子去了。正出神,又見一人拎著被子來換拉絲。不見縫紉攤兒,像是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哎,這兒不是一直有個縫補師傅嗎?羅師傅不在,我們只好拎著口袋滿街滿巷去找縫補的攤子,一下子覺得極不方便。縫縫補補看起來是件小事,關鍵時候還真是需要。
如今,少有人再穿帶補丁的衣服了。但扎線縫,換拉絲,改大小卻是常有的事。對許多人而言,穿針走線已成了遙遠的記憶。曾經,針線笸籮是居家過日子必不可少的物件。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少年時候,這些老話家喻戶曉,耳熟能詳。物質匱乏的年代,衣衫襤褸是常有的事。日子捉襟見肘,精打細算,節(jié)約勤儉,顯得尤為重要且必不可少。
衣服破了,被子裂了,可以補;鞋子壞了,雨傘壞了,可以修。會修鞋修傘的少,會補衣補被的卻多,只是手工有精細和粗劣之分而已。再說,尋常百姓,粗衣布裙,又不是金翠輝煌、碧彩閃爍的孔雀裘,哪里用得著晴雯般的心靈手巧呢。
記憶中,我們過年的新衣都是父親一針一線縫制出來的。那時候,父親總有干不完的活。直到新年臨近,父親幾乎徹夜不眠,量尺寸,畫印痕,裁剪,縫制。朔風凜冽的冬夜,昏暗的煤油燈下,靜坐的父親仿佛一尊色彩單調而凝重的油畫。當新年的太陽升起,我們一定會如期穿上新衣新鞋,和其他小朋友一樣高高興興地奔赴各家各院顯擺一番。
父親的手工極好,裁剪得當合體,一丁點兒布都不會浪費。針腳細密規(guī)整,好像縫紉機縫出來的一樣。不管是單衣還是棉襖,父親都自己做,不但能省下一筆錢,還美觀好看,牢實耐穿,這讓我們很是自豪。而他自己,長年累月一身破舊的衣服,讓我們心疼又羞愧。
不穿舊衣不得老,不吃稀飯不得飽。父親穿舊衣穿得有些理所當然。衣服舊得不成樣子了,還是舍不得扔掉。拆下布片來,搓成繩子,做背索;打成布殼,做鞋底鞋墊,物盡其用。長期以來,節(jié)儉于他,已變成一種習慣,深入骨髓。所謂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如今,古稀之年的父親,依然勤儉節(jié)約得要命。補衣補鞋,甚至破了的麻袋,當然還有籮筐筲箕,鐵鍋廚具。東西破了舊了,他從不會一扔了之,總是修修補補,用了又用。
現(xiàn)在想來,縫縫補補,沒有什么不妥,甚至無不顯示著生活的智慧。不管是衣物,還是情感,破了裂了,縫縫補補,又妥帖起來,歲月的車輪又緩緩向前。
王優(yōu):四川省蓬安中學教師,作品散見于多家報刊。
編輯 閆清 14533370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