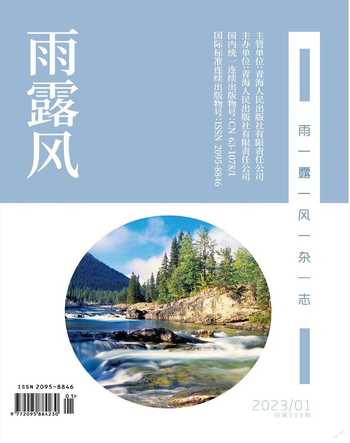論肖江虹小說中的悲劇色彩
2018年,肖江虹憑借其民俗“三部曲”中的《儺面》斬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在民俗“三部曲”中,作者描寫了蠱鎮、儺村、燕子峽的傳統習俗文化,表達了內心深處對傳統文化沒落的惋惜之感。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1]55,在肖江虹筆下,趙錦繡和顏素容的悲劇性、城市化影響下傳統技藝的失傳、農民掙扎求生的艱苦狀態,都展現出面對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沖突,以及人們的堅守與抗爭。悲劇不會讓讀者產生愉悅的心境,也不會帶來舒適的閱讀感受,但能從中找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了解作者對底層人們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及展示出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探尋。
一、女性悲劇
女性人物描寫在肖江虹作品中所占比例較少,大多是以男性人物形象為主要描寫和敘述對象。但在《蠱鎮》和《儺面》中,女性敘述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不管是嫁為人婦,面對丈夫外出務工的留守婦女趙錦繡,還是決心在城市打拼立足但被迫回到家鄉的顏素容,都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悲劇性色彩。
(一)留守婦女趙錦繡
趙錦繡,一個勤勞能干的留守婦女,主動承擔起家里的責任與重擔。她不僅要照顧公婆和兒子,家里的農活也全落在她肩上。在趙錦繡觀念里,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作為家庭婦女,趙錦繡辛勤勞動,為家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勞力。正如戴錦華與孟悅所談道,“家庭幾乎是專為女性而設的特殊強制系統,它具有顯而易見的性別針對性和性別專制意味”[2]6,女性在家庭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視與壓抑。在肖江虹小說中,我們仍能看到囿于家庭而無法展示自己真正女性價值的趙錦繡。
面對丈夫的背叛,趙錦繡選擇的是忍讓,甚至想以一種平和的方式處理。當趙錦繡質問丈夫時,她內心極度渴望王四維站出來與自己辯解,甚至希望丈夫欺騙自己。種種行為都顯示出趙錦繡將全部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寄予在丈夫身上,作為女性的主體性在趙錦繡身上完全消失。
趙錦繡在維持搖搖欲墜的家庭中親手扼殺了自己的女性意識,把自己置身于從屬地位。她對自己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妻子、母親、媳婦的身份上,唯獨忘記了自己作為女性的身份。把自己的兒子和丈夫作為生命全部,這是趙錦繡無意識狀態下接受和形成的觀念。
(二)“歸去來”的顏素容
率先離開故鄉踏上城市道路的顏素容,她最大的夢想是扎根大城市。在她的眼里,故鄉的一切都無法與城鎮相比,她輕視儺村的一切。在顏素容為扎根城市而打拼奮斗時,卻因患病而不得不離開都市。顏素容認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終會得到這個城市的接納,可命運不但不給她努力奮斗的機會,還要奪走她的生命。無奈之下的顏素容回到曾經逃離的儺村,回到自己最看不起的鄉村,看到秦安順制作儺面,還不忘嘲諷幾句“都哪朝哪月了,還鼓搗這破爛貨”[3]260。顏素容在意識深處始終傾向城市,顏素容總認為“城市的月亮要比儺村的圓”,她是一心奔向城市卻被拒之門外的脆弱女性。回鄉與秦安順相處期間,她慢慢沉下心來重新認識自己生長的故鄉,深入接觸儺村的傳統文化。看到家鄉美麗自然風光,也感受到濃濃的鄉里鄉情,更為秦安順身上的生死觀所震撼。是秦安順讓顏素容放下對儺村的芥蒂,重新找回屬于她的心靈棲息地,可秦安順的離去卻讓她再次陷入迷茫與絕望。命運就像一雙無形的手置于顏素容的頭頂上空,看到她找到一點希望就隨之將其毀滅。
顏素容處于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想要奔向城市而被拋棄,想要回到鄉村而無歸屬感,甚至發現自己與鄉村生活格格不入。正如小說開頭描述一樣,顏素容高跟鞋踏在歸鄉石板上發出壓抑悶響,身上的紅裙好似儺村一朵妖艷的蘑菇,她與故鄉的靜謐與美好景色是違和的,她既不屬于城市,也不屬于故鄉,而是處于“城鄉中間層”的尷尬位置。對她來說,遠方是無盡的,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
二、城鄉變遷帶來的悲劇
大批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傳統鄉村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肖江虹描寫出貴州獨特的傳統文化遺產與它面臨消亡的處境。在《蠱鎮》中,有對最后一代制蠱師王昌林制蠱與尋找下一代制蠱師的描寫,《儺面》中講述了最后一代儺面師堅守與儺戲的凋零。
(一)傳統文化沒落
在民俗“三部曲”中,作者著力描寫了隨著城鄉變遷人們不斷涌向城市,致使繼承傳統民俗文化的人極少,甚至后繼無人的現實境況。作為蠱鎮制蠱最后一代傳人,王昌林還在堅守與傳承,可是卻找不到傳承技藝的下一代蠱師。他最后的心愿是制成一道蛇蠱,關于蛇蠱的傳說,都認為這道蠱能“顛倒時序和返老還童”。面對年輕一代的離去無能為力,唯有制成這道蠱,在年齡上重返青年,繼續守護鄉村和傳承祖輩留下的技藝,這是年老一代技藝人的愿望。蠱鎮老人告誡人們“不要輕易越過豁口,一線天的那頭有吃人的妖怪,紅頭綠面,口若血盆”[3]178,這是老人想要守住自己村莊的善意謊言,可是人們還是沒有抵住外面世界的誘惑,離開了蠱鎮,甚至到了更加遙遠的地方。面對青年一代的相繼外出,蠱鎮陷入一片死氣沉沉的狀態,傳統文化淪落到無人繼承而失傳的悲涼境遇。
秦安順作為儺村的最后一位儺面師,一直堅守自己作為儺面師的職責。對于他來說,儺面是一種信念,更是一種精神的歸屬。對于獨自一人生活的秦安順來說,面具下母親與父親的生活瑣碎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安慰與補償,甚至堅信這一張老舊的面具能接通另一個世界,儺面帶給他的不僅是一種責任與守護,更是一種心靈的皈依。他總是跟自己說“唱哪樣唱喲!沒人聽得見,狗日的秦安順唱給狗日的秦安順聽”[3]304,這些都是秦安順心里的無奈與悲痛。在無聲無息中走向生命的末端,這是他作為最后一代儺面師的無聲告別,也預示著儺戲這種民間傳統就此凋零。作品中對老一輩的堅守與擔當給予了巨大的贊賞,但對他們獨自的堅守與離世展示出深深的哀婉之情。
(二)生態環境破壞
“面對現代社會,面對人與自然的關系越來越緊張的現狀,‘民俗三部曲中,人和這片土地上的動物、環境的和諧共生,滲透著原始的生態美,也表現出作品的生態思維。”[4]作者在文學創作中對生態意識做出回應,《懸棺》中能明顯看出作者的生態意識觀念。
在燕子峽,鷹燕是保證人們糧食豐收和不受饑餓的保障,燕子峽人民與之和諧相處,從未做出任何傷害鷹燕的行為,這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型。但是,來向南偷采燕窩販賣這一舉動給燕子峽和曲家寨兩族帶來巨大變動。采集燕窩使燕子峽的鷹燕逐漸離去,“那些黑點慢慢變淡了,天邊終于失去了鷹燕的影子,只剩下枯瘦冷漠的巖壁”[3]220,燕子峽人因此受到了大自然的懲罰,又過上了挨餓、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來向南把偷采來的燕窩賣到鎮上,正是知道人們的“需求”,才會動這一惻隱之心。從來向南破壞燕窩這一舉動來看,這是斷絕了燕子峽的生存之路,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這是破壞生態平衡,打破了生物鏈循環的錯誤之舉。縣上派人對燕子峽人的搬遷進行動員與勸導,并打算在燕子峽修建電站。對于縣級工作人員來說,修造電站是人類的一項壯舉,因為這是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大奇跡。但殊不知,這一舉措是人類的愚蠢行為,在尋根作家返回自然與返回傳統的兩大主題中,強調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
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而非征服與被征服的對立關系。生態意識背景下,作家立足貴州具體情況,在《懸棺》這一作品中流露出明顯的生態意識,強調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底層農民掙扎的悲劇
燕子峽人有著堅韌的意志力和頑強拼搏的精神,面對常年饑餓威脅,他們堅強努力地活著。在這里,莊稼收成全看天意,如果燕糞充足,雨水足夠,今年的糧食就足夠生活,不用忍受饑餓的折磨。可這樣的生活穩定性太弱,沒有保障。為了求活,要面對流傳久遠的攀巖精神文化被游客褻瀆,在物質生活與精神信仰堅守方面,只能選擇其一。
(一)物質生活的艱難
燕子峽所處地勢極其特殊,這里沒有厚實肥沃的土壤,經過暴雨的沖刷留下的只有成片的懸崖與石頭。面對貧瘠的土壤,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免遭受饑餓,這是不可擺脫的自然悲慘命運。
燕子峽人所取的名字也具有一定象征意義,來辛苦、來畏難、來高粱、來稻谷這些名字,寄予了農民對糧食的深切渴望,也銘刻了他們艱難的生活處境。名字背后暗含著人們飽受饑餓的折磨,害怕缺乏糧食,寄予對食物充足的美好愿望。燕子峽祖先遭受災難被困在山洞時,年老孱弱的一輩主動放棄生的希望,以保護青壯年、女人。在他們的思想觀念中,自己的存活只會搶奪后代子孫的生存空間,他們的選擇在大多數人看來是十分偉大的,但抉擇背后的原因只有無盡的心酸與無奈。這種自我犧牲行為與鷹燕殉崖是何等相似,其背后隱藏著的是現實生活壓力的無奈之舉。在來畏難的記憶中,摘野菜是常有的事,糧食缺乏只能靠野菜充饑,好不容易遇上茂盛的野菜也會感到無比欣喜。“鵝兒腸、車前草、蛤蟆菜、黃芽尖,這些飯桌上的常客”[3]237,足以窺見他們艱苦的生活,可以看到糧食缺乏帶來的饑餓問題一直困擾著燕子峽人,這是底層農民無法擺脫的艱難生活境況,所謂的摘野菜卻叫“向土地討口吃的”,只是為了填飽肚子和不挨餓。肖江虹小說立足于底層人民生活,強調從多角度展現農村農民的生活狀況,正如相關評論者談到“他關注底層、悲憫底層,不是與創作潮流、社會現實斷裂和對抗,而是順時隨俗,在感同身受中書寫社會的劇變。”[6],從而進行作者的人性思考。
(二)精神信仰的放棄
燕子峽人在這種環境下必須做出選擇,要么留在燕子峽,保護祖先的懸棺,繼續生活在這片飽含深情與信念的土地上;要么離開燕子峽,尋找一片易于生存的棲息地。但現實是,鷹燕離開了燕子峽的土地,也許明天回來,也許再也不回來了,沒有了栽種莊稼的肥料,全村再一次陷入缺糧的處境中。最后迫于生活的壓力,燕子峽與曲家寨兩族人還是妥協了,在痛苦與掙扎中放棄了自己的故鄉。在物質生活與精神信仰方面,他們不能兩全,只能舍掉其中之一。
燕子峽的巖壁上留下的是祖輩與命運和現實抗爭的痕跡,這是屬于燕子峽獨有的精神印記,寄予著燕子峽人的信仰與歸屬感。但最終來辛苦向現實妥協了,主動勸告兩寨人搬遷,這是在物質壓力下放棄了精神的守護,看到大水淹沒村寨,水中漂浮著的棺木,燕子峽人心中極其痛苦。來高粱選擇留下,不愿離去,他帶著自制的木翅膀從崖上降落,與燕子峽祖先一同沉入河中,用自己的生命來堅守和維護祖先遺留的信念。
在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中,物質與精神同樣重要,但在經濟與物質的影響下,人們還是被迫放棄了屬于整個族群的信仰,如《蠱鎮》中青壯年不愿學習和繼承歷史悠久的制蠱技藝,而是奔向城市尋求生活來源;《儺面》中梁興富只顧將儺面具推向市場,而忘記了儺面中豐富的深刻意義。不管是來辛苦選的擇離去,還是來高粱選擇的堅守,都無法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四、結語
王杰提出“悲劇沖突是悲劇藝術的核心情節,也是悲劇美構成的核心要素”[5]203,在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中,正因為城鄉間的對抗與沖突,才出現蠱鎮、儺村、燕子峽三個地方的人們與現實抗爭、搏斗的一系列故事,但最終都無法逃脫毀滅與消亡的悲劇性結局。作者并沒有直接展現悲劇性場景,而是探討在城鄉變遷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與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一變化給鄉村,尤其是鄉村人民帶來的變化。肖江虹在作品中將視點聚焦于鄉村人民,展示他們在城鄉沖突中不屈服于現實,奮力反抗與搏擊的斗爭精神,是對底層人民處境的關懷與思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處于城鄉沖突中的農村人究竟該走向何處,作品中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都是作者對當下現實問題的涉及與叩問,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民俗“三部曲”中的悲劇色彩,既表達了作者深切的人文關懷,也是他將悲劇性色彩從個人人生意義的感受轉化到社會性的價值意義,這是肖江虹作品的一大貢獻。
作者簡介:何雪(1997—),女,貴州黔西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注釋:
〔1〕來風儀.魯迅雜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9.
〔2〕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肖江虹.懸棺[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
〔4〕楊蕓.生態批評視域下肖江虹“民俗三部曲”研究[J].蘭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2,38(03):3-6.
〔5〕王杰.美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6〕陳國和.肖江虹:擦亮人性之光的貴州書寫[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4):25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