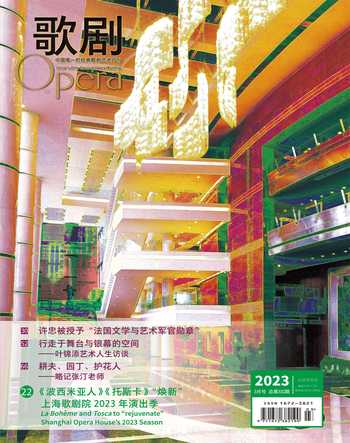以情動人以景引思
李棟全



作為上海歌劇院2023 演出季開幕大戲,新制作的《波西米亞人》早已讓懷念現場欣賞歌劇已久的觀眾們迫不及待、望眼欲穿。意大利歌劇大師普契尼耳熟能詳的經典歌劇、上海歌劇院重啟中外合作后的全新制作,加之石倚潔、王沖、周曉琳、孫礫等一眾優秀歌唱家,吊足了觀眾的胃口。
就現場效果而言,爆滿的上座率和持續不斷的掌聲,再次證明了普契尼歌劇的悠久影響力和上海歌劇院的滿滿誠意。普契尼用情至深的音樂在演員和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的詮釋下,足以消融2 月的春寒,滋潤觀眾渴望已久的心靈。同時,中外導演合作帶來的全新制作,以極富創意的舞臺布景和調度引發對人性和人類未來更深刻的思考。
一、《波西米亞人》的“巧計”與“潛能”
普契尼作為歌劇史上屈指可數的旋律天才之一,卻曾遭受遠超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所受到的非議和責難,不同于同時代理查· 施特勞斯常被詬病的“庸俗賣弄”,普契尼則主要被指責為“粗俗膚淺”。尤其是當這種責難來自歌劇批評界的泰山北斗約瑟夫· 科爾曼時,似乎更無可辯駁。科爾曼對普契尼的批評集中于《托斯卡》,延伸至《圖蘭朵》和其他作品,《波西米亞人》也未能幸免,被批評為“坦率地停留在表面,因而具有某種蒼白、貧血的病態魅力”。普契尼研究專家莫斯科· 卡爾納曾為普契尼的“感官傾向”和“做作傷感”辯駁,呼吁大家以更開放包容的藝術欣賞眼光看待普契尼歌劇。可科爾曼并不認可。幸運的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歌劇批評家伯納德· 威廉斯清晰客觀地觀察到了這種矛盾的本質,他在《新格羅夫歌劇辭典》“歌劇”詞條中解釋歌劇的本質時,指出普契尼具有“在這種無可爭辯的歌劇傳統中創作出高度受歡迎的新作的能力”。威廉斯洞悉了普契尼的“巧計”——利用觀眾對音樂技藝的期待、對歌唱家的期待來獲得劇場效果。
《波西米亞人》顯然是彰顯這種“巧計”的絕佳典范。這部經典歌劇值得反復觀賞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這種“巧計”,而非充足的戲劇深度。大部分熱愛歌劇的觀眾,哪怕不少剛入門歌劇的觀眾,都熟悉《波西米亞人》,他們走進歌劇院之前就已經或多或少知曉這部歌劇所能帶來的音樂期待。甚至,許多觀眾走進歌劇院就是為了再次體驗某些“停留在表面”的美好歌唱和某些樂隊中的美妙動機。顯然,普契尼早已預測到了這一點,甚至利用了這一點。
因此,觀眾對《波西米亞人》戲劇情節上的期待,自然會隨著對這部歌劇熟悉程度的增加而減少。那么,展現這部歌劇“潛能”的重任就落在了歌劇導演和指揮身上。一方面,如何在大家如此熟悉的作品中挖掘戲劇新意,成為導演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另一方面,如何把握音樂風格,處理好普契尼埋藏在總譜之中的主導動機和音樂色調,如何細致地處理音樂,形成獨具特色的樂團風格也成為指揮身上的重任。顯然,上海歌劇院此次的新制作在這些方面都獨具思考,亮點頗多。
二、歌劇導演的詮釋與審思
自20 世紀下半葉以來,歌劇保留劇目庫愈發固化,新創作難以躋身其中,歌劇導演的地位不斷攀升,兩種趨勢合謀,使“導演制歌劇”逐步盛行。因此,在傳統制作仍有一席之地的同時,不少經典歌劇在先鋒歌劇導演的奇思妙想中幻化出許多令人出乎意料的新制作,《波西米亞人》自然也不例外。傳統導演尊重自然主義風格,試圖還原19 世紀巴黎的人文風情,而先鋒導演則通過此劇表達自己的全新詮釋和精神世界。
弗朗哥· 澤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的制作古樸懷舊、布景逼真,竭盡全力地在舞臺上復刻19世紀巴黎拉丁區,細致地構思劇場空間,讓角色之間的互動更親密,時至今日仍不斷復排。當然這種相對傳統的舞臺制作在對普通觀眾十分友好的同時,也招致了不少先鋒導演的批評,指責這種“傳統”制作姿態媚俗、死氣沉沉。遭受同樣批評的還有約翰· 科普利(John Copley)導演的版本,同樣也使用了傳統布景和還原時代特點的精細服裝道具。但是這兩個經典版本能夠經久不衰,延續超過40 年,很重要的一點并非其自然主義的舞臺布景,而是這種“傳統”制作充分尊重音樂,能夠讓舞臺布景和調度配合歌者,未曾試圖剝奪觀眾對于音樂的欣賞。
然而,不少先鋒導演并不愿意還原這種陳舊復古的“傳統”舞臺。2017 年,理查· 瓊斯(RichardJones)導演為英國國家歌劇院制作的《波西米亞人》從灰色鋼結構閣樓開始就引導觀眾進入現代都市,在極簡的舞臺布景中思考當代都市人的現狀。同樣在2017 年,克勞斯·古特(Claus Guth)更加天馬行空,他為巴黎國家歌劇院制作的《波西米亞人》將故事地點改到了發生故障的太空飛船中,打造出了具有《星際穿越》風格的舞臺布景,并通過現實與幻想的并置,徹底顛覆了原有故事,引起不少爭議。
先鋒歌劇導演嘗試用獨特的視野為經典歌劇帶來新生,這一點值得肯定,不過當歌劇導演的奇思妙想成為不切實際的奇思怪想之時,這些導演構思會導致歌者或樂隊無法表達音樂的要求和內涵。當今觀眾顯然已經對導演的新奇構思有心理準備,不少觀眾甚至非常期待歌劇導演的奇思妙想,但是觀眾認可的前提條件是新制作不只是展示某些導演的個人風格,而是更應挖掘歌劇總譜中我們未曾發現的、或不經意間忽略的重要音樂細節。彼得· 塞拉斯(Peter Sellars)的某些經典制作就是這方面的典范,在激進主義的舞臺制作中也能為我們清晰、透明地展現歌劇總譜的意涵。
此次上海歌劇院新制作由意大利導演馬可· 卡尼蒂(Marco Carniti)和中國導演楊競澤合作完成。與克勞斯· 古特一樣,將《波西米亞人》的視角延伸至想象世界,只不過卡尼蒂和楊競澤構想出的未來世界是一個冰封世界,“寒冷”主題在此版新制作的服化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厚實的大衣、羽絨服甚至第二幕孩童的宇航服,都時刻提醒我們此刻的寒冷。不過,相較于克勞斯· 古特顛覆整個故事,兩位導演并未拋棄觀眾,故事仍舊是我們熟悉那個故事,只不過發生在未來,通過寒冷反襯人性的善良、人心的火熱。
卡尼蒂細致精妙的舞臺調度,讓故事得以輕松展開,尤其是咪咪與魯道夫初次見面之時,舉手投足間展現了這對年輕人一見鐘情卻羞于表達的含蓄,讓觀眾倍感真實,投身到他們的情感發展中。曲終之時,也不免讓觀眾感慨即使在遙遠的未來,彼時彼刻人與人之間的邂逅仍如此時此刻,人性的力量能夠打敗時間。
相較而言,楊競澤導演在這兩位導演中反而更顯激進,他主導的舞臺布景構建出頗為抽象的未來世界,不禁讓觀眾回想起2021 年他執導的未來主題歌劇《七日》。不過二者相較,《七日》的布景更加激進,甚至晦澀,彼時舞臺上具有象征意義的道具讓不少觀眾眉頭緊皺、迷惑不已。此次《波西米亞人》的布景顯然更易理解,舞臺上的冰天雪地和寒氣逼人的冰雕,與我們能夠想象到的寒冷更為貼近,未來世界并未成為侵占觀眾視覺注意力的焦點。此外,旋轉舞臺已經成為近些年中國歌劇制作的熱門選項,其靈活快速的特點能夠讓轉場銜接更為流暢,因此在第一、二幕之間,觀眾能夠清晰地跟隨魯道夫和咪咪走出閣樓,走進巴黎平安夜的街頭。全劇結尾魯道夫發現咪咪死去之時,伴隨著魯道夫撕心裂肺的呼喊聲,快速旋轉的舞臺制造出情緒崩潰時的眩暈感,與肅殺的血紅色燈光營造出強烈的悲劇感,讓觀眾沉浸其中、意猶未盡。可惜這種貼切的舞臺效果直至結尾才看到,稍嫌不過癮。此外,本劇劇本作家之一的賈科薩在創作時就發現第二幕頗為令人擔心,尤其是街景和室內場景不斷穿插,在普契尼大師手筆之下人物調度成為每個導演的難題。此次兩位導演采用了分區設計,讓室內外場景分立兩側,來解決這一難題。不過該場景中舞者的介入稍微吸引了觀眾的注意,或多或少會影響觀眾的視覺重心。
歌劇導演如果只從劇本出發思考舞臺制作和調度,難免會喪失歌劇音樂中的意圖和趣味,這也是不少先鋒制作的通病。普契尼這部歌劇音樂色調豐富,埋藏了大量主導動機,如果導演不細讀總譜就難以理解這部歌劇,難以真正理解普契尼。這版新制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導演在這方面的諸多思考,例如第一幕與“魯道夫動機”同時出現稿紙,“冰涼的小手”中“愛情動機”出現后埃菲爾鐵塔上亮起紅色“Je taime”(法語“我愛你”),以及為第二幕巴黎街頭嘈雜音樂安排了嘈雜的群演,這些導演構思都試圖讓舞臺制作與音樂達到更深層次的關聯。
三、準確且不失個性的角色塑造
蕭伯納在1894 年《曼儂·萊斯科》倫敦首演后,就斷言普契尼“比任何競爭對手都更像威爾第的接班人”。普契尼延續了意大利歌劇的極致抒情,在用音樂刻畫人物方面獨具色彩。正如前文所言,普契尼必然清楚,塑造人物的重任很大程度依靠歌唱家,因此他總能把握觀眾的期待,在恰當的戲劇情境下停止時間,盡情施展自己的旋律天才,為歌唱家揮灑歌喉提供空間。
飾演魯道夫的石倚潔擁有豐富的舞臺經驗,能夠在舞臺上信手拈來。在第一幕名場面“冰涼的小手”中深情款款、揮灑自如,他甜美的音色為魯道夫帶來了一股詩人的書生氣和溫柔淺色。整場歌劇,他的舞臺動作自然流暢,在展現魯道夫的年輕活力的同時,更凸顯出歌唱者熟稔舞臺的個人魅力,贏得掌聲不斷。王沖飾演的魯道夫,則著重展現底層藝術家的含蓄和哀愁,舉手投足間都是魯道夫落魄詩人的灰暗顏色,讓觀眾入戲更深,感同身受。
不同于普契尼筆下的柳兒和巧巧桑,盡管都是悲劇女性,咪咪似乎只有與魯道夫在一起時才有一絲活力與血色。我們看到周曉琳飾演的咪咪著重表現溫柔,她溫暖的聲線隨著戲劇的發展逐漸變化,極致弱音讓她在最后一幕咪咪死亡的場景中保持了優雅,瀕死之時都在表達對朋友的感謝,更令人心碎。楊琪飾演的咪咪纖弱動人,第一幕與魯道夫初見之時的柔弱體態更凸顯出社會底層的艱辛,游刃有余的演唱讓觀眾感受到咪咪的另一個側面,同樣令人動容。
穆賽塔的塑造難度在于其驕中帶柔,媚而不俗,張文沁的詮釋激情四射,初登場時的一襲紅裙和爽朗的聲音成為全劇寒風凜冽、雪窖冰天中的一抹亮色,“漫步街上”更贏得連連掌聲。
兩組演員都精準塑造了一個個戲劇人物,無論是友善的馬爾切洛、熱心腸的柯林、衣冠楚楚的舒奧納還是喜劇性的貝努瓦和阿欽多羅,都有細致微妙的個性風格,真實自然,唱演俱佳。從現場熱烈不斷的掌聲來看,這些歌唱家們滿足了普契尼的“巧計”,滿足了觀眾們的期待,更凸顯了個人魅力。
四、樂隊直擊心靈的音樂色調
歌劇的重中之重是音樂表演,而歌劇音樂的表演絕非只在于歌唱,更在于樂隊,尤其對于《波西米亞人》而言,樂隊的表現更會直接影響歌劇的觀賞體驗。
普契尼在《波西米亞人》中善于用樂隊營造氣氛,這種氣氛不僅是第二幕巴黎街頭的喧鬧氣氛,更是全劇富有幻想和悲傷氣質的青春色彩。莫斯科· 卡爾納稱《波西米亞人》“能夠喚起對永恒青春的想象”。對于樂隊來說,如何把握這種氣氛成為每個指揮的重任。上海歌劇院交響樂團在許忠駕輕就熟、揮灑自如的指揮下,展現出出神入化、巧奪天工的精妙把控,肆意挑逗我們的音樂感官。第一幕,魯道夫與咪咪初見之時,樂隊中的層次和情緒逐步鋪陳展開,弦樂的細致刻畫,單簧管的時間凝固,豎琴描摹的水滴和月光,都極富色彩與詩意,為這種青春色彩奠定了基色。而到第四幕,當第一幕的音樂元素再次大量出現時,樂隊準確表現出的則是青春的悲傷氣質,尤其當咪咪在“我的小軟帽”中回憶與魯道夫的初次見面時,樂隊總能適時改變色彩,沁入一絲凄涼。
普契尼在《波西米亞人》中的另一成就在于細致的“主導動機”。他不僅僅為每位主角色量身打造諸如“魯道夫動機”“咪咪動機”“穆賽塔動機”等人物動機,更為一些生活化的小物件打造了精妙動機,比如第一幕的“爐火動機”、第二幕的“帽子動機”,此外還有最容易被聽到和記住的“愛情動機”。這些細致的“主導動機”在各個聲部之間切換游走,甚至疊加裂變,而樂隊總能準確把握,音響清澈干凈、層次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小提琴聲部展現出無與倫比的細膩情感,可謂行云流水、爐火純青。樂團首席張樂熟稔歌劇,不僅在多個獨奏片段展現出豐富的音樂色彩和強烈的情感張力,更能帶領聲部準確把握音樂情緒的細致變化,尤其小提琴聲部在咪咪臨終場景中渲染出了震撼人心的情感維度,在肝腸寸斷和撕心裂肺之間自如切換、游刃有余。這段曾讓普契尼掩面哭泣,感慨“咪咪之死仿佛看著自己的孩子死去”的片段,曾在過去一百多年間贏得無數淚水和掌聲,此次演出也不例外。
不可否認,盡管有些細節仍需繼續打磨,但是樂隊整體效果才高氣清,沒有絲毫矯揉造作和惺惺作態,充滿了真摯的感情,非行家里手不可為也。除此此外,童聲合唱和舞臺樂隊也是此次制作的一大亮點,既輕松活潑、詼諧幽默,又能恰如其分地融入第二幕的喧鬧之中,絲毫不影響戲劇進展和音樂質量,而且合唱團與舞臺樂隊在上半場結束時謝幕也頗具新意,讓小朋友們免于熬夜,彰顯出主創團隊的人文關懷。
總而言之,《波西米亞人》在公眾中獲得了極高的認可度和強烈的情感共鳴,導演充分發揮才思,突破時代壁壘,與觀眾的情感緊密相連。上海歌劇院此次新制作證明只要尊重總譜,尊重人性,尊重觀眾,就能大獲成功。更難能可貴的是,新制作在中外導演的攜手努力下,更深地思考未來。或許未來世界充滿寒冷、沖突、磨難和艱難,但是我們對未來的期待,正如觀眾期待“冰涼的小手”中的high C 一樣,期待其歌詞“La Speranza”所表達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