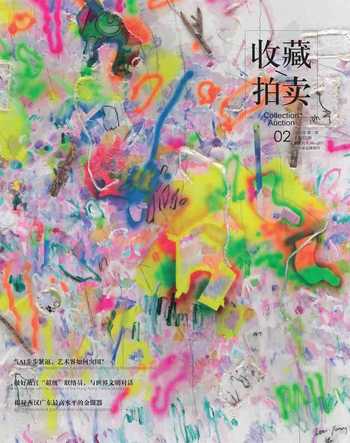知名藏家近年頻頻釋貨:你的藏品最后留給誰?
馮瑋瑜



去年,香港的收藏市場風云一變,多名資深收藏家的藏品驚艷拍場,劉鑾雄、張宗憲的舊藏幾乎每季拍賣都有重器出現于拍場,而香港著名收藏團體“敏求精舍”的會員幾乎同時把自己收藏多年的藏品推出市場,例如嘉德香港2022年秋拍同時推出了三個敏求精舍會員專場,即“大巧若拙——竹月堂藏瓷”“瓷緣——達文堂藏明清御窯瓷器”“軒華六帝——懷海堂藏清代御窯瓷器”,同時期,保利香港、香港邦瀚斯也分別推出了敏求會員舊藏品拍賣。
為什么一時之間,以往稀見于拍場的著名收藏家的藏品頻頻出現于拍賣會呢?難道是這些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因資金緊張而要變賣藏品?
事情由一場香港網拍引起
絕對不是!以懷海堂鐘棋偉先生為例,他去年捐贈了價值1億多元的中國古陶瓷藏品給香港藝術館,還另外捐贈了一些藏品給剛開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在不停捐贈藏品的富豪,左看右看都是個不差錢的主。
而另一個專場“大巧若拙——竹月堂藏瓷”的竹月堂主人簡永楨先生,與我更是相熟,他和我及香港明成館更在2022年10月于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御案存珍——竹月堂、明成館、自得堂藏清初三代御案單色釉文房瓷器”
展覽。簡先生和我在這些時日里時常聚在一起,他正雄心勃勃籌備2024年在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單色釉瓷器展,還出資800多萬元購買了一只元青花梅瓶捐贈給吉美博物館,哪有資金方面的問題!
事情的導火索或許是香港的一場網拍。
那是2021年6月11日佳士得香港“古今網上拍賣——中國藝術”網絡拍賣,這場拍賣拍出了佳士得香港有史以來網拍的最高成交額。
由于是網拍,拍賣行對拍品沒怎么認真地斷代,大部分都是隨意定為民國之類,有的拍品干脆不寫年代了,有的還是幾件拍品合成一個低價標的就上拍,其實是清三代的名品。估價大多不超過10萬元,真系咁大只蛤乸隨街跳(意思是:天上真的會掉下那么大的餡餅)?沒想到拍賣時波瀾迭起,多件拍品拍出的成交價不低于大拍的價格,數百萬元的成交價不斷涌現,令人吃驚不已。
即使如此,仍然讓很多行家大叫“撿了大漏”,而且是一個接一個的“大漏”。
后來市場才傳出,這場網拍的部分拍品是香港某富豪舊藏的一部分,是其某一支后人拿出來的。
都是香港有頭有面的富豪,大家對彼此之間的收藏多少還是有所了解的,如此身份地位,其藏品竟然以網拍的形式出現,讓其他人撿了大漏,這讓那些知根底的藏家無不搖頭嘆息:崽賣爺田心不疼。
藏品的最終歸宿應該在哪?
“藏品的最終歸宿”一直是收藏家們不可避免的話題。畢竟藏品都是自己畢其一生的心血,價值也不少,這其中含有藏家收藏的艱辛、研究的喜悅,還有藏友間來往的情誼等。藏家到了晚年,如何處理藏品歸宿便不得不考慮“家人的意見”,但往往很多后人對藏品并不懂或者并不感興趣,藏品最后落得個被變賣的下場。
如果藏品的最終歸宿能落到真正的藏家手里,當然是最好的,那樣才能挖掘和發揮藏品的真正價值,更是藏品生命的延續。不過并不是所有的藏品都有這樣的幸運。
不到半年,那場網拍出來的拍品再次出現在國內拍場,價格翻了一倍多,一件東西就被人半年賺去幾百萬元,可想而知,那一場網拍,當初被低估賤賣了多少!這活生生的事例極大地震撼了香港那批老藏家:與其留給不喜歡、不懂行、不知價的后代賤賣,不如趁自己在生時處理掉,把錢留給后代,好過把藏品留給后代。
既然后代不喜歡,就不必強留給后代了,自己抓緊處理吧。
換一個角度看,現在香港那批老藏家,大多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收藏的,到現在已經四五十年了,年紀漸漸老邁,也到了交班換棒的時候,所以從這兩年開始,香港老藏家舊藏的釋出浪潮一波接一波,讓我們這些后來者有機會接棒名家舊藏。一個時代的落幕,也是一個新機遇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