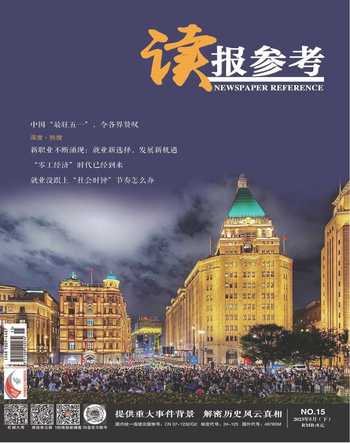仇恨、暴力:美國愈演愈烈的亞裔歧視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ué)歷史系助理教授貝絲·廖-威廉姆斯在《無處落腳:暴力、排斥和在美異族的形成》一書中說,“種族暴力是美國建立的基礎(chǔ)”。這一論斷在亞裔被歧視的命運上再次得到印證。近年來,美國少數(shù)族裔在醫(yī)療、教育、住房等領(lǐng)域持續(xù)面臨系統(tǒng)性歧視,其中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尤為猖獗。
美國亞裔遭受歧視現(xiàn)狀
19世紀(jì)以來,亞裔在美國被歧視的黑暗史從未停止,而且如今越發(fā)嚴(yán)重。根據(jù)美國“制止仇恨亞太裔美國人組織”發(fā)布的《2020-2021年國家安全報告》,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間,共有9081件針對亞裔群體的歧視和騷擾事件,64%的亞裔美國人受到侮辱性言辭對待,超過13%受到不同程度的身體攻擊。其中,華裔在受歧視的群體中占比43.5%,韓裔、菲律賓裔、日裔和越南裔占比42.7%。華裔成為受害最為嚴(yán)重的群體。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持續(xù)高發(fā)。2020-2022年間,“制止仇恨亞太裔美國人組織”共收到近11500起仇恨犯罪事件報告。據(jù)《洛杉磯時報》報道,亞太裔數(shù)據(jù)研究組織的在線民意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2021年每6個亞裔美國人中就有1人經(jīng)歷過種族暴力。
另外,亞裔還遭遇高等教育“平權(quán)歧視”。1960年代,美國社會興起平權(quán)運動,旨在幫助社會中長期受到歧視的群體爭取教育以及就業(yè)平等機會。為此,政府部門招收職員或公立學(xué)校招收學(xué)生時,將為少數(shù)族裔留出一定名額。但隨著高等學(xué)校實施“種族配額”措施,一部分優(yōu)秀的亞裔群體反而被排斥在入學(xué)范圍之外,導(dǎo)致亞裔群體在接受高等教育領(lǐng)域遭受“平權(quán)歧視”。2015年5月,在美國亞裔教育聯(lián)盟的組織下,包括華裔、印度裔、韓裔等在內(nèi)的64個美國亞裔團體,聯(lián)合向美國聯(lián)邦教育部平權(quán)司和司法部遞交申訴,要求對哈佛大學(xué)實施“種族限額”措施導(dǎo)致的亞裔歧視展開調(diào)查。
總的來看,美國亞裔遭遇種族歧視和迫害的特點有四:一是亞裔遭襲事件呈現(xiàn)遞增趨勢;二是亞裔遭襲事件中,老人與婦女等弱勢群體最容易受到攻擊;三是華裔成為亞裔遭襲事件中的主要被襲擊對象;四是亞裔遭襲事件中,襲擊地點通常為公共場合。
亞裔歧視的社會根源
一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結(jié)構(gòu)和思潮作祟。白人至上可謂是美國立國的思想之基,貫穿了美國迄今兩百四十余年歷史。在其影響下,美國形成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結(jié)構(gòu),處于上層和中心地位的是白人,而處于底層和邊緣地位的是少數(shù)族裔。白人種族主義群體通過奴役、反對、排斥和暴力迫害少數(shù)族裔,維護白人群體的利益和特權(quán)。當(dāng)前反亞裔種族主義便是美國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的表現(xiàn)之一。
二是美國經(jīng)濟衰退刺激白人勞工階級極端主義復(fù)燃。白人勞工階級針對亞裔的暴力歷史可追溯至1860年代,而這一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從未被根除。當(dāng)下美國,近六分之一的黃金工作年齡男性(25-54歲)沒有穩(wěn)定工作,近八分之一的男性完全失去了工作動力。這類人群的主體是從事非月薪型工作,沒接受過大學(xué)教育的白人勞工階層。他們將失業(yè)或收入下降的原因歸咎于外來移民和其他種族群體對于白人特權(quán)的“腐蝕”。美國白人指責(zé)亞裔搶走美國人的資源和工作機會,而亞裔中老年人、勞工、服務(wù)員等收入較低的弱勢群體,則面臨當(dāng)?shù)匕兹说钠圬?fù)和侮辱。
三是美國政治的白人至上主義化。隨著中美關(guān)系摩擦加劇,美國極端分子和政客反復(fù)渲染“中國威脅論”,引發(fā)新一輪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浪潮。在美華人及其他亞裔群體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危險的外來人群。美國官員的煽動性言論加深了錯誤的刻板印象,從而給整個少數(shù)族裔群體帶來進一步的歧視和生存性危機。
此外,美國多元文化主義民族政策的失效和“大替換”理論給美國政客排斥移民提供了借口。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推行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即承認(rèn)各個族群或宗教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并將其考慮到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中。然而在“9·11”事件以后,美國開始從多元文化主義回歸白人至上主義文化。植根于歷史土壤的社會仇恨認(rèn)知,有時會體現(xiàn)為仇視外來移民和少數(shù)族裔的極端主義行徑。
與此同時,人口的變化,特別是非白人人口的增多,使一些白人認(rèn)為西方社會正在遭遇“大替換”,即白人正在被非白人群體所替換。人口結(jié)構(gòu)的變化正在改變著美國社會的政治,因為將不會有足夠多的白人選民來支持白人至上主義。當(dāng)前“大替換”理論已經(jīng)成為美國社會和政治話語,為白人政客反對移民和亞裔等少數(shù)族裔提供了口實。
四是美國霸權(quán)的衰落造成白人認(rèn)同的焦慮。在非白人國際力量崛起,非白人文明國際秩序觀發(fā)展,以及國際種族批判理論敘事興起的多重沖擊下,美國主導(dǎo)的白人至上的國際秩序出現(xiàn)了危機。這種霸權(quán)衰落的失落感、危機感讓美國白人精英和大眾感到焦慮,成為“美國優(yōu)先”“美國至上”等白人民族主義內(nèi)政外交政策出現(xiàn)的緣由,亞裔也因此遭受更多的歧視與攻擊。
(摘自《光明日報》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