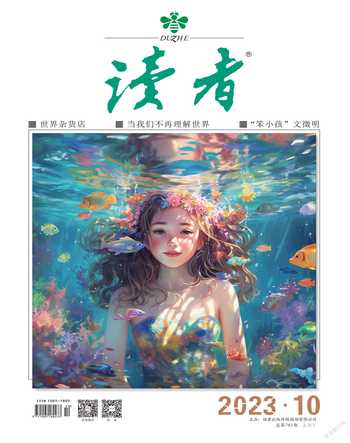疤痕效應
香帥

人類會對巨大的傷痛存有長久的記憶。
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一場創傷結束后,它的直接影響會被個體遺忘,但創傷所帶來的心理后遺癥仍將持續。中國古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經歷過大災大難后,人們的行為會不自覺地發生變化。比如,有研究發現,在印度尼西亞,那些經歷過地震或海嘯的人,在之后的3年中性格會明顯變得更加保守,做出冒險行為的可能性會比其他人群的低41%。同樣,在日本,大地震后的5年時間內,震區居民會變得更加厭惡風險。
人們會因為一次重大事件永久性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比如,即使之后一切回歸正常,經歷過重大危機的消費者也未必愿意大膽花錢,企業未必愿意正常投資、生產,暫時關門的小微個體未必能夠重新開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勞拉·維爾德坎普用“疤痕效應”來描述這種現象。
歷史經驗的產物
每個人對未來的預期,都是其自身歷史經驗的產物。比如,中國的“80后”“90后”“95后”這幾代人生活在國家快速向上發展的時期,繁榮和增長就是他們的歷史經驗。所以,他們會認為所謂的經濟危機、大蕭條,離自己很遙遠。但是,如果經歷了一場重大的、長期的沖擊,人們就會被現實教育,從而生長出新的歷史經驗。比如,在經歷過一次持續性饑荒事件后,人們就經常會擔心將來再次發生糧食危機。又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任何銀行的流動性危機,都會被市場反復解讀。2022年,金融巨頭瑞士信貸的流動性出現問題后,市場馬上變得風聲鶴唳,擔心它會成為下一個雷曼兄弟,引發新的金融危機。在長久的沖擊事件影響下,人們可能會被教育得過度悲觀,更厭惡風險,更追求穩定。個人和家庭會更多地存錢,企業會攥緊現金,這些都是疤痕效應的體現。
所謂正態分布,就是在正常狀態下,一般事物總體呈現出的一種數據分布規律,即處于平均值水平的最多,處于極端值水平的極少。在正態分布下,越偏離均值的數據出現的可能性越小,所以數據是呈“細尾”分布的。比如在我們上學時,大部分同學的學習成績是中等水平,滿分和不及格的比較少。
但是,在感受過一次重大尾部事件沖擊后,人們的思維模式會受到影響,覺得尾部事件并非黑天鵝事件,偏離均值的尾部事件發生的概率因此會被人為放大。人們傾向于認為“細尾”會變成“肥尾”。在這種預期下,人們自然會在行為上做出反饋,比如存留余錢,行為趨向于保守;抑或是覺得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不如及時行樂,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
疤痕效應
從美國的相關數據里,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疤痕效應正在持久地重挫長期產出。比如,經濟數據顯示,在疫情補貼停止之后,美國消費者的支出跟過去相比顯著減少。對感染病毒的恐懼,讓文娛、旅游等服務行業很難完全復蘇。學者預測,從長期來看,疫情后的經濟產出可能會比疫情前的水平低3%~4%。
勞動力市場的“疤痕”更深。疫情前,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一直保持在63%以上,最高曾達到67%左右。疫情中,勞動參與率一度跌到60.2%,此后一直沒有恢復元氣。
截至2022年10月,美國的勞動參與率為62.2%,盡管經濟增速已經到了5.9%的歷史高點,但勞動參與率仍然沒有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63%和62.2%,看上去僅僅不到一個百分點的差距,但實際對應的勞動力缺口高達160萬人。勞動力缺口大,會導致工資水平難以降低,從而影響美國控制通貨膨脹的節奏,對貨幣政策、資本市場都將產生連帶影響。
為什么勞動力市場的缺口這么大?原因很復雜,但疤痕效應一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很多資深勞動者在暫時離開勞動市場后,會因為“疲倦感”而就此永久離開,很多公司也選擇永久性歇業。研究發現,2020年3—5月,有43%的美國公司選擇了暫時停業。而在疫情后的恢復期內,有超過10萬家公司永久關閉,它們之前提供的勞動崗位也就永遠消失了。
除了勞動參與率,勞動者在遭遇創傷后的疤痕效應可能更嚴重。
人們往往認為生不逢時是最悲慘的事,其實“畢業不逢時”也一樣。
美國斯坦福大學勞工經濟學教授保羅·歐耶爾發現,在經濟衰退期畢業的MBA(工商管理碩士)學生,會因為起點低,導致終生收入比經濟繁榮期進入職場的個體低150萬~5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000萬~3500萬元)。就業市場的“摩擦”是極大的。
如果一個人讀完MBA,因為大環境不好,沒能去華爾街工作,那么他之后再到華爾街工作的難度就會更大。
中國這幾屆在疫情中畢業的大學生,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也需要花費很大精力來使這個疤痕愈合。不過,疫情只是2022年眾多疤痕中的一道而已。中美貿易摩擦、俄烏沖突、歐洲能源危機等,無一不在造成長期的創傷。
漫長的愈合之路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和《經濟學人》前編輯、現彭博社專欄作家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在他們合著的《繁榮與衰退》一書中寫道:“金融周期的下行區間總是比上行區間更容易凸顯,因為恐懼是一種比貪婪更有力量的情緒——當人們擔心自己一生的努力會化為泡影時,這種恐懼會促使他們用盡一切手段來保護自己不受這場危機的侵害。”換句話說,疤痕會漸漸變淡,但很難完全消退。
2021年的前兩個月,武漢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3.6%,而全國的數據是增長6.4%。和武漢經濟規模相差不大的其他幾個城市,蘇州是13.1%,成都是8.9%,南京是15.7%。疫情前,成都與武漢的發展條件最為相似,而且這兩個城市的相對經濟增速具有長期穩定性。從消費看,武漢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恢復程度遠遠落后于成都,也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武漢不是特例,全球多個國家都有過類似“疤痕”: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金融學教授大衛·艾克曼等人觀測了巴西等5個新興國家,以及美國等19個發達國家自1970年以來經歷各種危機后的經濟恢復情況,分析了50年(1970—2019年)的數據,發現這些國家從“疤痕”中恢復的速度比人們想象的要慢得多,一次重大沖擊的拖累時間可能長達10年。
而受影響的經濟體在10年間的實際GDP增長率會下降4.25%。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儲蓄率持續10余年一路上升,英國持續了6年,歐盟持續了4年。
為什么在遭受巨大創傷后疤痕難以徹底愈合呢?大概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第一,在經濟嚴重衰退期間,社會整體利潤率大幅下降,會給一部分剛進入市場但未來可能有更大潛力的新企業造成傷害,導致這部分企業被“錯殺”,進而阻礙新企業進入市場和創新的速度。衰退時間越長,對企業的扼殺越徹底。其實,繁榮經常是和冗余相連的。
第二,長期、大面積的失業問題會影響社會的人力資本積累。就像一個優秀的外科醫生必須通過完成足夠多的手術才能被培養出來一樣,人力資本的積累也需要在干中學,沒有干的機會,人力資本會迅速折舊。同時,高失業率還會導致人力資本的錯配,導致“能搞原子彈的去賣茶葉蛋”。雖然從個人角度來說職業無貴賤,但從社會角度來說,人力資本的錯配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下降。
第三,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企業和居民都會喪失投資和消費的動力,更不要說增加在創新上的投入。尤其像新冠病毒疫情這樣的重大沖擊,改變的是人們長遠的心理預期,這將造成長期總需求的重大缺口。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這個缺口很難自然愈合。
中國經濟在2023—2024年可能會面臨一個帶疤的恢復期,和一般經濟周期下行的負向沖擊不同,疫情沖擊對中低收入人群、小企業和新企業的影響更大。如果面對疤痕效應,政策層面不能有清晰的認識,不能對癥下藥的話,這個恢復期可能會更長。相應地,不管是企業、家庭還是個人,可能都需要對此有更清醒的認識。
(夏 扇摘自新星出版社《錢從哪里來4:島鏈化經濟》一書,辛 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