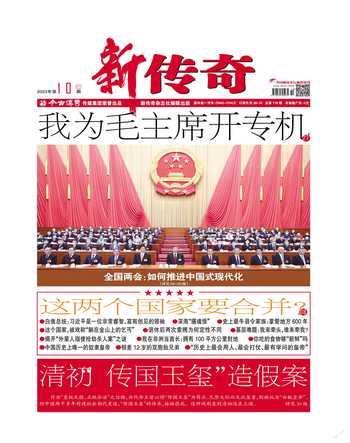“改革先鋒”厲以寧

“中國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這條路并不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而是彎彎曲曲的。”厲以寧認為,經濟學家應該有勇氣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反復提醒:“可以不說話,但不要說假話。”
2023年2月27日,著名經濟學家、“改革先鋒”厲以寧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3歲。
1930年11月22日,厲以寧出生于南京,后隨經商的父親移居上海。抗戰爆發后,他隨母輾轉至湖南沅陵,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開始了在北大長達70余年的生活。
由同學代填志愿考入北大
1949年4月,南京解放。這個歷史事件改變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運,包括金陵中學的才子厲以寧。厲以寧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深造。他當時選擇了化學工程系。因為他立志要做一個化學家,實現工業救國抱負。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了運轉。厲以寧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幾年后,厲以寧再次參加高考,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學趙輝杰代為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選學經濟系最為適合,優勢較大,就替老同學作主,第一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最終厲以寧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大。
大學期間,他從宿舍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到老師的辦公室,埋頭苦讀、孜孜探索,學問和思想都迅速成長起來。在老師們的影響下,厲以寧的研究目標和領域明確了下來:探索現代經濟的規律,服務祖國和人民。
1955年,厲以寧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他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一干就是20年。
盡管資料室的工作冷清寂寞,但他卻得以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持之以恒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進行獨立思考和判斷。“這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使我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視野進一步拓寬”。
后來,厲以寧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與他這段經歷不無關系。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看講義,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
獲得“厲股份”的稱號
與此同時,厲以寧也密切關注著現實的經濟問題。到1979年,回城知識青年大約1700萬,再加上320萬沒有就業的留城青年,總數達到2000多萬,幾乎相當于當時全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就業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和國家勞動總局聯合召開的勞動就業座談會上,厲以寧第一次提出,可以號召大家集資興辦一些企業,以此來解決就業問題,企業也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遺憾的是,他的建議無人響應。
但是,厲以寧從此開始深入研究股份制。其實,在股份制背后,是他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路徑的思考。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明確提出,實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1986年,他在北京大學的科學研討會上,講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在理論界的激烈爭論中,厲以寧堅持為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大聲疾呼,獲得了“厲股份”的稱號。
時代的大潮把厲以寧推到了有關改革重要問題研究和建言獻策的前沿。在火熱的20世紀80年代,厲以寧曾借調到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也曾受國家體改委的委托,領導課題組研究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期規劃。和他們同時開展研究的,還有吳敬璉、劉國光等經濟學家領銜的其他多個課題組。他后來回顧這段歷史時曾坦承,當時沒有想過改革的時間表,“中國一定要走改革的路,但是這條路并不是一條筆直的大道,而是彎彎曲曲的”。
改革時代風云激蕩,唯有大勢無可逆轉。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改革新目標,極大地推動了股份制的步伐。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混合所有制”新概念,股份制得到了認可。股份制改革得到長足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出現新面貌。在這些重要改革成果的背后,厲以寧的貢獻不可磨滅。
從1988年起,厲以寧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仍然不遺余力地為推行股份制而努力。
1992年成立全國人大證券法起草小組,厲以寧被任命為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因為涉及利益復雜,關注者非常多,爭論也非常大。1998年,證券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1999年,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成立,厲以寧再次擔任組長。2003年10月,該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高票通過。
“可以不說話,但不要說假話”
2003年,厲以寧轉到全國政協,他十分關注民營經濟。2003年,厲以寧給國務院提交的一份調研報告,提出了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拓寬融資渠道、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等建議。一年多以后,國務院制定了“非公經濟36條”,要求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由于各種影響因素存在,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并非易事。
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每年全國“兩會”上都有這位經濟學家的身影。厲以寧的一言一行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也曾身陷爭議。他認為,經濟學家應該有勇氣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反復提醒:“可以不說話,但不要說假話。”
不管是在人大常委會還是作為政協常委,厲以寧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在做官。他“不想當官,只想做學者”。作為一名教授,他從未遠離過北京大學的校園。每一代知識分子都要面對不同的時代,厲以寧的身上背負著前輩知識分子的厚望與期待,他自己又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著思想領域。
在厲以寧看來,從1979年起,中國進入了雙重轉型階段:一個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一個是發展轉型,就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兩種轉型的重疊,在世界上是沒有前例的,因此中國改革的難度非常大,絕非是一代人的事業。
“參與改革,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這是厲以寧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通過撰寫回憶錄,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驕傲,就是我們參加了改革,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財經》 馬國川/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