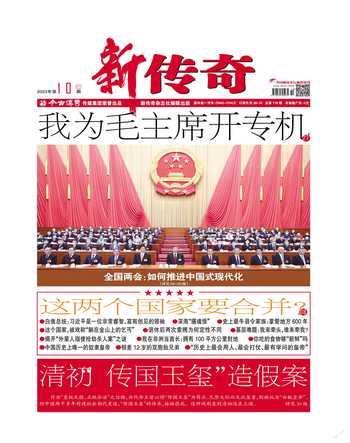破紀錄!26年得12次腫瘤竟然痊愈
人的一生患上腫瘤的概率是多少?在26年間先后患上12種腫瘤的概率又是多少?這個聽起來超越了醫學認知的提問,實際上是一名女性的親身經歷。她從出生起先后被診斷出12種腫瘤,但她一次次從死亡陰影中逃脫,至今仍幸存于世。
人的一生患上腫瘤的概率是多少?在26年間先后患上12種腫瘤的概率又是多少?這個聽起來超越了醫學認知的提問,實際上是一名女性的親身經歷。她從出生起先后被診斷出12種腫瘤,但她一次次從死亡陰影中逃脫,至今仍幸存于世。
26 年,12 種腫瘤接踵而至
W(患者化名),出生于1986年。出生時,她的體重和身長略低于平均水平,在新生兒期還出現了生長遲緩和精神運動遲滯的跡象。但隨著W長大,這些問題逐漸消失,W似乎像普通的孩子一樣茁壯成長。
然而,在W兩歲時,她被診斷出患有外耳道胚胎型橫紋肌肉瘤。這是一種發生自胚胎間葉組織的惡性腫瘤。幸運的是,在經過多個療程的放化療后,W的腫瘤被成功治愈,但同時她也出現了生長發育延遲的情況,開始使用生長激素治療。
15歲時,W的股骨、肱骨和尺骨相繼被檢查出內生軟骨瘤。這是一種良性腫瘤,呈惰性生長,可以通過保守治療來成功控制。但沒過多久,W又被診斷出早期宮頸透明細胞癌。詭異的是,宮頸透明細胞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胎兒期母親服用己烯雌酚或患者感染HPV,但W的母親從未服用過己烯雌酚,后續檢查證實W也沒有感染HPV。這意味著,W的早期宮頸透明細胞癌可能是某些未知因素所推動形成的。因此,在切除了子宮、雙側附件并接受了放療后,W又一次戰勝了癌癥。
20歲時,W被診斷出腮腺多形性腺瘤,這是一種具有較強惡變傾向的良性腫瘤,她不得已又接受了手術。一年后,檢查發現W左側腮腺和左側乳突相繼出現梭形細胞肉瘤,她再次接受手術,第三次戰勝了癌癥。此后4 年間,W 陸續因非典型痣、乳腺脂肪瘤、毛母質瘤和多結節性甲狀腺腫接受手術,好在這些均為良性腫瘤,切除后復發風險并不高。
26歲時,W因結腸腺瘤接受切除手術,醫生在結腸腺瘤中發現了黏膜內腺癌,這已經是W第四次患上癌癥了。28歲時,醫生又從W的直腸中切除一枚腺癌,隨后又在腸鏡下切除了管狀腺瘤。
至此,W已經接受了至少10次手術和多輪放化療。不幸中的萬幸,此后她再也沒有罹患新的腫瘤,此前的腫瘤也沒有再復發。
地毯式搜索,鎖定元兇
W為什么會患上12種腫瘤?又是如何一次次死里逃生的?西班牙國立癌癥研究中心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人員首先為W進行了全面體檢。結果發現,W存在較為嚴重的發育遲緩,她的身高僅有146cm。她的雙顳骨較窄、眼睛深陷、中面發育不全、小頜畸形、耳位低并后旋、眼球震顫……顯然,她在外貌方面存在諸多異常。
同時,W的皮膚有廣泛色素沉著和色素脫失區域,有咖啡牛奶斑(一種皮膚色素沉著性病變,是多種遺傳性疾病的皮膚表現之一)和角化過度性斑塊。結合這些特征,研究人員懷疑W存在某種遺傳性癌癥綜合征。
很快,研究人員在全基因組測序中發現,W的血樣中檢測到了有絲分裂抑制缺陷蛋白1樣蛋白1(MAD1L1)的雙等位基因突變Q66*和E628*,這兩個終止突變會導致細胞內合成的有絲分裂抑制缺陷蛋白1(MAD1)出現缺陷,使人體內存在大量但并非全部的非整倍體細胞,即鑲嵌型非整倍體現象。
非整倍體細胞由于其染色體結構不穩定,很容易出現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突變,進而導致腫瘤發生。讓W頻繁患癌的原因似乎找到了。
死里逃生,她的幸存能否復制
研究人員進一步對W的家人進行了測序和病史調查工作,發現W的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中均存在患有癌癥或不明原因流產等疾病的成員。
通過對W及其父母的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MCs)進行染色體核型分析,研究人員發現,W父親的PBMCs中有0.7%為非整倍體細胞,W母親的PBMCs中有1.5%為非整倍體細胞,而在W體內,這個數字竟然高達39%。
雙等位基因突變加上異常高的非整倍體細胞比例,讓W的體細胞中充滿了非整倍體細胞,如同充滿了一個個“不定時炸彈”,進而導致了腫瘤的頻頻發生。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讓W能夠屢次從癌癥中逃生?
在對W的PBMCs進行進一步分析時,研究人員發現,鑲嵌型非整倍體(MVA)在W的腫瘤發病過程中,同時起到了正面和負面作用。也就是說,這個讓W患癌的“罪魁禍首”,一定程度上也是她的“救命恩人”。
MVA在人體內誘發的強烈炎癥反應,似乎可以解釋W家族中不同成員出現不同表現的現象。例如,W的家族成員中有MAD1L1突變攜帶者出現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發流產等情況,這和免疫系統的過度活躍有一定關聯。而W屢次患上惡性腫瘤,其中部分腫瘤(如之前切除的直腸癌病灶)已經進入中晚期階段,但針對惡性腫瘤的治療在W身上屢現奇效,讓她在28歲以后維持了無腫瘤狀態,這與她持續活躍攻擊異常細胞的免疫系統同樣息息相關。
截至研究發表時,W的身體依然保持健康,而W的經歷也能為更多癌癥患者帶來新的希望。
(澎湃新聞網 方婧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