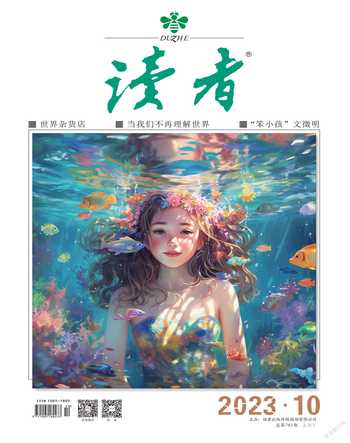一場道聽途說的往事
林特特

我在天通苑西打車,來的是個女司機,皮膚黑,細眉細眼,燙過的頭發綁成馬尾,非常健談。堵車時,她已和我聊完三代的家事。
車行至龍德廣場,我們在紅燈前停住,的姐忽然不說話了。她搖下車窗,臉沖馬路那邊發愣。后面的司機按著喇叭,對她喊:“干嗎呢!”過了一會兒,她沖剛才發愣的方向努努嘴,又對我打開話匣子:“紅燈那兒過去一個人,我還以為是我妹的前男友。”
“你妹的前男友?”我很驚訝,上上下下打量她,“瞅年紀,您有四十五歲?”我故意說小幾歲。
“哪里,五十多嘍。”的姐如實答。
“那你妹妹想必小不了幾歲,是她三十年前的前男友吧?你還認得出?”我表示疑惑。
“怎么會認不出呢?”的姐緊握方向盤,目光聚焦前方,“說個故事給你聽。”
三十年前的“前男友”,姓馬,人喚“小馬”。三十年前,小馬二十歲,和的姐的妹妹同齡。兩個人是發小,在一條胡同長大,一直同班,成績爛成一條水平線,中學畢業后,分別招工進了紡織廠和鋼廠。他們二十歲時,的姐二十三歲。遮遮掩掩地早戀若干年,正式出雙入對整一年時,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我按常理猜,“懷孕?”
“宮外孕。”的姐嘆口氣。
二十一歲的妹妹昏倒在紡織廠車間,大出血,她的工服,紅了兩條褲管。等小馬跪在病床前,妹妹還在昏迷中,他握著妹妹的手懺悔,的姐哭著攔住大哥雨點般落向小馬的拳頭。隔了三十年,的姐仍咋舌:“就這樣,我哥也把他揍成了‘豬頭!”
那天,小馬就頂著一顆“豬頭”,對妹妹的親人們,包括的姐,磕頭如搗蒜,發誓會一輩子對妹妹好,非她不娶。
妹妹醒來,張口第一句話:“你們別怪小馬。”事已至此,只能順其自然。出院后,小馬的媽媽伺候妹妹的小月子。小馬不上班時,都在妹妹那兒。
“后來呢?”我著急聽結局。
“后來,我妹的身體好了,又過了一年,兩家人開始給他們籌備婚禮。眾人齊心合力,將擺在院子里的新家具挪進房間,小屋滿滿當當,只差帶電的。”
“帶電的?”
“對,彩電、冰箱、洗衣機,還有錄音機。”
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鋼廠的青年工人,靠工資,按市價集齊它們,可望而不可即。
就在小馬抓耳撓腮之際,幫打家具的一個哥們兒帶來“好消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批貨便宜出。小馬將四大件拉回家時,妹妹去胡同口接,兩個人親親熱熱。遇見街坊鄰居,他們就邊推著四大件,邊喊:“婚禮那天全來啊!”
“他們結婚了?”我也感染了喜氣。
“那就不是前男友,是前夫嘍!”的姐幽幽地拖長了話音。
那批貨,四大件只要一大件的錢。事后證明,那是一批贓物,團伙作案,負責銷贓的,正是小馬的哥們兒。小馬沒參與作案,可購買贓物的事實在,小馬沒法兒自證清白,他和四大件被一起帶走,警笛呼嘯,胡同口圍觀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一判就是十五年,婚禮沒有舉行,連結婚證都沒來得及領。
“幸好沒領。”
“你妹呢?”
“我妹等了幾年,小馬的媽去世了,是我妹料理的后事。后來,我妹年紀大了,我們都說,別等了。再后來,我媽生病,醫院下病危通知書。手術前,我哥簽字,對我妹說,你要是孝順,就該干嗎干嗎,讓媽能活著看到你成家立業……我妹三十歲才結婚,做了三次試管,才要上孩子,宮外孕的后遺癥。”
“小馬呢?”
“表現好,沒到十五年就放出來了,他沒回胡同,聽說去南邊跟人做服裝生意,又說去國外打過工,消息都是老街坊給的。”
“你妹就再沒見過小馬?”
“到了,請帶好隨身物品。”的姐靠路邊停車。
“你妹就再也沒見過小馬?”我不想下車。
她深吸一口氣:“上個月,我在今天你打車的地方附近下車,去超市買水果。路過肉攤,想起晚上要給兒子包餃子。那師傅挺胖的,也不作聲,默默剁好肉,裝進袋子,把袋子遞給我時,喊了我一聲‘大姐。我一看,這不是小馬嗎?”
“你和他相認沒?”我問。
“認了。他問,都挺好的?我說,挺好。他說,麗麗也挺好?我說,好著呢,結婚了,有兩套房,孩子讀高二。他說,那就好。”
“你妹知道嗎?”
“知道,我回去就告訴我妹了。第二天我和她一起再去那個超市,經理說,馬師傅昨天已經辭職了。”
“什么?”我驚詫,繼而嘆息,“也許他不想你妹見到他現在的樣子。”
“從超市出來,我妹坐在馬路牙子上捧著腦袋哭。她說,是她害了小馬,她該等他的,她就想當面告訴他這句話。”的姐說。
我驀地想起什么:“所以,你最近都在那條路載客?想為你妹找到她前男友?”
的姐沒回答,陽光刺眼,從車前窗直射到我們臉上。她掰下遮陽板想擋住陽光,收手時,卻忽然抽泣起來。
我們沉默了幾分鐘,她戴上墨鏡,遮住紅腫的眼睛,聲音哽咽,極力保持鎮定:“請帶好隨身物品。”
“謝謝。”我說道。
我緩緩解開安全帶,特意看了一眼前排的司機證件,是的姐的照片,她姓“梁”,名“小麗”。
我下車了,走出一百米,回頭看,那輛車還在,路況良好,完全不堵,不知道為什么,一直沒有前行。
也許,只是她們姐妹的名字相近。
(從 容摘自《啄木鳥》2021年第8期,王 赟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