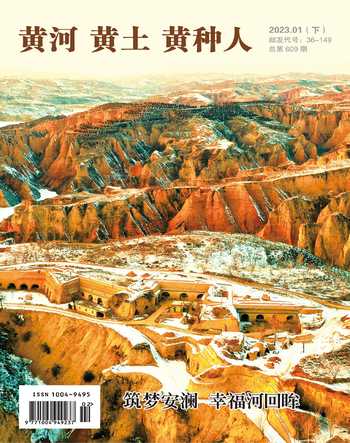我們的“三十里畫廊”
劉遂林



題記:2022年國慶節,友人來鄭,這是其上次來鄭多年后又一次來到黃河大堤,他非常驚詫這段大堤的變化。這段黃河大堤的變化主要發生于最近三年,生態廊道、312沿黃大道與灘地公園相繼開工,目前基本打造完成。友人感慨景色之美,稱其為“三十公里畫廊”,我說沒詩意,就叫“三十里畫廊”吧!其后的日子,我不知又走了多少遍這“三十里畫廊”,其中有品不盡的風景,講不完的故事,訴不盡的大河壯美。我找不到能把這些風景與故事串聯在一起的線索,又不想平鋪直敘。直到深秋,楓葉紅了秋色,才打定主意以大堤門樹紅楓為引,以黃河大堤為線,串起零亂的風景與故事,將我瑣碎的遐想匯集成一路的低吟淺唱。“三十里畫廊”就此徐徐展開。
黃河蕩來蕩去,不知在何時將鄭州的邙山沖開了口子。有人說原來她不從這里過,而是沿著太行山往北去的。她的桀驁不馴也不知吃掉了多少個邙山頭,面對廣袤的大地,見山吃山,見水越水。歲月不停輪轉,日月悄然更迭。她帶著大量的泥沙,年年淤填,平了山,填了河,高高在上,人們只好筑了堤,束了地,這便是黃河下游大堤的起點——0公里。從鯀、共工、禹開始,沒少費心,又經歷了多少代人的前赴后繼,她依然無休無止地繼續,依然是蕩來蕩去,唱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單曲循環。直至有了今天的控導工程,她的游蕩才有了些許停歇。而零公里的大堤正是上接峽谷,下送平原的起點。千里金堤始于足下,這里有一塊標志石,高高佇立著,預示著0的開始。一個個獨立柱構成的大漩渦寫滿了黃河大事記,記錄著黃河曾經的滄海桑田。
深秋,寒意初上。從0公里出發,楓葉紅了秋色,江山如此多嬌,那紅的楓,血樣的熱烈。秋風過處,一葉一葉地飄落。“小楓一夜偷天酒,卻倩孤松掩醉容”。這該是怎樣的景象,兩年前栽下的棵棵大堤門樹紅楓,如今似火炬,如烈焰,一路東行,紅楓一路相伴,心也與落下的楓葉形影相隨。
四季植物園是生態廊道的一個節點,各種名貴樹種在這深秋的暈染下,紅的、黃的、綠的,姹紫嫣紅,一團團的粉黛暈開宛如朝霞的腮紅,在一笑回眸中綻放。
旁邊便是花園口水利樞紐的泄洪閘——十八門閘。十八門閘的上首是黃河的支流枯河入黃的拐彎處,下首是十八門閘的消力池,也就是如今的崗李水庫。閘仍然銹跡斑斑地沉睡在那里,無聲訴說著曾經的崢嶸歲月。
它靜止在這里,閘前的枯河在這變了樣,河中的小島與島上的樹倒映在湖面上,秋風秋水,蕩起層層漣漪,無不勾起時光的薄涼。如火的歲月,停滯在冰冷的鋼筋混凝土上,靜靜訴說著曾經的浮沉往事。崗李水庫,它只是十八門閘的消力池,曾經在缺水的鄭州,有這么一汪不大的水池,竟賦予了它一個大的名字——崗李水庫。池的四周,密密麻麻長滿了許多不知名的樹,以楊柳居多。楊柳的品性與眾不同,它不算名貴,有自生自滅的屬性,喜歡居河而生,生長期短,成材快,北方比較多。正是它們裝點著這個水庫,賦予了它無窮的生命,點綴了靜默的十八門閘。歲月更輪如煙,解一裳往事的熏染,揣一念歷史的感慨,淘染的鉛華,臨水的依念,文字是寒涼的秋風,思緒愈拉愈遠。
往前走,兩邊的楓葉更紅了。歲月如風,經歷了嚴冬盛夏,由青澀步入茂盛,如今已是最后的輝煌,真不想讓它片片飄落,但生命就是這樣的過程。好在臨終還是走進那片熾烈和燦爛,這是最后的時光。是一份妥妥的安暖,投生了生養它的土地,回歸了最終的陪伴。
往0公里東行10千米,就到了花園口。抗日戰爭時,為阻日軍西進,在此決堤,水淹日軍,同時形成廣大的黃泛區,日軍淹死3千,中國軍民淹死80余萬,功過不用后人說,也便知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巨大災難。花園口,多么充滿詩意的名字,卻因此黯淡了許多。站在時光的深處,凝望遠方,在這深秋的寒意中,在南北廣場的浮雕墻上,似乎仍能聽到這近百萬人如泣如訴地吶喊。
本來黃河流到這里,清朝就有馮莊漫決。為此,百姓祈愿,豎了鎮河鐵犀,立了大將軍像,到了民國,又有了花園口的決堤。人為的、自然的,這段黃河承受了太多的災難。花園口這個美好的名字未能為這里帶來該有的歲月靜好,反而處處傷痕累累,直到人民治黃,淤了背河的洼地、寬了窄薄的大堤、成了國家級水利風景區,才恢復了花園口該有的詩意,留下這段厚重的歷史,流淌在時代的記憶里。前事之史,殷鑒不遠。那掙扎在泥濘中的車馬、日本兵和流離失所的中國民眾浮雕,讓人不禁為前者的累累罪惡而憤慨,更為后者的餓殍遍野而哀嘆。戰爭的無情在這兩幅浮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里歷史厚重,不僅在于那場人為的大決口,還在于人民治黃的偉大成就。將軍壩穩固的根石,是黃河下游最大沖深的歷史見證。花園口閘是黃河母親用它的乳汁滋養中華民族的現實展示,而花園口水利樞紐工程則是一代代治黃人的不斷探索。走到這里,如秋風吹起一串風鈴,激蕩著不同的聲響,或清脆悠揚,或蕩氣回腸,或低沉哀怨,或鰲憤龍悲,無不填充著我們的心田。
駐足在惠金黃河記憶展覽館前,那青花瓷色的“記憶”兩字以及舒緩平靜的《問天曲》,彰顯著惠金人的匠心。展覽館內陳列的老物件和老圖片,無不在喚起你的記憶。秋的晨光,秋的艷陽,秋的暮色,是輕盈,是張揚,是厚重。循著歲月的煙火,書一份不老的情懷,編織最初的相逢,讓那份深深淺淺的記憶越過千山萬水,與你在這靜好的歲月里相結于此,這便是展覽館設計者的眷眷心念。
再向東走,是一段塔松的門樹,那是一年盛夏栽種的,當時只有3米高,如今已是十幾米的參天大樹,兩邊的枝條已握了手,形成一個綠色的隧道。深秋了,它們仍蒼翠欲滴,陽光透過樹縫斑駁陸離。一對小年輕在這里拍婚紗照,他們手挽手,與歲月相牽;他們互相擁抱,對視中覓得靜好,臉上是淡淡的清歡。他們一顰一笑的細膩、一個會心的眼神,都傳遞著深情,與這牽手的塔松相伴,相得益彰。
終于走到了15+800的標準化堤防展示點,不遠處就是鄭工堵口所在地。鄭工堵口,歷史著名。20千米的黃河大堤,竟在近現代就有三次決口,真的是多災多難。黃河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三絕碑”在這里復刻,黃河大堤的歷史在這里記述,堵口五大臣的人生在這里沉浮。說它著名是因為此次堵口花費了全國當年四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而且此次黃河治理第一次使用了電話、電車、水泥。最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金石學家、書法家、河東河道總督吳大瀓碑刻的字樣,竟和電腦打印的隸書沒有多大區別,令人叫絕。不禁想起成也黃河、敗也黃河的李鶴年,即便身遭誣陷,卻仍心懷志堅……這些治黃前輩的事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眼前。
這是一段黃河的著名史。走到這里,不難想象曾經的場面,定是車水馬龍、人聲鼎沸、淚眼婆娑和歡欣鼓舞。歷史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啟迪,而歷史人物又都在世人腦海里鮮活呈現。前人走過的往往是后人不斷重復的。他們的敬業與睿智,令人贊嘆。
往前從惠濟區進入金水區的堤界,兩邊的門樹變成了紫荊,它在春天絢爛,在深秋烏暗,忽然間由熱烈走入靜然,黯淡了色的光艷。
泥馬渡康王的傳說發生在這里,但也只是傳說,是后人的杜撰。那時的黃河大概不從這里經過。
馬渡下延的色彩是這個季節里最為絢爛的。春天時這里是花的海洋,秋天時這里是彩葉樹種的展示地。這里有金水區最美觀河點、河道工程展示點、搶險演練場,還有令人驚艷的砌石文化。要我說這里最美的是那個觀景點,大河迎面而來,或浩浩蕩蕩,或靜謐安詳,可以觀長河落日,也可以賞鷹擊長云,只是魚翔淺底看不到,但可以想象。河畔的金柳,真的是大河夕陽中的新娘,她比其他的樹早早地綠了河岸,往往又比其他樹更晚地褪去暈染。秋光里的倒影,是那種渾然天成的美,是相安相偎的朝暮,是滿腹的相思、相戀、相融。你真的是大河夕陽中的新娘,是人世間最美的畫卷,是秋季的情詩。
渡頭柳是“三十里畫廊”的最后一個景點。這里是30+968,中牟和惠金的交界。一棵古柳挺立在這兒,經歷著百年滄桑,如今依然蔥蘢。死去的殘枝還躺在它的身邊,無情的雷火燒毀了它的偉岸,在毀了的偉岸旁又有新的生命。生生不息、堅貞忠實,決定它的隨情隨性。花崗巖的保護圍欄,幾尊表達少男少女綿綿的情思、別離、等待的石刻,無不將“留住”的意境體現。能體會長河渡口旁,夫去婦隨,自此分別,折柳為念,等一個歸人的情景。縱然隔著長河,也早已將彼此融入生命。品味彼此的心靈呼喚,將折柳折出彼此走過的點點滴滴,用眷戀折緊情緣,用懂得浸潤時光,點綴起每一程山水,絢爛出銘心的印證,謹記最初的相遇,堅守一生的承諾。
深秋的黃昏,回覽“三十里畫廊”,金黃、蒼翠、火紅,是一路的主色調。白蠟、紫荊、娜塔櫟、云杉、塔松與紅楓,還有銀杏,是一路相伴的樹種。走過一路的瀲滟清歡,還有竊竊的濃情。有塵世的滄桑,還有心陌上的素雅。時光靜好,歲月安恬,任憑歲月滄海桑田,守著不變的誓言。經半世的世事變遷,許下一懷柔情的網,打撈出對人生的期盼、緣分和遇見。
惠金黃河,潮起潮落。“我愛你,惠金的‘三十里畫廊!”感你、知你、想你、念你,愿你裝扮的黃河大堤在今后的歲月里,靜美安晚,安瀾無恙。